近代学者对国际法定义的认知
时间:2022-10-25 01:3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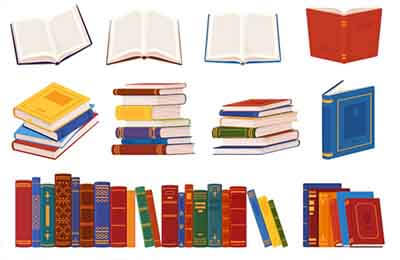
一、基于主体范围的界定
尽管国际法主体在国家之外的新鲜发展已经被近代中国学者所注意和观察,也不乏专著或论文就此明确述及或着意探讨①。但在予国际法以学科定义时,学者们仍对主体的范畴表现出普遍的谨慎。民族、国际组织、个人都成为20世纪初叶学者热议的国际法主体的新可能,但直到20世纪30、40年代,在国际法的定义中,几乎所有有关主体的措辞仍被严格限定于“国家”。1926年朱采真列举已知的一些代表性见解,最终认为国际法的“新的意义”即“国际法是关于文明国家相互关系上所设定的规则而为各国所承认”。在对这一定义的分析中,将“国际法是关于文明国家相互关系上所设定的规则”作为其第一层次的要义,强调“这种权利义务的主体限于文明国家,并不是他国人民,也非野蛮社会”,因而国际的“相互关系”就“包含着下列两种:国家相互间的交际行为;国际相互间的战争行为”[6]4-5。同样将定义分不同要件进行阐释的如1935年王承勋编《国际公法》、1936年吴昆吾编《国际法纲要》。王承勋认为,国际法定义大致可概括为:“国际公法是在国家相互间的关系上,支配其行为的规则,而且经多数文明国家所承认和公同遵守的”。言下其第一要件应为:“国际公法的主体是国家,不是国民”,而由国家交往才产生了国际法的三类规则:“(甲)平时相互间的交际行为,(乙)相互间的战争行为,(丙)非常时中立国的权利义务行为”[7]1。吴昆吾接受了“法国学者彭斐士氏之说”,认为:“国家与国家交际,规定其权利义务之关系者,曰国际公法。”由此定义分析出二大要件,其一便为“国际公法只规定国家间权利义务之关系,逾此范围,即非国际公法”[8]1。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能对国际法定义以清晰分层的方式予以解析,在民国时期其他的国际法著作中,仍可轻易发现“国家”在定义要件中基础地位。如1933年谭锡痒著《新编平时国际公法》,将定义表述为“国际法者乃规定国家互相间之行为而共同所遵由之法则也”,并由国际法存在之前提做出解释:“国与国交际而有行为,有行为故有法则,此法则谓之国际法……若不有法则于其间,为一般之所遵循,则破裂立见,殊非国际间之幸福也”[9]3。1934年,周鲠生在其《国际法大纲》中提出,国际法是“一部习惯的及协定的规则,世界文明国家所认为在他们相互关系上,对于他们有法律的拘束力者”,简而言之,这应“是规律文明国家相互关系之行为的规则”[10]2。1931年上海法学编译社所编《国际公法私法问答》、1932年周还著《国际公法》、1937年刘达人等编《国际法发达史》也都以简要的语句突出了对主体的相同坚持。一说为:“公法者,定国家与国家权利义务之关系也”[11]1;一说为:“国际公法是规律国家与国家在相互邦交中权利与义务的规则总体”[12]1;一说为:“国际法一词,约言之,即为规律国家与国家之关系的法律”[13]1。
二、基于效力依据的研判
1922年谭焯宏简要定义国际法为“国际间利害共通之法则也”,其“共通”二字正道出了各国共认对国际法成立的决定性地位[14]2。意即,国际法规则的成立需要国家的承认或公诺。同样,1926年朱采真在其《国际法ABC》中紧随主体要件而列出的第二层次便是:“国际法要经各国承认”,“国际法的有效存在,须以经过各国的承认为要体”[6]5。1927年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自称作出了“著者最新之国际法定义”,称:“独立诸国。集成团体。创立机关。其团体间所有关于和战之义利。与卫护人道讲信修睦之法规条约、学说成例。其团体员、皆承认之而遵守之以为一定之准则者。是即国际法也”(标点为原文所有)。在这个极具本土色彩的表述中,仍未忽略国际法应为国际主体“皆承认之而遵守之”准则。在作者随之进行的阐释中,其第四项更是明确表示“国际法即万国承认之法规条约学说成例”,既然它“非由最高者所制定。整部颁行……乃合今古无数之法规条约学说成例而后先成立者也。方其次第成立为国际法。必经万国之承认”[15]16-18。王惠中对这一分析也颇为接受:“以国家之至高无上,故学者遂谓国际法为存于各国家间之法,非加于各国家上之法。换言之,国际法非某权力者加于各国之上之法,乃各国自行承认之法也”,由此判定,“承认遂为国际法之成立要件”[16]1-2。类似的认知还可从众多后来者的论述中找到踪迹。例如,1933年谭锡痒称:“此法则为文明诸国所承认者,谓之国际法”[9]3;1935年王承勋言:“国际法的主要基础,就是须经国际社会共同意思的承认,始可能有效的成立”[7]1-2;1941年张道行的定义是:“国际法者,国际社会间相互间关系之行为的规则,经多数文明国家所承认而遵守之者也”,并强调“现今国际法学者,都一致的承认国际法的基础是公诺(commonconsent)”[17]3;1946年崔书琴也指出,国际法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是国际社会各分子公认的法律”,“国际法的一切规则都须经过世界各国公认始能成立”[18]1。关于承认的方式,学者们也基本达成共识:有分为“明示的承认”与“默示的承认”,有分为“明许之承认”与“默许之承认”,有分为“明示的公诺”与“默示的公诺”。尽管措辞有些微出入,但其含义已然统一。如朱采真提出:“明示承认是由于条约或其他方式加以承认;默示承认是关于习惯上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宁协万也认为:“明许之承认”就是“将条约及其他之外交文书、特为意思之表示”;“默许之承认”即“无披露之形式,而于事实上依其习惯实行焉”;王惠中称“国际条约或国际会议所规定之事项”应属明示承认,而“事实上为各国所准据之事项”为默示承认;王承勋则直接地释义:“明示承认是订立国际条约,默示承认就是沿用国际习惯”。当然,以承认为国际法成立之要件并非要求全部国家无一遗漏地为意思表示。关于这一点,近代中国学者们也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宁协万的说明如下:“……夫既云万国。似宜包括世界所有各独立国。然试问现行之国际法。果皆经世界似有各独立国之承认乎……是以知凡法规条约学说成例之蜕化为国际法。但有多数独立国之承认。即可以无摇动之虞矣。”[15]16-18王惠中也明述“各国家之承认”只是“在原则上”的提法,“实则只须对于某规则所定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国家多数承认时,该规则即成为国际法而发生效力”[16]2。张道行也分析说:“所谓公诺,不是说国际社会内的一切国家,均须明示的就各项规则,一一加以承认;乃是指国际间大多数的国家,已加明许,或默认的解释。”[17]3
三、基于内涵范畴的概说
以调整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或以规定国家间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成为当时公认的支撑国际法定义的第三大基本面。1931年《国际公法私法问答》指公法是在“文明竞争之世”,“定国家与国家权利义务之关系也”[11]1。1932年盛沛东言:“国际公法详言之亦可谓由数国家以惯行或条约所承认而规定国家相互权利义务之法也。”[19]1这与同年出版的周还著《国际公法》中的表述几乎完全一致:“国际公法是规律国家与国家在相互邦交中权利与义务的规则总体。”[12]1一方面,学者们以权利义务的安排为国际交往的务实需求。王惠中提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有互相交通之必要,爰组成一个社会,是为国际社会。属于国际社会之各国家,为尊重彼此之权利利益及增进国际共同生活之幸福,必须有应行遵守之一般规则”,由此,规律“各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之一般规则”才为国际法[16]1。吴昆吾在分析其所认可的法国学者的定义时也称:“权利义务,由交际而生”,故“无国家交际,斯不必有国际法”[8]1。另一方面,正如朱采真所言:“国际法原是一种法律,自有权利义务的观念之存在”[6]4,规定国际法必须以设定国家间权利义务为功能或目标,其实是国际法为法的当然内涵,也是对国际法法律性质的再次印证。郑斌提出,国际规则并非都具法律属性,“有关于道德或礼让者,有决定权利义务之关系者”,“后者之中……有定国际团体中一切国家间之关系者……谓之国际法”,故国际法为“规定国际团体中国家间权利义务共通关系之规则也”[20]1-2。赵理海也确认,各种关于国际法定义之说,“皆假定各国相互关系以及此各关系的法律性质之存在;此种事实,固由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共同法律观念,抑亦真正国际社会运用的结果”[21]1-2。既为法律,以分配权利义务为核心来实现国际法的规范和调整,便为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面对国际法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已日渐坦然,上述三方面的要件作为国际法定义的基本范畴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接受。不过,在限定主体、要求承认、确认权利义务三者之外,也有学者提及其他方面的关注与考虑。如崔书琴就认为国际法的定义应包括四大要件,除与上述相合的三条件之外,国际法规范还须是实然的而非应然的,“它只包括国际间公认‘必须’遵守的法则,而不包括学者以为国际间‘应该’遵守的规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有法律拘束力,而后者无;“前者是国际法的实质,后者是国际法的学理”;“前者是国际法科学观,后者是国际法的哲学观”[18]1。尽管作者将此点独立于其他三要件外,但所谓实然与应然的区分仍不过是依法律拘束力判断的结果,是证明国际法规则应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又一种表达,而此点凭依各国承认及规定权利义务的要件已足以被涵盖其中。当然,上述的定义命题其实都发生在系统接收欧洲国际法学理论的背景之下,而在笔者可见的资料中,近代中国学者所处的特殊历史时空与来自于其他思潮的冲击也催生出某些独树一帜的定义视角。如,蔡可成曾专门界定所谓“非常时期之国际法”。他认为,国际法仍是“规律世界文明国家间之关系的法律”,“不论平时或战时,国际关系上均有一定法规为之规律”。以“非常”来定位国际法,其一是指所处时间段的“非常”,是“指情势严重,有异于平时,而将陷入战时的这一个时期而言”,既不为和平时期,也不为战争时期,而是介于两者间的“一个承前接后的阶段”;其二是所侧重的研究内容的“非常”,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国际争议频发,国际交涉繁密,而国际形势成为危殆”,“如果不幸而争议不决,谈判无效,则趋向所在,必不出战争之一途”。因此,这时期的研究应着重于三项内容:“第一为外交谈判的形势,第二为争议之解决办法,第三为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一旦发生,中立国的地位如何”[22]1-2。另一种独特的界定来自刘独峰,在他所著的《国际学大纲》中,处处表现出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这一具有强烈阶段倾向的思维模式也自然地适用于其对国际法的定义。他提出:“法律既然是阶段社会的产物,那么,国际法的产生,也当然不能够脱离阶级性的。”由此,分别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国际法的含义也不同。对前者而言,“国际法就是为着保护资产阶层在国际上的权益的工具”,而对后者,“国际法就是为着增进无产阶层在国际上权益的工具”。因此,刘独峰总结,国际法应是“同阶级的法律”,“是保护和增进同阶级在国际上权益的法律”[23]92。这一界定也可算是另辟蹊径。
四、独立界定“国际法学”的学术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法”定义之外,已有学者意识到应就“国际法学”单独观察、另行界定。应该说,近代中国学者依循欧洲国际法体系所推进的系统研究在不断丰富,但从专门学问或学科部门的角度就国际法学进行阐释者仍屈指可数。成果寥寥,却更显可贵。1894年傅兰雅等译《各国交涉公法论》,粗略回溯了国际法学的由来,先称“各国交涉公法之源……日见精详”,得益于“文人著述成书,甚为明晰”;又说学者们“各有著述”,“便于考究此学”,因此,该书“先论历来著名之法师,后论公法之学”[24]1。种种表述,无不透露着国际法学与国际法专门家之学说著述间的直接关联,暗示着国际法学应是以国际法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尽管上述译文并未就“国际法学”做出明确的定义,这一理解“国际法学”的角度与立场却得到了中国学界的接受。如周纬在《新国际公法》中有言:“国际法理之需要,既随各国交涉而产生,于是国际公法学,遂积渐而成为专门学”[25]3。其意一为,国际法学应区别于各国交涉规则的国际法;其意二为,国际法学是就国际法理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累积。由此反映出的正是与傅兰雅译书一脉相承的认知立场。不过,以笔者之见,真正称得上对“国际法学”做出明确界定的似只有朱采真所著《国际法ABC》。该书在阐释国际法定义之后,特就国际法学专门界说。先就欧洲学者的相关见解简要介绍:国际法学或被认为是“指导各国间所有权利义务的科学”,或被认为“是支配各国独立生活之法则的科学”;再就自己的观点予以表张:“足见国际法学也是一种科学,并且是关于国际间权利义务的法则的实用科学”[6]5。
五、余论
至此,近代中国学者在探讨国际法定义时所牵涉的基本要素及相关努力纵深略表于上。一如今天学者仍有的困扰,学科定义尽管为筑基所需却又离不开对学科各域的整体把握。近代中国学者对国际法定义之体认或创见,也正是在学科名称、适用范围、材料渊源、基本原则、性质效力、研究方法等相关原理的发展、融汇、浸染中慢慢得以充实与演变。作为国际法学最为基本问题之一,有关学科定义的探讨与结论无疑是近代中国国际法学理论研究与制度建构的基础与起点;而对当时学界基于西方译著从直观搬译到系统解析再到质疑改造的演化历程有所回溯,既是把握近代中国国际法学理论基线的必要步骤,亦是探寻当代中国国际法学的概念源起以为借鉴的重要凭依。(本文来自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杂志。《南京政治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刘畅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