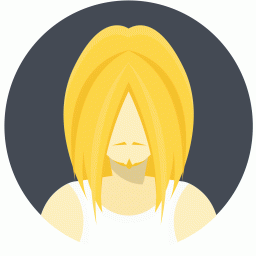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研究
时间:2022-01-28 10:35:45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及公共领域的关系。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欧洲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绝对君权时发展出来的概念,它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市民们假定可以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者要求确保代议的权利、言论与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对民意的尊重,于是他们就借助公共领域,通过报纸和期刊引发的辩论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权益。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就是公共领域――大众传媒有力地参与营造了大众文化得以生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可以突破统治者的话语霸权垄断而实现自由信息的传输与制造。
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和官员曾预期,借助媒介便有可能建构一个欧洲文化政治的公共领域。他们假定媒介受众渴求知识和信息,这知识和信息成为政治反思和论辩的基础。帕迪・斯坎内尔(Scannell,P.)曾指出,现代民众民主政治将论坛设在全新的、由广播电视构成的公共领域。有证据表明,电视对于组织、安排人们参与政治和休闲活动这样的公众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事务委员会在1964年就曾指出“通过运用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有可能触及大部分有影响的国民――给他们提供信息、影响他们的态度……促动他们走上特定的行动方向。这些集团反过来又能够向其政府施加显著、甚至是决定性的压力。”传媒在连接私人世界与公共领域中起到潜在的作用,传媒受众常常被视为由家庭单位构成,而国家又是由家庭组成。传媒将国家这个政治概念演化成想象中的社会群体,它通过连接家庭、组织日常生活以及构建国家机制,可以增强象征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然而,传媒技术的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以及其他的新型通信方式的出现,使民族文化群落被分解,大众世界分散、零落、多样化。
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一位批评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J.)就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对公共领域予以关注,引起理论界的广泛注意。而公共领域与传媒成为世界范围的研究课题是80年代以来的事。英国学者彼得・达格伦(Peter Dahlgren)在《电视与公共领域》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文化环境有三大特点:一是认同多元化,二是社会关系表面化,三是符号环境传媒化。这三个特点都与电视与公共领域有关。
大众传媒的民主功能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日趋下降:18世纪的大众传媒将个人意见转为公众舆论,公众可以通过传媒参与讨论、干预政事,从而加快社会的民主进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众传媒日趋被意识形态所操纵,于是,大众话语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取代、公民的民利被损害、公众舆论失去其原有性质而成为传媒操纵的结果。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了”。最终的结果是:公众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消费,(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是私有媒介和广告商的利益占上风,超过了对公共服务和媒介民主的关注。)公众失去对政治和民主社会的参与热情,从传统文化批判者的“公众”(public)转化为传媒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大众”(mass)。所以,文化研究者越来越对大众传媒对民主和公共领域的威胁表示担忧。对此,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指出,公共领域并非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传播媒介的发展已经创造了一种传统模式不能适应的新的非空间化、非对话性的公共性。即与其说大众传媒的发展导致公共领域的消失,不如说是创造了新的中介化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它可以使更多的个体经历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从而提高自己的民力。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对信息的接触难以控制,但是,一旦控制传媒又有可能导致传媒专制,所以说大众传媒所创造的这种中介化的公共性是一把双刃剑。
当前,公共休闲形式日益衰落(比如电影),家庭休闲日益私人化(比如录像机的使用),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人们提供了远程购物、电话银行和电脑网络化家庭办公,这都预示着工作领域与休闲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型。媒体可以迎合受众的需要(甚至是低级的非理性的欲望)而在市场走红获得商业利润;同时,由于传媒运作经费越来越依附于广告,其间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受众接触过程中的商品化问题,而是同时改变了交换过程中的“价值机制”的动态关系,也涉及不同团体(如广告客户与受众的对立)决定生产机制的权利以及彼此消长的演变。于是商业媒介本身就其内在机制而言,原本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促使其自身与流行文化的品位和结构产生某种程度契合的内驱力。传媒因其控制权造成文化同质化的同时,它的具体运作也为各种消费文化建构起了巨大的市场,换句话说,通过传媒所放送的各种产品(电视节目、广播及网络信息等)直接目的是吸引受众和广告商,以获得商业利润,因而公共领域丧失了真正的公共性,而服从于某种权力的立场和利益。
虽然我们看到大众传媒市场化所带来的一些弊端,但是也并不完全同意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如阿多诺、阿尔库赛、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的悲观论调,因为传媒受众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的接受文化商品及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内容。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分析公众对电视节目的态度,他认为观众中可能存在三种“解码”立场――霸权性立场、协商性立场和反抗性立场。如果说第一种立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调提供了某种来自受众视角的支持的话,那么第二种立场就已经有所偏离了,第三种立场就转而站在了其对立面。换句话说,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公众的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人们的“位置”各不相同,分别拥有着自己的话语,因而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从自己的经验、环境和知识背景出发加入到生产和流通各种不同的意义中去,根据自己的话语来理解文本。所以,我们应该考察研究媒体的社会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影响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简单的,甚至也不是直接的。这种复杂性和间接性的本质同样需要以一种清醒的理智态度去审视,需要得到论证、研究和探讨,或许,这更为重要。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