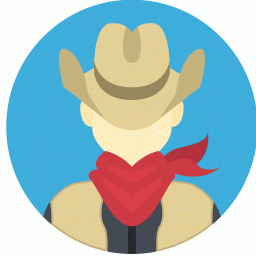上海文化总也不老:沪语话剧迎回“尹雪艳”
时间:2022-08-19 07:53:37

最近上海滩最火热的文化事件,莫过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心中最重要的女人——尹雪艳,在其诞生47年后首度从小说中走出来,活生生地站在了舞台上。和白先勇其余作品被影视、舞台剧多次改编不同,白先勇从未对任何人授权改编过《永远的尹雪艳》,而最终让白先勇放心交出“尹雪艳”的,却是因为沪剧演员出身的导演徐俊的4个字——“沪语话剧”。
对白先勇而言,《永远的尹雪艳》很重要。在他的《台北人》系列小说中,它被放在第一篇。小说最初的故事缘自白先勇与上海的三年因缘:1945年抗战结束后,白先勇在上海度过了他9岁至11岁的时光。在白先勇的印象里,重庆都是尘土,而上海却是个光鲜亮丽的花花世界。当然,当时还是小学生的白先勇并不曾踏进过百乐门,“只是路过门口张望时,总看见懒懒摇着扇子的舞小姐婀娜地款步踏入”,而正如白先勇在首场演出之后与记者笑谈所说,“永远不要小看孩子的眼睛”,这些印象慢慢酝酿,日渐鲜明,若干年后当白先勇萌生创作《台北人》时,《永远的尹雪艳》成了第一个跳出他脑海的作品。
更值得一提的是,《永远的尹雪艳》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刊登的第一篇台湾小说,刊载于1979年的《当代》创刊号。而白先勇最得意的也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尹雪艳总也不老。“不老是违反自然的,所以严格说起来尹雪艳是个超自然的人物,她就和上海这个城市一样,即便历经跌宕饱经沧桑,面上却是不留丝毫痕迹,依然故我地绝然超脱于碌碌俗世间,永远年轻、永远自信,永远有转机和福运。”在白先勇眼里,尹雪艳是上海钟灵毓秀的产物,她有着上海独有的精致内敛和低调富丽,他说,“1987年时我就曾预言,上海是长江的龙头,它一旦抬了头,就不得了。现在你们看,正如尹雪艳不老,上海也不会老。”
如果说支撑一位美人“永远不老”的是她的人格魅力,那么支撑一个城市“永远不老”的,自然是它独特的城市文化——而语言正是文化中最重要和首要的那部分。所以,当“尹雪艳”轻摇折扇,笑带一口纯熟软糯的“上海闲话”华丽归来时,不仅迅速笼络、熨帖了一众上海男女老少的心,更是引发了沪上文化界人士的种种热评,上海剧协亦为此组织研讨,一时间,“沪语话剧”俨然成为了一宗“文化事件”,被赋予了“重振海派文化”的重要意义。
白先勇说,尹雪艳总也不老。
我们相信,上海文化亦然。
北方有《茶馆》,上海拿什么“别苗头”?
谁都知道,“尹雪艳”是白先勇心里“最特别的女人”。据白先勇透露,此前除了谢晋导演曾想将“尹雪艳”搬上银幕外,还有不少人“觊觎”着这位美丽不可方物的女人。可是他都因为太“爱护”而一直“深藏”着她,直到这一次他才终于放心地把“尹雪艳”交给了徐俊。对此,虽然徐俊连连自谦表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道”,但其实他心里自然是有数的:“真正能够让白老师放心‘交出’尹雪艳的,应该是‘方言话剧’这四个字。”
“方言话剧”这个词,对许多70后以后的年轻观众(也包括青年演员)来说,可能已经有些陌生了。这并不奇怪,因为方言话剧确实已经在上海消失了很久。其实方言话剧在“”前曾经极为盛行,几乎每个省的话剧院都曾用当地的方言演过反映当地现实生活的戏,有的戏甚至已成为经典,后人难以超越,辟如川味话剧《抓壮丁》,剧中的演员们并非说的都是纯粹的四川话,而是带有川味的普通话,当时的学术界称之为“地方普通话”。当然,用这种形式做得最好的、流传最广的、亦是至今都无法被超越的作品,自然就是老舍先生的京味话剧《茶馆》。
老舍先生是创作京味话剧的大师级专家,演京味戏又是北京人艺的长项,可以说没有老舍、没有《茶馆》、没有焦菊隐,就不可能有北京人艺的昨天和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完全用普通话来演《茶馆》是个什么样子。《茶馆》第一幕一开场就有一段“数来宝”交代时代和背景,这“数来宝”正是北京曲艺的一个品种,通俗易懂,极有平民性,用这种形式串场是老舍先生的一大发明。而在《茶馆》甫开场的这段“数来宝”中就有不少“京味词”,如:“提笼架鸟”、“白瞧着”、“外洒”、“就许”等等,有人可能听不懂,但这段数来宝既简化了剧情又概括了时代,且非常吸引观众的眼球,倘若不采用这种与全剧极为协调的演出形式,而改用普通话的旁白由演员来朗诵——当然所有观众肯定都听懂了——可问题是这还是老舍么?这还是茶馆吗?这还是老北京的玩艺儿吗?同理,如果“尹雪艳”这位在百乐门叱咤风云、迷倒众生的“舞国皇后”,在众人翘首中缓步自高台而下,悠悠落座于她红色天鹅绒的“皇后宝座”之上,一开口却是标准的普通话——“大家好”,这还是尹雪艳么?这还是百乐门么?这还是上海滩么?所以,正如她的创造者白先勇所说:“徐导一说用上海话演,我就对这个创意大感兴趣。因为只有上海的文化和精致才能孕育得出尹雪艳这样的人物,而尹雪艳只能是说上海话的!”
对于如何想出“说上海话”这么个“神来之笔”,导演徐俊并不居功:“看过白老师这篇小说的朋友一定知道,其实主人翁讲的话,白老师就是用上海话写的。”正因如此,作为上海人、作为曾经的沪剧演员,徐俊敏感地捕捉到了原著的语言精神。“并且,用上海的方言演话剧也不是我们首创。”徐俊介绍说,“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过这样的构想,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以实现。佐临先生当时之所以创办方言话剧,按他的话说,上海话剧应该两条腿一起走,一个是上海话,一个是普通话,我想他这么提出,一定对上海话剧有非常全面的思考。这次我们也是希望能把佐临先生的精神传承下来,在舞台上进行探索和实践,接续海派艺术的文脉和风韵。” 于是徐俊去征求白先勇的意见,“我说咱们尝试一下,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这种尝试和探索肯定是有意义的。”这个想法立刻得到白先勇的支持和肯定,“所以我们从写剧本开始,就是用上海话写的——我们的剧本就是上海话剧本。”
如果说作家、导演的“一拍即合”还只能解释为一种“直觉”,那么上戏戏剧戏曲学学术带头人叶长海教授的开宗明义则是给出了“理论”的支撑:“这部戏最有特色也是最让大家记住的,我觉得正是它上海话的演出。” 叶教授表示,在此之前曾经也有过一些讨论,比如梨园戏外地人听不懂,是不是改成普通话?“我那个时候就强烈反对,这就好比把欧洲的大歌剧翻译成中文来唱——之前虽然我听不懂,但看着字幕听着原唱词,完全可以同时做到理解和欣赏的;现在你们如果翻译了,我想我会更听不懂的。”所以语言不是根本问题,文化才是根本问题,这个戏的成功之处正是用上海话精准地传达了上海的文化。
什么是上海文化?我们不妨把目光再次投射到这部话剧上,在剧中,尹雪艳为什么既能吸引男人又能吸引女人——剧中的一句台词足以说明一切,“有尹雪艳的地方,就是上海”。正如上戏教授丁罗男的解读:“尹雪艳实际上吸引我们的是什么?优雅的老式上海话?张叔平手工缝制的旗袍?说穿了,是综合所有因素所重现出来的上海的美,只不过是投射在了一个具体的上海女人身上。”所以,尹雪艳即是上海;尹雪艳对男人们的态度,即是上海对所有人的态度——欲迎还拒;而男人们对尹雪艳的趋之若鹜,即是所有人对上海文化的向往和归属感。而上海的美到底是什么?上海的美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上海的美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占有的,就如同剧中的尹雪艳,那么多人围绕她转,那么多男人追求她、女人羡慕她,可是这样一种美却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占有的,如果你想一个人去占有它,你必将失败。这正如上海的文化,是现代的、开放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是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小格局的那种上海精神。复旦大学教授陆士清说自己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1937年以前,上海50个精英人物里——戏剧、电影、文学,包括演艺界的精英人物,真正的上海人就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外地来的。上海吸引了这么多人来到这座城市,留在这座城市,最终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这就是上海文化的根基。
语言不止是文化的载体,它就是文化
本身就是沪剧演员出身、对上海话颇有研究的徐俊导演说,他希望通过这出戏能掀起大家对上海方言和上海文化的关注:“上海话也在不断变化中,这与城市的记忆有关,有城市的韵律在其中。上海话有着与生俱来的优雅、斯文、含蓄。我希望戏里能呼唤出这种神韵,体现上海话真正的美学价值和文化魅力。”这得到了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的共鸣:“一地的文艺作品是应该直通当地人的性情的,所以,如果没有本来就对上海话十分有研究的导演徐俊和编剧曹路生的精心操作,如果没有本来就说得一口流利沪语的本土演员的精彩演绎,就不可能首创出如此精致的沪语话剧。”
钱乃荣强调,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曾经写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可以说,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力量和文化模式——人们自幼习得了这种语言,也就把其中包含一切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准则、文化习俗的文化符号深深地融进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语言还是一种有特殊性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代表的是不同的习俗,不同的语言习俗反映出不同的思想观念。所以,语言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很容易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在世界万物中,语言与人类思维的联系最为密切。”钱乃荣说,“国外现今的研究成果证明,一种语言,构成了一个地域的人的独特的思维,它会自然落实到人的生活、工作的每个方面,哪怕设计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因此有差异,更何况在文艺和情感、习俗上的差异。”所以,用沪语表现得好的话剧,当然会自然展现上海文化的风味。而语言经过翻译就等于是思维也换了一种,“就成了洋泾浜”,作品原有的韵味也会因此大打折扣的。正如古诗如译成现代诗,就会韵味全失,那其中的节奏带来的奥妙,是“语言统一派”绝对不能体味出来的。“何况上海的语言多元、文化多元、艺术多元历来就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主要特色,多元文化自有其创作和欣赏的根基。”在钱乃荣看来,多元才能借鉴和创新发展,上海以前轻工业产品的丰富性和前卫性也是一个明证。
在钱乃荣的记忆里,其实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全国各地都曾涌现出植根于地方方言和文化的优秀作品:像王洛宾就是躬耕于民间的音乐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源自吴越文化越剧和江南民间音乐;而以河北方言民谣《小白菜》为基调的插曲《北风吹》是电影《白毛女》的灵魂;《洪湖赤卫队》《怒潮》中动听的歌来自两湖楚地民俗文化;《江姐》的歌曲融入了川北号子的激越,并吸收了吴侬软语基础上的越剧的唱腔,才如此婉转优美;《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等又是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歌腔调的基础上形成了影片旋律。传达出中华民族各地特别风情的作品,总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因此,方言不仅是语言,还是中华文明的土壤;发掘方言的语言资源软实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地方口语哪怕带上一点,作品就会生动,或再稍加客地典型口语,就更加活泼,这都是得到证明的。”钱乃荣总结说,“就我所见,如今上海话的散文、小说、话剧,当前在初创和恢复中就已经很有市场效应了。”
而戏剧评论家翁思再则是从另一种角度强调“方言是一种文化”的。他指出,有很多汉语古音其实还保留在方言里,当我们用普通话读古诗词有时会感觉不押韵很别扭时,如果一旦改用某地的方言来读,很可能就会神奇地找到韵脚。“近年沈善增先后以《还吾老子》和《还吾庄子》重新注释先哲,一些新论即是通过对上古、中古、现代的字音考辨之后做出来的。”由此可见保护方言对于古籍整理、学术研究的重大作用。而上海话里的古音表现在哪里呢?比如“屋、北、鹿、独、宿”这些短促的入声字,在北方方言里是没有的。老上海称“龙华”为“龙花”,浦东话读“风”为“轰”,便是古音。又如上海话说某人脾气不好时称脾气“楸”,这种说法见诸宋朝的《广韵》和《集韵》。此外如浊声母系统以及本地话里的尖字系统等,都藏有汉语古音的影子。
除了“封存古音”的作用,翁思再说,方言的另一种文化表征体现为“作为抒情方式的承载”:中国地域广阔,文化多元,各地的群众抒情方式是有区别的。“比如女子失恋的情感反应,《红楼梦》里写南方的林黛玉是泪水连绵:‘春流到秋,冬流到夏’。”翁思再笑谈道,“而在北方呢,《诗经》有云:老女不嫁,踏地唤天。”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话就是承载上海人抒情方式的工具。清末韩邦庆以吴语写小说《海上花列传》,章培恒教授在《中国文学史新著》里列出其中一段评之:“如果是吴语区域的人,读了这一段就会觉得好像听到了她的倾诉,不仅充分感受到了她的语气及其中所包含的感情,而且其说话时的神态也恍在目前,如此真切、生动。这一切是无法用普通话来表现的。”张爱玲在把《海上花列传》改写成国语后,自己也觉得不满意,她说:“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成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失去语气的神韵。”因此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说:“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至于有些人担心的,“沪语话剧”这种形式会不会造成把一部分“非上海人”排除出去,更有甚者会不会引起“地域问题”的紧张化,导演徐俊表示不用多虑:“既然说语言即是文化,那么上海话就是上海这个城市文化的本身,所以,我们用上海话演戏不是为了排除谁——恰恰相反,我们是想用一种欢迎的姿态,欢迎所有对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来通过这个戏更亲近上海的内心,更了解上海的文化。”而对于这个稍有敏感的话题,翁思再半开玩笑说:“我觉得放在全局的语境当中,将来《永远的尹雪艳》这部戏在全世界演的话,市场是有细分的,我们就卖给上海人看就行了。我记得周立波前几年来找我,我说你坚持讲上海话,你就卖给上海人看就行了——事实证明这个方向是不错的。” 当然玩笑归玩笑,翁思再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这种担心和顾虑,换一种角度,也正反应了眼下在上海“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话”此消彼长甚至剑拔弩张的尴尬局面。“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嘛。”翁思再说,先哲对此早有预言——胡适早在《〈吴歌甲集〉序》中写道:我在七年前曾说,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胡适这番话是在上世纪初期,也就是白话文和国语运动兴起时说的,如果他看到今天国语已经凭借电视机的翅膀迅速普及全国,那么必定会告诫我们注意克服普通话和方言此长彼消的局面。”
提升“文化自觉”,重振“上海格调”
曾经,滑稽明星周立波以上海话脱口秀爆红;又曾经,以独脚戏为主的笑林大会栏目跃居上海电视台收视率之首;现如今,《永远的尹雪艳》打着“沪语话剧”的鲜明旗号,又一次成功地把自己从“文艺作品”变成了“文化事件”。这样的事接二连三,于是大家都看出这并非偶然:上海市民对乡音的亲切之感和维护之情,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向心力。
向心力固然是一种正能量,可是它背后隐藏的兼具学术和文化价值的吴方言、上海话日现颓势的表现却不容忽视——本市初中以下的学生,多数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而且年级越低越不会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沪剧,在招生时报名者寥寥,而这寥寥中能说得一口纯正沪语的报名者更是几近绝迹。而近二三十年来上海城市规模迅速扩张,户籍制度不断放宽,外来人口日益增多,也直接造成了本地方言被逐渐稀释和蚕食的现况。
对于这个现象,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戏教授罗怀臻一语指出其弊:“上海最显著的文化标志就是以沪语方言为支撑的地域文化,比如沪剧、滑稽戏、说唱和评弹,这是对一个城市文化气质、文化传统、文化基因的识别。这些民间地方艺术呈现出上海的文化表情和文化声音,传递出上海的文化气质和文化风情。如果到了上海听不到上海话,这会让一个地方失去存在感。”
罗怀臻说,上海过去一直被称为是“文化大码头”,政府和市民都以此为荣,然而我们对于“码头”二字却存在着某种误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只理解了一半——但凡有历史积淀的码头,上面总有自己的老字号,不全是出租柜台;即便是供“百花齐放”的地方,也会有独属于它自己的可以与“百花”媲美斗艳的地域特色产品。成熟的文化交流码头,也必然是文化滋生的源头。否则,过于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过于强调文化的国际化和标准化,本土文化就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被忽略,最显著表现为现在上海的孩子正逐渐丧失沪语表达的能力。“早年在上海街头巷尾能感受到的那种城市气息已经越来越淡薄了,曾经夹杂着苏北腔、宁波腔的上海闲话如今也不大能听到了。”罗怀臻说起这些很是惋惜,“毕竟地方特色是建立在地方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地方和民族的艺术,两者缺一不可。”
为此,罗怀臻曾不止一次地呼吁上海的电视台、电台重视开辟沪语频道、频率或栏目——其实它们中的很多原本就是存在的——但他更想引起正视的是,在这些现存的沪语节目背后,沪语方言被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格调?“我们现在很容易把沪语节目做得很市井,很嘈杂,甚至有走向低俗的趋势。久而久之,美妙的沪语表情就可能被扭曲被糟蹋。”罗怀臻对此有些痛心,“沪语难道只适合用来吵架,用来家长里短么?沪语怎么就不能用来读书、念诗、播报新闻,用来做高雅的交谈呢?”“上海格调”不应该被某些人或是某些模式所定型,它不仅仅可以用来道家长里短或是市井故事,更应该被用来展示和传达高尚的“上海精神”。在这一点上,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无疑是近期做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不仅够格成为上海文化“码头”上夺人耳目的一件展品,更是完全有资格成为多姿多彩的海派文化中的一支“源头”。
然而,肯定之余,罗怀臻对剧组和导演亦有更多寄望:“苛刻点说,这部戏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不可谓无。比如,几位主演的功力自然是好的,但有些配角,如果放到其它说普通话的高水平的话剧剧组里,可能还是不够格的——只因为在这样一个沪语话剧的氛围和语境里,他们才发挥得如此自然如此鲜活。”罗怀臻毫不讳言地表示,这部戏的成功,必将以“沪语话剧”之名、在海派文化的年鉴上留下一页里程碑式的纪录。然而如此盛名之下,导演究竟又具备了多少的文化自觉呢?——当然,有好的艺术敏感也是自身能力的一部分,但既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再能有意识地助以“文化自觉”,相信这部作品和导演本人都能走得更远。
什么是叫“文化自觉”?罗怀臻对此有自己的理论:它应当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乃至每个文化创造者、享用者共有的自觉。自觉意识源于自省意识,文化自觉依赖于反躬自省:我们能否改变互相推诿的状态,而变成自我发问,也就是说作为文化的创造者,我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怎样做?埋怨或是推诿只会让人心浮气躁,而自省则会促使人清醒,紧迫,担当。我们在建设着怎样的文化?我们的管理在催生着怎样的文化?我们享用和欣赏的文化是否有益于心灵的健康?我们的文化还可以在怎样的生态中继续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了自觉意识、反省意识、提升意识,那么整体的文化就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整个城市的文化品格就会随之提升,而“上海格调”也会重现它的非凡魅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