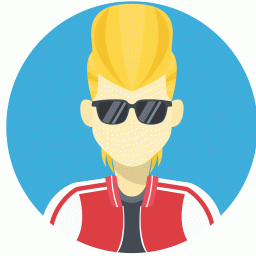于蓝拜访记
时间:2022-10-14 12:30:18
2013年春节,我在老家接到剧院老演员宋戈的电话:“于蓝拿到《唯有赤子心》的书了,跟我说,‘孙维世研讨会怎么不通知我呢,我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啊!’……这样吧,你回来了我带你去见于蓝。”
3月的京城春寒料峭,多霾,宋戈老师也已80高龄,我有些担心老人不便出行,而就在我们约定的那个日子,无风无霾,还现出了蓝天白云。下午三点多,我与宋戈走进了西土城路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宿舍院。院子安静整洁,电梯里遇到的老人们都觉眼熟,孩提时所看电影里的形象呼之欲出。
于蓝在我的记忆中是母亲念及的江姐,机智果敢的女英雄。门铃响后,听到人问“谁啊?”“我是宋戈,和您约好啦!”门开了,“哦,是你呀,我都不记得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笑着招呼道。她显得有些瘦小,怎么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挺拔的“江姐”呢?想想老人今年已经92岁了,与孙维世同龄呢。
于蓝不让我扶,自己推着轮椅把手往前走,“70岁还没事,到80岁觉得不行了,85岁以后费劲,没重心,现在我推着这个每天在走廊里走十圈。”
来到一个房间,桌上摆着各种水果。她把纸盒饮料递给我们,又把牙签插在草莓上,“来,喝水,吃点水果。”她问宋戈,“你多大了?看着像60多呢。”宋戈笑着摇头。“来,把你的年龄写下来,现在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她拿出一本书打开来,是《苦乐无边谈人生》,“现在它成了我的字典了。你们要问什么?我现在都不接受采访了,要不是维世……” 之前,《国话研究》编辑部已把孙维世的纪念图书送给她,我这次上门,是想进一步求证书中与她相关的部分。
“我呀,在延安时经历过‘整风’,那时候弄错了一些人,后来在的时候我就很清醒,看出了不对。我想等时间过去一段,这些会翻过来。可是维世死得很惨,她很高尚,很英烈。她要活着,能做多少事啊……”于蓝开门见山,动情地对我们说。
“您是什么时候和孙维世合作的呢?我们书上写的是1957年。”
“比那还要早啊,我在东北文工团时,孙维世就喜欢我。1950年,她让我到北京来,和石羽一起演《万尼亚舅舅》。我俩是严肃演法,根本不行。她不谈理论,只讲求怎么去做。我和石羽都是老实人,视像里没有啊,俄罗斯那种风情万种的妇女,我也没见过……”说到这里,她哈哈地笑起来,“这个戏没排成。后来列斯里来了,冀淑平、金山才演出‘’的样子。”原来,于蓝最初与孙维世的合作遇到过难题。也许是从那时起,孙维世意识到,演员扮演的角色要与自身的条件相符,才能激发出她们的创造力,那个角色并不适合于蓝。
我环顾屋中,发现玻璃柜中一张于蓝年轻时的电影剧照,“好漂亮!”
“那是演《翠岗红旗》的时候,那个编剧看过我演的很多话剧,向张骏祥推荐我演这个角色。”
1951年,这部表现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等待红军丈夫归来所经历苦难的电影,在当时的革命题材影片中显得别具一格,于蓝扮演的向五儿质朴感人。当时中国电影代表团带这部片子参加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起初,电影节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但某位有“左”的思想的领导认为,片中的女主人公只是一个等待胜利的女性形象,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极力反对,后来改为接受最佳摄影奖。这是中国电影摄影首次受到世界影坛的褒奖,从这张剧照上也可得见当时摄影技术的精湛。
“您的声音好响亮啊,还很清楚!”于蓝的耳朵不太好,我蹲下来对她大声说。
她马上高兴地回答:“那是当话剧演员锻炼的啊,做演员要身体好啊!”
“您那时候知道斯坦尼吗?”
“知道啊,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学到表演的科学的方法,我们都非常重视斯坦尼,那时候我们看的是章泯的书……”
“是郑君里、章泯合译的《演员自我修养》,1942年重庆新知书店出版的那个?那是最早的版本了。”
“对啊,如饥似渴,可认真啦,可是不懂啊!”于蓝又笑起来,“知道那个目标,但是怎么走到那一步,不知道,行动起来相反,变成表演情绪了。大家都按这个去挤情绪,演情绪。后来到1954年,我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训练班,库里涅夫总是说,‘光靠情绪不行,必须在动作中有愿望、目的,才能产生情绪。’我终于明白了。”
“您从表训班毕业后就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去了吧,演了孙维世导演的《同甘共苦》。”“还有《百丑图》和《小市民》。”宋戈补充说,“《同甘共苦》可受欢迎了,那时候的票价是两毛钱,演出前一天票就被抢光了。”
“可是后来,您又去演电影了。您什么时候离开话剧院的呢?”
“我1952年调到青艺,后来从中戏学习出来到了实验话剧院。怎么演上电影的呢?那是舒绣文生病,张水华导演找我去试镜,一下子就通过了,拍了《革命家庭》。我在外面拍电影的时候,话剧院演出的节目单上总写A组于蓝,B组某某,但是我人又不在,心里觉得不安,1962年就调到北影厂了,后来又拍了《烈火中永生》。”
于蓝在《革命家庭》中扮演了一个嫁给革命者的农家姑娘,在丈夫和儿子相继被杀害的过程中慢慢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最后赶赴革命圣地延安。而《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则是一位经历了严酷斗争的非常成熟的女英雄。1961年,于蓝因《革命家庭》荣获了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至于《烈火中永生》中于蓝与赵丹两人挺拔屹立的身姿则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最为经典的电影形象而深入人心。今天的演员很难想象,为了拍摄这两部电影,作为女主演的于蓝对角色是多么投入,做了多少前期的案头准备,仅采访小说《红岩》烈士原型家属的笔记就达到20万字。不过,让今人更加难以理解的是,于蓝对角色的钟情与准确演绎其实来源于她个人的革命之路。
“我两岁时就离开家乡岫岩到哈尔滨了,八岁时妈妈去世,父亲就带着我到了北平,所以你听我的普通话还可以吧……”
“刚到时还有点东北味儿,后来就没了。”宋戈说。
于蓝17岁时两次从家中逃出,第一次被日本宪兵抓住,第二次终于穿越日军的封锁,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达延安。
“那时候我急着要到延安去,走之前改的名,是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改的,她说,‘你去延安,前途广阔,那就是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啊,你就叫于蓝吧。”
说着这些时,于蓝眼神明亮,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这个名字带给了于蓝演艺事业的坦途。也正是《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这两部电影,奠定了于蓝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1962年,她被评为“中国22大影星之一”。但更令人敬重的是,“”之后,于蓝以60岁高龄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那时候她已经经历了癌症的病痛折磨并成功地走了出来。
“我的丈夫田方相信党的事业一定能成功,但他害了病,得了胆管癌,我对癌症的知识就是从那会儿得来的,所以我后来患了乳腺癌,一点也不害怕,先拿掉了一个,后来自己又主动拿掉了另一个,拿掉了就好了。”
望着于蓝老师,我从眼前这个瘦小的身躯里看到了她内里蕴蓄的强大的力量。丈夫离去,癌症困扰,都未能改变一个女人对事业的坚忍与执著、对生活的承受与担当。于蓝直到80岁才正式退休,“我做厂长,是按做小组长的方式去工作,搞好融合。”
“你还当过话剧院的书记,你没整过人。”宋戈补充说。
一番交谈,一个多小时已经不知不觉地过去。合影之后,于蓝老师推着轮椅,执意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回首间,我看到她的眼神还像年轻时一样坚定与刚毅,又有种母性的慈祥,心里想:要是孙维世也活到今天,我们该有多少感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