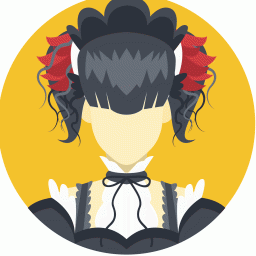理性――到达理想的通途
时间:2022-08-03 12:32:41
在李普曼于1922年写就的《公众舆论》中,“公众”成为这位天才学者在论述中无可回避的一个群体,他们无处不在,是成见的发出者,民主的参与者,公意的形成者,媒体的争取者,但是也因每个个体自身的缺陷和联结成群体后的天然特性使这个群体有着巨大的局限性,这直接导致了所谓“公众舆论”或者说“公共意见”的无数可能性。
在这本300页的书中,李普曼以一个天才的头脑、笔触、思想和见识在写作,广涉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仅是这本书的结构与论述思维就令人觉得高山仰止,笔者试图沿着残存的感知谈谈此书中的几个问题。
一、公众的局限
在《公众舆论》的前半部分,李普曼不遗余力地发现着公众自身的局限性与现实的复杂性,比如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决定的社会交往范围,比如每个个体的时间分配,比如我们的立场和自尊、盲点和期望。这些个体的局限性加上社会长期形成的积习的成见系统,使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用“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去填补剩下的画面”,①即李普曼在一开始就阐明了的“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②
当然这早就被先贤柏拉图说明过了,那个“洞中人”的寓言或者是预言嘲讽着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些影子,看不到火焰与那堵墙上的人,只是天真地对世界进行最大的虚构。只是,故事到李普曼这里变成了舞台、舞台形象的比喻,他说“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③
根据李普曼的论述,笔者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最简单层面上简化为下面的图示:
也就是说,经过层层传递,如果事实在本初是菱形,那么到最后形成公众舆论时早已变成了六边形,不复原有的面貌。
二、拟态环境与议程设置
在上述对舞台形象的构建中,李普曼对媒体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首先他在第四章《时间与注意力》中用了本书中并不多见的大量的数字来证实每个个体在获取舆论资料时所用的巨大时间,而耗费这些时间的主要方式却是通过媒体(当时还主要是报纸),这个推导的结论即是人们每天在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
据此,李普曼得出在当时应是颇为震惊的结论:“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也就是媒体直接构成人们脑中的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对于大众传播的本质,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新闻机构)能够记录的通常只是由于制度的运转而被它记录下的东西。其余的便都是观点和见解,而且随着世事变迁、自我意识和意气用事而起伏不定。”④这无疑最残酷地将此书写成的前一段时代里以杜威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们,对媒体作用的大肆吹捧和无限期望击得粉碎,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残酷的本质往往是因其正确真实。
这个有着数十年记者生涯,且在一战时参加过克里尔委员会的多面学者坚持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一回事,而且必须清楚地区分”,⑤但是一方面他希望新闻能够客观地探求世界真相,认同媒体和新闻在现代社会的崇高价值,另一方面却在此书的后半部分中大谈拟态环境对于公众,对于成见的宣传和控制。
这就涉及了传播学中的另一个经典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虽然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表面上并未得出确切的结论来发展成一个理论,但是诸多资料中都将“议程设置”的父亲寻到了李普曼身上。的确,李普曼在对于大众传播的拟态环境构建、其在民主中的运用、兴趣的建立和成见的屏蔽等诸多问题的论述中,“议程设置”这几个字已经呼之欲出。直至40年后科恩对于“怎样想”和“想什么”进行论证,而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才将“议程设置”命名,后人才惊觉又犯了那个天才所说的“先定义后理解”的毛病,还好,求本溯源,又找回了这里。
笔者认为,单是新闻本身距离真相有多远其实并不是核心问题,媒体到底如何设置议程构建环境也不是最重要,毕竟舞台形象再美再不真实也不过是一场喧嚷的大戏,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舞台的那些观众,因为他们依照着那个舞台,却在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正如复旦大学传播学教授黄旦先生所说:“图像是虚拟的,反应却是千真万确的。”⑥这也是李普曼最终的落脚点:理性。
三、回归理性
李普曼在最后一章《诉诸理性》的开头部分用令人迷恋的语气写道:“本书的结尾我曾几易其稿。每一次都脱不开最后章节的这一定数――所有观念似乎都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作者念念不忘的所有谜团都已解开。在政治学里,主人公今后不会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也不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局。”
他说:“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思维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他像自己描述的柏拉图那样,在开始总结的时候也近乎怯场地说:“我们可以在某种直觉中树立对理性的信念。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为理性开辟一席之地。”
因为说得太精彩,除了一直引用我们似乎不能多言。但是,理性,确实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最佳武器。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中早已指出,当个人陷入群体中,理性会弱化甚至湮灭,变得易受感染和挑拨,没有思想,只有口号。那么“公众舆论”的最大挑战就是一个具有“乌合之众”潜质的群体聚集,面对敏感议题,依靠与真相相距甚远的介质,如何能做出最理性的反应?
在精彩的最后一章收尾后,《公众舆论》前面的论述似乎都已掩埋在记忆深处,笔者一厢情愿地将这本书简化为“公众舆论”如何达到理性的彼岸,而大众传播、民主等全部都是渡船。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继续以媒体为主体来探讨问题,而是从公众出发,回到最古老的智者那里,向他们借取理性的火把,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公众的理性化选择,是媒体文明、政治民主的起点和回归。
lippman这个名字里都带有“嘴”的人以一个文人的语言,一个学者的学识,一个辩者的思维著就了这本书,他是一个天才。
注释:
①~⑤沃尔特・李普曼[美]著:《公众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⑥黄旦:《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新闻记者》,2005,(1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