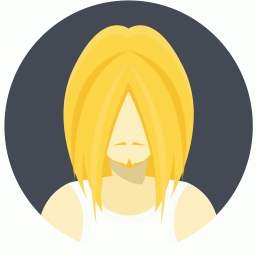民间及延伸空间在中国电影中的情绪表达
时间:2022-09-13 12:04:30

摘要 基于城市、乡土空间表象及其意义所指的不确定性,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乡土或城市都不足以独自表达中国遭遇现代性的体验。与此相关,近期的中国电影普遍以尘世关切的民间视野,表达转型时期独特的情绪体验。
关键词 民间 情绪表达 转型 中国电影
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影像世界,关于城市或乡土的空间表象及其意义所指并不总那么明确。乡土或城市都不足以独自表达中国遭遇现代性的体验,那么在民间层面所呈现的情感体验与空间差异反而更能显现时间与历史的绵延性。在近期的电影创作中,包括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杨亚洲的《泥鳅也是鱼》以及哈斯朝鲁的《剃头匠》,普遍从尘世关切的平民视角出发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疑惑和伤感,这也成为转型社会复杂性与艰难性的最佳情绪表达。
面对行将消失的一种文化或者生活方式。创作者用镜头“雕刻时光”,从而使民间及其延伸空间中的风物想象性地实现了与时间抗衡的神话。在一期访谈节目中,贾樟柯称“抢时间拍摄跟消失的城市赛跑”。之所以将影片定位于“寻找”,很大程度上基于那些逐渐失落的东西,包括古老的县城、淹没在水下的古迹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和事。与烟、酒、糖、茶四个物质的标题结构形成对照的,既有被淘汰的计划经济,也有被遗弃的文化生态。遗忘通过不断变化的水位线数字得到证明,最令人心悸的场景则定格在废墟墙壁上的奖状、涂鸦、照片上,作为存在的表征,它们代表民间立场的日常生活和市民生活,穿着古怪隔离服的工作人员对这个空间消毒,意味着这些生活的静物不但被遗忘,甚至被销毁。
这种被遗忘的焦虑同样体现在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中。一家外国媒体评价王全安展示了一些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快要消失的东西:蒙古牧羊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在这片草原消失之前,王全安通过强调一个女人的生存压力来纪录严酷的生态环境。虽然从剧情上来看,图雅“嫁夫养夫”的荒诞行为严重违背了文明社会的伦理秩序,但某种程度上,图雅连同她所在的空间――退化的草原一起。呈现出某种特定人文生态以及生存态度的顽强与韧性。可以断定,对侵害草原生态的元凶――过度的工业开发导演是十分愤怒的,因此城市等一切与现代化/工业化有关的场景几乎在空间呈现上缺席。让图雅浑身不自在的宾馆豪华大床以及陷入草原土坑的奔驰车,均暗示了宝力格无法获得图雅的失败结局。卖掉羊群买大卡车的森格也注定会被的老婆抛弃。不同于现代工业的冰冷异化,乡土系于某种稳定的价值感情。在影片中,乡土性意象化为一口维系生命和情感的水井。通过打井,图雅失去/获得生理/精神意义上的丈夫,尽管是两个丈夫。对于生存恐惧达到极限的图雅来说,只有在生死于斯的故土草原上,“嫁夫养夫”才能得到宽容和认可。然而即便在乡土文化包容下顺利地穿上了嫁衣,图雅依然遭到现代文明法则的惩罚――在两位丈夫和两个家庭孩子的厮打中,流下了心酸的眼泪。
在上述的影片中非职业演员的普遍介入,在纪实层面和民间层面均对影片的生成意义产生独特的效果。“非职业”以民间的身份表达对现实和世俗的情感认同,从而彰显“面孔”的力量。与《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对人与空间不确定关系以及传统空间被遗落的焦虑不同,《剃头匠》将一个跨越世纪的老手艺人的面孔指涉为老北京的视觉表征。作为传统的表征,他独立呈现出一股遗世的古旧风格,拒不接受外在环境的挤压,现代性元素几乎无法进入他的生活。因此围绕着他的鼓楼、街道、胡同、四合院以及剃头、爆肚等老北京风物的展现,就同贾樟柯电影中城乡交叉身份模糊的县城严格地区分开来。在空间层面,作者以立交桥、摩天大厦、地铁为表征的现代北京与以四合院、茶楼、胡同为表征的老北京进行视觉对抗。在现实层面,则处处以剃头匠敬大爷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进行观念对抗。那只总是慢五分钟的台式座钟在老钟表店亨得利遭遇电子表和石英钟,得到无法修复的拒绝:敬大爷与老友打麻将时黑白电视中出现的泳装模特和去皱广告,表达色调与时代错置的间离。当然,影片并没有刻意去强调“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是通过敬大爷那张被岁月写满了故事的脸来展现老北京独有的精、气、神。但是与文化传统的被遗忘不同,死亡意味着终结,“到底伴随着死亡所逝去的一个年代、一段历史、一座城市,它内在的、更深厚的东西是什么?”面对追问,影片只能选择在时间的消逝中等候死亡却不呈现死亡的结局。
相较而言,《泥鳅也是鱼》中的民间元素密度虽高但质地轻薄,虽然影片的主体角色构成为清一色的民工,空间场景也大多局限在民工施工、生活的场所。但是与《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剃头匠》中虽然受到城市,现代化/工业化诸多元素影响但依然适度保持人文景观的原生状态不同,片中乡土气息的发散只局限于狭窄的生存夹缝,且带有相当程度的压抑。压抑首先表现在人物所处的空间。影片一开场即是光线晦暗拥挤脏乱的民工车厢,晃动的机位、混乱的构图与粗劣低俗的黄色段子组合的视听画面,将社会底层不被城市法则同化/接纳的压抑转化为生理性调侃。而男泥鳅与女泥鳅的相识,是在狭窄的座位下,没有任何情感铺垫,一遭遇就是裸的性骚扰。随后的剧情空间多是在拆迁场地、铁轨旁的废弃民房、肮脏的下水管道中铺展,很难在画面中找到豪华现代的城市景观。与城市的交流,也仅局限于在街头烧纸遭到居委会大妈围剿、坐公交车不买票被售票员谩骂、当保姆被教授女儿“调教”以及被包工头赖账并遭受人格侮辱。片中唯一一次民间色彩的野性张扬则是在一个大俯拍镜头下展现民工集体露天裸澡并大唱“骚歌”,这种舒张呈现为视觉上的拥挤和难登大雅,依然指向压抑。在颇诗意的一个空镜头中,古旧的寺庙檐角高高升向湛蓝的天空。画外是男女泥鳅的呢喃情话。在男泥鳅死后,女泥鳅回乡时这个镜头再度出现。来自城市的创伤与回归乡土的念想在民间的伤感中得以缝合。
选择民间及其情感空间而非“都市,乡土”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来表达转型时期的社会情绪,几乎成为新千年中国青年导演影像陈述的公共命题。带着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的阵痛,他们试图通过民间的温情来填补城市与乡土之间的裂隙。尽管二者之间总是保持着难以消弭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