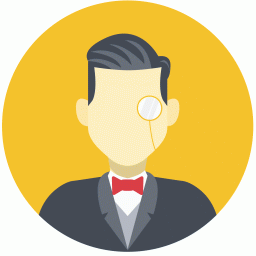“艺术的忠臣”闻一多
时间:2022-08-20 03:52:38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最为人们所了解的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人骨气的“拍案而起,横眉怒对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闻一多。为了追求民主和真理,1946年闻一多牺牲在的枪口下。他47年的生命,始终贯串彰显着同一个追求――美,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审美的人生。他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同时还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但早年在美国学习油画艺术,而且还两度在北京国立艺专任教务长兼油画系主任。他进行艺术创作,发表美术评论,设计书籍装帧,甚至还热心参与了戏剧美术设计,并在书法和篆刻领域里留下了足迹。他在诗集《红烛》中歌颂过“艺术的忠臣”,而他自己就是十分忠实于艺术的。
臧克家曾说过:“作为美术家、诗人、学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与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卓然独立的统一体。”吴晗也说:“一多一生在追求美,不只是形式上的美,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善。早年搞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有变化,目标却从来没有变。”
一
绘画是闻一多最早选择的专业,他留学国外时的志愿就是学画。按闻一多自己的说法:“绘画本来是我的原配夫人。”可见闻一多一开始是准备将绘画专业作为毕生理想之追求和终身职业的。
闻一多自幼喜欢绘画,在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读书期间,就对美术有广泛的兴趣。教美术的美籍老师很看重他的才能,更激发了他的兴趣。他参加了美术教师组织的“校外写生团”,曾经“以图画冠全级,奖景画一幅”。他担任过《清华学报》的美术副编辑。他还曾专门研究过北京各种书刊封面设计,写了一篇《出版物的封面》,对封面美术进行评价。还写过一篇《建设的美术》。早在1919年,20岁的闻一多已醒悟到“人之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观念,提倡美术,就是尊重人格”。同年秋,他与同班同学杨廷宝、吴泽霖等发起成立美术社,社员多达50多人,除课余练习绘画创作外,还经常作有关西方著名画家、雕塑家及其作品的介绍。
《梦笔生花》是闻一多1921年毕业前夕为清华年刊设计的12幅专栏题图画之一。这是借李白少年时梦见笔头生花,于是天才瞻逸而闻名天下的典故,表现清华当年那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幻想走上社会报效国家显露才华的抱负。画面表现在深夜的烛光下,一个姿态优美、侧靠书案熟睡的少女梦幻中笔头生花的情景。传统的线描加上大块的黑白,组成鲜明的调子,构成完美的构图。他充分运用形式美的规律,把画面营造得十分和谐。准确的人体造型、透视的运用、平面构成的运用,显示了闻一多在出国深造前已经具备的良好的西方艺术造型能力;而意境的凝练、线描的功力、装饰性手法的运用,又体现了闻一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90多年前,青年闻一多在尚未得到正规专业训练之前,不但已经掌握了中西绘画艺术语言的基本要素,而且能使西方黑白画技法(比亚兹来)与中国传统木刻版画创造性的巧妙融为一体,其和谐完美的程度,不能不令当今的读者与专家赞不绝口。
1922年,闻一多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学习西方绘画艺术。翌年他又转学到丹佛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学习美术理论和各家画法,浏览古今名画。该校美术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和她的妹妹一个教绘画,一个教理论,都很欣赏闻一多的才华,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对其创作评价很高。在一年一度的画展征画时,她俩鼓励闻一多去参加。闻一多为了参展埋头作了一个月的画,并在画展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闻一多在绘画领域下过一番功夫,但他并未在这个专业上继续发展下去。对西方美术的深入了解,使他日益觉得自己不应当做一个西方的画家,且更重要的是专凭颜色和线条已不足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闻一多要用诗、用文学来抒发自己炽热的情感。
尽管绘画后来不再是闻一多的职业和专长,但绘画对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陈梦家回忆说:“绘画是他早年选择的行业,他去国外时的志愿是学画。很快的回国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在北京美专做事,后来不干了,开始教西洋诗。在青岛的时候,我看见他画过《诗经》的画,很工整的。后来在贵州步行中用铅笔作过写生画,这些画还保存着一部分。作过一些封面设计,画过话剧的布景,这些都是很有限的。但是绘画对于他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所喜爱的颜色(黑与红)也象征着他思想情感中对立的两个倾向。”
1927年,闻一多为潘光旦所著《冯小青》一书设计了封面,并作彩色插图一幅。冯小青是我国明代一位美丽的才女,但初婚为妾,不久又被遗弃,最终抑郁而死,后葬于杭州孤山放鹤亭。闻一多的这幅插图被潘光旦命名为《对镜》。冯小青心情抑郁不得解,常临池自照对镜愁思,“罗衣压肌,镜无乾影;朝泪镜潮,夕泪镜汐”(冯小青《与杨夫人永诀书》)。闻一多画中的小青披着睡衣,左肩半露,背对观众,圆形的镜面映出她憔悴美丽的面容,散乱的鬓发、微蹙的娥眉、忧郁的眼神,作者以深深的同情,塑造了封建社会中不幸的女性形象。画面上方挂着一只鸟笼,寓意画面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对镜》既典型也成功地反映了闻一多“中西会通、古今融和”的美学理想,在中国上世纪20年代的人物画中堪称珍品,称得上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闻一多在绘画等艺术方面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920年10月,闻一多发表《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的呼声》长文,呼喊艺术“是社会的需要”,是“促进人类的友谊”、“抬高社会的程度”、“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浩劫,是由于崇拜物质文明的恶果,说明“单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在都倾向于艺术,要托庇于她的保护之下”。他想用艺术来美化、净化人类的灵魂,洗刷人们思想中的污泥浊水,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他的这种艺术救国论虽不免过于幼稚,但把艺术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艺术是改造社会的急务”,因此在选择职业时以“社会的需要为标准”,不只是为谋生找“饭碗”的个人需要为标准,而放弃对社会与人类的责任。他说:“叫一个性近艺术的,为了‘饭碗’问题,摧残他的个性,流离颠沛于科学界里,也要算天下最悲惨的一桩事了。在我个人,宁肯牺牲生命,不肯违逆个性。”这也是他留美时选择艺术这个专业的原因。
闻一多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主张艺术要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闻一多是西南联大阳光美术社的导师,当时美术社的成员赵宝熙、闻山回忆说:“除了南下途中曾画了不少速写之外,到昆明后几乎就扔了画笔,但是他鼓励我们画画,特别是画和作斗争的漫画、宣传画。他对待画的态度和诗一样,他认为绘画也不应是为画而画;他叫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画笔专涂抹‘闲情逸致’,去装点‘风雅’。……他却一再告诉我们,那些为封建士大夫消遣的中国画题材,什么‘松荫高士’,‘芭蕉仕女’等等,在今天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统统都要不得,再画这些东西,就是‘帮凶’!在绘画技法上,他告诉我们,要尽量摒弃主观虚构的东西,强调写实;他甚至把是否写实,提高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当他看到我们有人画倒毙在马路边的尸体时,他就加以肯定,说对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用画笔来控诉!”
二
青年时代的闻一多,在艺术的宫殿里流连忘返,新诗、油画、舞台美术,都曾使他倾倒。上世纪20年代,回国初期,他又对篆刻艺术着了迷,曾一度连他热爱的美术和诗都放到一边去了。1927年8月,他从南京写信给友人饶子离先生,寄去了五枚印章,并风趣地说到自己一时热衷于篆刻的情况:“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来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后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闻一多家学渊源,有深厚的古文字学的造诣,有西方美术教育的基础,早年又曾摹拟秦汉印章,中西合璧,深得篆刻艺术三味。他的篆刻能师法秦汉而又变化出新,别具匠心,活泼而有韵味,古朴而不呆滞;分朱布白,疏密有致;刀法刚劲,有笔有墨;藏锋露锋,顿挫放纵,皆能运用自如。
1944年,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生活问题,闻一多挂牌治印。学术界名流梅贻琦、蒋梦麟、朱自清等具名推荐介绍,许多人慕名前来,希望得到闻一多用钟鼎文字雕刻出来的印章,一时生意兴隆。闻一多曾笑着对朋友说:“我是个手工业劳动者。”从1944年4月起,到1946年7月15日牺牲之日止,两年多的时间里,闻一多刻了大量的图章,仅现在留在印谱上的就有400余方,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刻一方。
刻印章虽然是闻一多的“手工业”,但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当成纯粹的商品,每一方印都是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对待的。他精心设计,刻好以后又左右端详,有时刻了磨磨了刻,多次反复,直到满意为止。作为一个有素养的艺术家,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小小的印章是粗制滥造,不符合美的原则的。
闻一多为生活而治印,但治印却不是单纯为了个人生活,更不是为了名利。当时云南省代主席、“一二・一”惨案的刽子手李宗黄,有钱有势,派人送来石章一方,扬言润金从优,闻一多却一口拒绝,不买这种人的账。他宁肯饿死,也不肯把艺术、把劳动成果给予这种靠贪污或杀人起家,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权贵。比起有些人的一味钻营、屈从的作风来,闻一多更显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尽管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清苦,闻一多还常常资助因穷困而付不出伙食费的学生。
闻一多热爱艺术,尤重友情,他常常为朋友们欣然命笔。他为吴晗篆书:“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他给华罗庚印章边款上刻过:“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他为学生题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也常常为朋友们欣然奏刀,对一些青年穷苦学生,他更是有求必应。
晚年的闻一多自觉地把一切服从革命事业――包括他的篆刻。他自觉地在困难的条件下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他为自己用钟鼎文刻了“叛徒”二字,表明自己做旧世界的叛徒、投身革命事业的决心。他用这种信念鼓舞同志,教育青年。当联大开始复员时,新诗社中一位他很得意的学生黄海到家里辞行,闻一多留他在家里一起吃了晚饭,师生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临别前,闻一多又提笔写下了下面的话:“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最后,他蘸了通红的印泥,有力地按下了那枚小小的“叛徒”印章。
闻一多有许多印章更是直接为民主事业服务的。为了有更多的言论阵地,闻一多和他的战友们决定成立一个“时代评论社”,为了争取时间,能在向当局报批的同时就出刊,需要先刻一枚公章。闻一多二话没说,连夜以隶书入印,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在这方寿山石章的一侧,用铁笔写着:“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制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时代评论》周刊对于揭露反动派,唤起人们投入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闻一多多才多艺,也十分热衷于戏剧活动。有人评价说:“解放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两所大学,两位大师,在中国戏剧运动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两所大学是南开和清华,两位大师就是曹禺和闻一多。”可见闻一多在戏剧运动方面的成就了。
1912年冬,闻一多进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看到校内外掀起的一股诋毁革命、反对共和的逆流,十分气愤。他和几位同班好友自编自演了一幕独幕新剧《革命党》,在全校演出。这个戏是以他耳闻目睹武昌起义真实情景为题材,描述湖北都督瑞在事变前夕镇压革命党人,后来革命党人起义事起他狼狈逃窜的故事。闻一多在这出戏中饰演“革命党人”,塑造了一个在反动势力的镇压面前,横眉冷对、威武不屈的义士形象。这个戏在全校演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获得第二名。
此后闻一多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几乎连年演出。1913年,他在《打城隍》一剧中饰差役,翌年在《两仆计》中饰律师,在《兰言》一剧中扮演老母。1916年2月,为创办贫民小学筹款,清华学生演出洪深编的《卖梨人》和《贫民惨剧》,后者描写贫富不均、贫民受压迫的惨状,筹得的款项建成了成府小学。同年10月在全校会演中,闻一多所在班表演《蓬莱会》,他在其中扮演了一只驴,“振耳长鸣,众皆失笑”。这次演出获全校第一名。1917年为中国运动员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募集捐款,闻一多参加演出《都在我》,被评为“化装精工,表演细致,极淋漓曲折之妙”。他演出《可以风》时也反响强烈,时人评述:“剧中情节新奇,而演者又素以艺术著,摹情写景,大有可观。”1918年12月演出《鸳鸯仇》等,1919年演出以秋瑾革命经历为主题的《巾帼剑》以及《是可忍》、《我先死》、《得其所哉》等四剧。据当时人描述:“清华为爱国运动募集款项,曾由闻一多与高班罗发组同学共编一部五幕新话剧,当演到悲伤最高潮处,声泪俱下,博得台下观众不少同情之泪。于是(演主角的)梅僧与一多之名遍传遐迩。”
当年清华园内的戏剧活动非常蓬勃,清华学生还成立了“游艺社”(后改名为“新剧社”),闻一多任副社长。学校的戏剧活动,闻一多无不参加。他或任编导,或任演员,或任舞台设计,或作组织工作,有时兼任教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数月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
在赴美留学期间,闻一多结识了专攻戏剧艺术的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1924年中秋节后,他们曾排演洪深编的《牛郎织女》,接着又筹备演出余上沅编的《杨贵妃》。闻一多等负责译成英文。至于化装布景当然也是闻一多的分内事。闻一多“戏兴很高”,“忙得头昏脑乱”,化装布景的图案画出来了,还要动手制作。同年底,《杨贵妃》在美国纽约公演,大获成功。闻一多几个人大受鼓舞,决定回国开展“国剧运动”。
抗战爆发以后,闻一多积极参加战时的宣传教育活动。他本来很长时间以来很少参加戏剧运动的,但仍然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参加了话剧《祖国》和《原野》等剧的演出工作。《祖国》多幕话剧是描写在日军占领下某城一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与旧日宿怨,和学生、工人一起抗击敌人,最后为国壮烈牺牲。此剧于1939年2月在昆明演出,激起同仇敌忾,在场观众齐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云南日报》评述说:“诗人闻一多设计的布景也取得很好的效果。”“特别配以灯光,用黄色表现第一幕中的忠勇,用蓝色表现第四幕的悲惨,把感情突出了。”同样获得极大成功的《原野》的演出,也是由闻一多担任舞台和服装设计的。曹禺曾说:“闻先生的美术设计增强了《原野》的悲剧气氛,是对《原野》主题的最好诠释。”在戏剧活动中,闻一多的诗人、画家和舞台设计师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