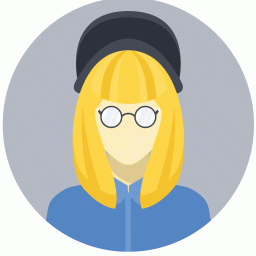美国类型电影观念中国化接受中的变异的策略应对
时间:2022-09-27 07:37:30

类型电影产生于美国、繁荣于美国,影响波及全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中国电影创作及研究界也深受美国类型电影观念的影响——创作界开始自觉地模仿美国类型电影的模式拍片,学术界逐步展开了系统研究。可以说,国内类型电影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类型电影观念密不可分,而且理论与创作互相比照,形成了中国类型电影发展的特定语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类型电影甚至被看作发展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1]。然而,引进美国类型电影观念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类型片创作普遍来说不成熟,创新意识和能力薄弱,整体制作水平也不高,而这恰恰也正是目前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难以扩展的根本原因”[2],指望类型电影拯救中国电影的预期目标显然并没有实现。是类型电影观念本身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还是我们念错了经;对类型电影的学习与借鉴过程中出了差错?对于美国类型电影,众口一词的肯定语境阻碍了我们对中国电影存在的更深层问题的思考,也不利于我们正确吸收美国类型电影观念的精华。
本文是关于美国类型电影研究系列的一部分,重点考察美国类型电影观念及实践中国化接受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变异。
先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美国类型电影观念中国化过程首先体现在电影理论界,即使20世纪80年代创作过一些所谓的类型电影,基本上也是观念先行的产物,因此,本文将主要以中国类型电影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兼顾中国本土类型电影的实际创作进行评述。二是本文所谓“变异”,主要是指美国类型电影观念中国化接受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及误区(这些问题及误区与“文化折扣”、本土化、民族化的本义都没有任何关联),对中国类型电影发展与研究具有负面效应。
一、接受的过程
美国类型电影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时间并不长,共计二十多年。为了描述的方便,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觉醒期(1986-1994年)
电影观众数量急剧下滑、电影市场萎缩直接促进了中国类型电影观念的诞生。自1979年的高峰值以后,中国内地电影观众数量以年均6%的速度下滑,到了1985年跌至谷底,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国产电影市场的第一次危机。在现实的危机面前,电影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产业化比较发达的美国电影,试图从美国电影产业的繁荣中寻觅拯救中国电影产业的一剂良方。在当时,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禁锢与偏见,美国电影(或者说好莱坞电影)是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但对于急于解决观众危机、票房危机的中国电影界来说,美国电影的产业化、娱乐化、类型化等特征还是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关注。
第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86年初,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招收的一批研究生提出要“重新认识好莱坞”,“要研究类型电影”[3],标志中国类型电影意识的正式觉醒。紧接着,《电影创作》杂志1987年1月号、2月号连续开展关于中国电影危机与出路的讨论,表明了中国电影界强烈的危机感及寻求突围的迫切心情。《当代电影》杂志于1987年第1、2、3期连续刊登《对话:娱乐片》专题讨论。1988年12月初,《当代电影》编辑部又专门召开“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上述关于娱乐片的对话,虽然主要探讨的是电影的娱乐属性、娱乐电影类型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为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壮大扫清了某些思想上的障碍。因为娱乐性、商业性正是类型电影的基本元素,而这些特点在强调政治性、教育性的话语背景下曾经都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借着娱乐片的讨论,饶曙光提出“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有一个树立类型观念和类型意识的问题”[4],陈怀恺也主张多元化、强调类型化[5]。有人则干脆提出“娱乐影片的规范学术称呼乃是‘类型电影’”[6]。在这样的背景下,郝建与杨勇于1988年联名发表了《类型电影和大众心理模式》一文,文章提出:“类型化现象在中国影坛早有端倪,近年来颇有大量摄制的趋势,有些理论家们将这种影片打入另册算作低档次,但深入探讨这一电影现象的产生及其规律性是完全必要的。”[7]该文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篇研究类型电影的学术文章”,标志着中国内地在理论层面正式开展对类型电影的学术研究。同一年,宫宇和祭光合作撰文,提出要为类型电影“正名”[8]。期间,两篇较早的关于类型电影的译文非常引人注目,其中美国学者查·阿尔特曼的《类型片刍议》一文的学术影响非常惊人。
几乎与理论上的萌芽同步,创作界也带着初步的自觉意识拍摄了一些类型片。从1985年到1989年间,以滕文骥的《大明星》和《飓风行动》、黄蜀芹的《超国界行动》、张子恩的《神鞭》、吴贻弓与张建亚合导的《少爷的磨难》、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产电影,与仍然占据主流话语的“探索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少影片得到了票房的好成绩。90年代初,随着管理层对娱乐片态度的转变及整个社会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铺开,“类型电影在国内院线中的生存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类型电影的制作也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阶段”[9],然而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发展却随着1995年好莱坞电影正式进军中国市场带来的冲击戛然而止。
这一时期总体特征是理论先导,创作紧随,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效应非常明显。中国类型电影观念是以借鉴与模仿为主,类型片的创作显得十分稚嫩,类型电影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二)震荡期(1995-2001年)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类型电影观念的觉醒,还属于一种“在真正的跨国资本与全球化全面展开之前,来自中国本土的对于它的想象”[9](68),那么自1995年开始,中国电影亲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正面来袭。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市场急剧萎缩,据《中国电影市场》统计的数字:1979年,全国电影观众人次293亿,而到1994年下降到3亿。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电影市场,1994年广电部电影局批复中影公司每年可以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1995年7部进口大片占据了中国电影票房的80%。与此同时,国产电影数量急剧下滑,据相关资料显示,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电影产量开始明显减少,1997年产量为88部,比90年代中国电影的平均年产量低约30%,而1998年这种负增长的趋势有增无减,审查通过的电影数量到12月仅有四十多部。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大片以1/3的放映时间攫取了2/3的票房。
事实胜于雄辩,进口大片的巨大票房号召力以感性形式为中国电影人补了一课,中国电影界不再纠结于类型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意识[第一 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和论文,欢迎光临]形态性等抽象的辩论,摆在人们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类型电影的问题,而是如何拍好中国本土类型电影的问题。在这方面,冯小刚的贺岁片成了最为成功的尝试。从1998年的《甲方乙方》、1999年的《不见不散》、2000年的《没完没了》,到2001年的《大腕》,这些影片都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冯氏贺岁电影成为中国本土类型电影的一个醒目标志,也成为与进口大片争夺国内电影市场的有力武器。
这一时期的突出态势是创作先行,理论强化。进口大片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类型电影观念的更新,虽然这一时期类型电影研究成果较前一时期并无明显扩大,但由于理论总结本身具有相对滞后性,因此并不能低估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类型电影观念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较少讨论发展类型电影在娱乐性、商业性、艺术性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而更多地是从正面直接探讨美国类型电影的叙事规律及研究方法,较前一时期更为接近类型电影本身。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亮点是出现了几篇专门探讨类型电影创作问题的论文、论着,它们是姚国强的《读解高科技类型片的声音艺术构思》(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穆德远的《美国商业类型片与电影摄影》(载《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梁明的《摄影造型与类型片》(载《当代电影》2000年第4期)及桂青山的着作《电影创作类型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王海洲的论文《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动作类型片的发展演变》(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利用类型电影理论集中探讨了一个动作片这个特定类型的发展,既有历史的细致梳理,又有客观的评价,是一篇比较有学术见地的专题论文。期间还出现了专论美国着名类型片导演的论文,其中陆川导演的《体制中的作者:新好莱坞背景下的科波技研究》(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1998年第4期及1999年第1期)采取较为辩证的立场对“体制”与“作者”这对看似矛盾的元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表明中国导演已经不再把两个方面看作是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两篇译文探讨了类型批评的方法问题,分别是T.贝沃特与T.索布夏克合作撰写的《类型批评法:程式电影分析》(载《世界电影》1997年第1期)、安·图德的《类型与批评的方法论》(载《世界电影》1998年第3期)。聂欣如、李维琨合着的《类型电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则是一部关于美国类型电影的介绍性的着作,对于普及类型电影观念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深化期(2002年至今)
2002年,是中国类型电影创作真正走入正轨的一年。张艺谋的古装大片《英雄》取得国内票房2.5亿元人民币的骄人业绩,一举超过了进口大片。而冯小刚的喜剧片《大腕》也获得了5000万的票房。这两部电影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市场化探索的初步成功,类型电影的合法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
在理论界,对类型电影的研究则向着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研究类型电影的十多部国内研究专着、译着几乎全部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成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出现了持续研究类型电影问题的多位学者。研究论文数量激增,涉及范围进一步扩大。
专门研究类型电影的着作有13本之多。郝建于2002年出版的专着《影视类型学》被称为是大陆第一本电影电视类型学研究的专着,该书被称为内地研究类型电影的重要参考书,受到诸多引用和评论,并于2011年出版了修订版《类型电影教程》。蔡卫与游飞合着的《美国电影研究》(2004)、沈国芳的《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2005)及香港科技大学的郑树森所着《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2006)乃集中研究美国电影中的主要类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2008)则集中探讨香港类型电影。吴琼的《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2005)、田卉群《探寻:中国电影的本土化与类型化之路》(2009)及陈林侠的《中国类型电影的知识结构及其跨文化比较》(2010)都是着眼于探讨中国本土类型电影的。另外,美国学者托马斯·沙茨(Thomas Schatz)研究好莱坞类型电影的专着Hollywood Genres: Formulas,Filmmaking,and the Studio System的中文版《好莱坞类型电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9正式出版,该书几乎成了国内所有类型电影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可小觑。王志敏与陈晓云合作主编的《理论与批评:电影的类型研究》(2007)则是译文集,提供了国外十多篇类型电影特别是喜剧电影研究的中译本,对国内学者研究颇具文献价值。这一时期见证了一批学者对中国类型电影的持续关注,他们的关注跨越了不同时期,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或谈话,成为国内类型电影研究的重要代表,其中有郝建、胡克、虞吉、饶曙光、桂青山、颜纯钧、沈国芳等,余恕不一一列举。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类型电影创作及理论研究皆走向深化,但创作与理论研究两方面有渐行渐远的趋势,不像第一个时期那样互动效应明显。
二、接受中的变异
美国类型电影观念中国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忽略了两国类型电影产生、生存与发展的背景
从生成、发展的背景来看,美中两国类型电影观念有三点重要的区别:①美国类型电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们是人为的、后天的;②美国类型电影既是一种完成时态,又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存在,而中国类型电影尚处于构建中的未完成状态,将来能否建成、在何种意义上建成都是未知数。③美国类型电影虽然不乏意识形态性、艺术性,但从根本上、总体上却服从、服务于市场经济规律,而中国类型电影(商业片)虽然从形式上与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并列,但这种并列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类型电影一种特殊的生存境遇。鉴于以上原因,简单地将中国类型电影比附美国类型电影,往往会对很多问题发生误判。比如如果缺乏对类型电影发展历史过程的基本认知,则很容易忽视对类型电影深厚历史背景及其经验的认真梳理,从而以一种很轻率的态度来发展类型电影,最后只能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境地。学者饶曙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无论是电影的生产机制和消费机制,还是社会/文化语境,类型电影形成和发展的必要的土壤和条件都是不存在的。现在人们习惯上谈论的所谓反特片类型、与革命历史题材相关的各种准类型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借用‘类型电影’来尝试性描述十七年电影中的一些现象和特点,与西方经典电影理论话语中的类型电影存在有相当大的距离和差别”[10]脱离了两国类型电影产生、生存与发展的具体背景,是很难对两国类型电影进行客观、科学的比较研究的。
(二)无限泛化类型电影概念
近年来的中国类型电影研究中,类型电影观念的无限泛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所谓的无限泛化是指将美国类型电影的几个元素抽离出来,直接用于对中国电影史的考察,从而导致对中国类型电影发展史上限的无限回溯,引起人们对中国类型电影发展阶段的误判与认识上的混乱。巴赞在研究美国西部片时曾指出:“竭力把西部片的本质归结为它所包含的任何一项表面元素都是徒劳的。同样的元素在别处也可见到,而独占这些元素的特权似乎是没有的。因此,西部片的概念应当比它的形式更丰富。莽莽荒原、纵马飞驰、持枪格斗、剽悍骁勇的男子汉,这些特点不足以界定这种电影类型或概括它的魅力。”[11]近些年来,国内有人运用美国类型电影的一些元素,去分析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认为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已经 具备了类型电影特征①,稍微保守一点的说法认为中国早期电影已经有了初步类型电影经验:“中国电影自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类型片的尝试,滑稽短片、社会片、爱情片、、稗史片、武侠片和神怪片相继推出,虽然尚未形成美国西部片那样鲜明的文化意义,但就表面形式而言,有些已可称为类型雏形。”[12]这在时间上甚至要早于典型的美国类型电影——因为普遍的看法是美国类型电影形成于大制片厂发达的三四十年代。其别令人费解的是,有人把“”和“”时期的工业题材电影也看作类型电影(“工业片”)[13]。仅仅从单个元素的简单叠加原则出发,把十七年电影甚至“”电影都算作类型电影,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运用美国类型电影观念去分析中国早期电影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忽略了类型电影起码的背景及基本内涵,只能得出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是不利于中国类型电影发展的。对此,有学者清醒地指出:“在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概念是特定的,它不是像我国学者那样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将电影做全面、简单的分类,如‘时政电影’、‘都市电影’、‘农村电影’等,而完全是出自电影工业‘标准化’、‘模式化’、‘系统化’的需求,以既方便于实际操作又能确保质量为出发点。……严格说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前40年的电影完全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特别是1979年之前,强调电影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属于典型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具。虽说这其中也不乏受当时观众欢迎的好作品,但都不以票房论输赢。‘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早已将电影的商品价值排除在外,所以,这一阶段的中国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好莱坞那样的类型电影。”[14]这是我们今后运用类型电影概念来解读中国电影史时要特别注意的。
(三)用电影的本土化/民族化问题取代了电影的国际化属性
在类型电影观念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倡类型电影本土化/民族化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它既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又很容易变成一个强势话语。很多东西,一旦和本土化/民族化扯上关系,往往就变得不容反驳,冷静的学理辨析和对话很难进行下去,类型电影也是如此。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是对于到底如何本土化、民族化,人们往往又是莫衷一是。在谈论任何类型电影本土化、民族化的话题之前,必须首先明确,电影是世界性的、通适性的现代传播媒介,因为电影的“许多创作欣赏的规律是有共同性的,人类的基本兴趣爱好在许多方面是普遍的。电影语言的许多规则与人们观察、认识世界的习惯相符,就因为这些,研究深入到审美心理模式是必要的。通过对各国观众的统计、观察,发现许多深层规范是不可破除的,只能去利用。……如影调色彩引起的反应,构图给人的感觉,前景在构图上的重要性,黄金分割的运用,不同运动形态、不同光色镜头的组接。以具备一般文化水平的人为标准,这些对各国观众具有普遍意义。”[7](48)电影固然有民族特点,但脱离或违背电影的基本叙事规律及表现手段的民族性是不可想象的。说到底,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想不实行本土化、民族化都难,因为不论是强调本土化、民族化,还是一心向往国际化,都是当代民族性的典型症候!至于那些模仿美国西部片的所谓中国式西部片,也许称其为“山寨西部片”更为恰当,是一种“伪民族性”或“伪国际化”的表现。巴赞认为:“我们通常是按照这些形式特征确认西部片的,其实,它们只是西部片深层实际的符号或象征,西部片的深层实际就是神话。西部片是一种神话与一种表现手法相结合的产物。”[11]而我们既没有美国西部的神话,又缺乏那种好莱坞那种娴熟的表现手法,何来西部片?何必非要搞所谓的中国式西部片?这是简单滥用本土化、民族化概念的后果之一。所以,光提本土化、民族化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谈论类型电影时,仍需更多地关注电影基本的叙事规则及表现手法。否则,靠表面的题材、猎奇的仪式是不可能带领中国电影走向真正的国际化、市场化、民族化的。
(四)类型电影研究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电影叙事一般规则的研究
现在电影界越来越重视类型电影,把振兴国产电影寄希望于发展类型电影,而不少人认为我们自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所谓的类型电影,至少从80年代自觉发展类型电影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可为什么国产电影在总体上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还让人觉得危机重重呢?这不是美国类型电影观念本身的错,而是我们对此观念的接受出了问题。 率先在国内引进美国类型电影观念的学者郝建、杨勇曾提出疑问和猜测:“真得好好想一想。类型化现象为什么在电影中如此明显,电影的创作、欣赏模式是怎样建立发展的?类型电影与非类型化影片的关系如何?通过类型电影这一现象,我们对电影艺术特征和大众的审美模式能有些什么新了解由此还可引出些更深入的问题,类型电影这一现象还有更深层的规律吗?”[7](42)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有见地的疑问和猜测一直没有得到后来的研究者们的回应,更没有对未来的国内类型电影研究走向产生过影响。这一疑问和猜测给人的启发在于,它没有就类型电影来谈论类型电影,而是把类型电影放在电影这一更大的框架内来进行观察和思考。这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内就类型电影谈类型电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的狭隘视角。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最为迫切也是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发展类型电影、如何发展类型电影的表层问题,而是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电影叙事的一般规律和手段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最根本问题不是“类型的”问题,而是“电影的”问题。这是一个类似于还没学会走路就要学跑步的问题。
电影叙事的一般规律和手段是一项基本功,不管是对于类型电影还是非类型电影。做出中国电影现在整体上还没有完全掌握基本功的判断,在感情上会令人难以接受,毕竟中国电影已经诞生100多年。但是,建国后中国电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创新电影语言的诉求,表明了中国电影语言整体上存在着“基本功的焦虑”。早在1962年,就发生过关于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问题的争论。当时就有人提出,中国电影只有几十年历史,没有什么传统。又有一种说法,中国电影五十年来,还只是向外国学步的阶段。那场争论的一位主要参与者瞿白音则强调:“难道不要重视规律和特性?一定要重视。对电影艺术的规律和特性探索、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电影艺术规律和特性,是否可以概括为创造视觉形象和蒙太奇结构两点呢?……这两点似乎可以比较明确地使电影艺术区别于小说和戏剧吧。”[15]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1979年,张暖忻、李陀发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提出当时我们的电影“落后于形势……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我们应该不应该向世界电影艺术学习、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们这篇文章,只想从一个角度做一点探索,这就是如何使我国电影跟上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实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问题。”[16]显而易见,文章充满着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唯恐落后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也一直延续到中国电影此后三十年的发展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感叹“我国……电影语言方面……仍然因袭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是三十年代的老一套……”、“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六七十年代之后,(世界)电影语言的变革……十分迅速”[16](44),力推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新浪潮电影与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将它们作为未来电影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恰恰是巴赞自己宣称:“美法两国生产的影片毕竟足以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有声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已经明显达到均衡和成熟的水平。……总之,我们看到一种‘经典的’艺术臻于完美形态的一切特征。”[11](65)该文被称为“探索片的纲领”或“第四代导演的艺术宣言”[17],其核心艺术取向左右了中国电影创作很长一段时间,而这份宣言的核心主张很显然与后来推崇的类型电影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该文的重要影响,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于2005年第3期还特意重发全文,以示纪念。及至1986年,邵牧君重提“中国电影创新之路”,但仍然强调“电影创新的合理局限性,指的是电影同其他艺术相比起来,在创造 上有某些不可跨越的合理界线”[18],又说“电影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因此,中国电影注定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模仿时期”[18](6)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中国电影一直在吁求“创新”,倒不如说是为了“补旧”、“补课”。对于中国电影的创新诉求与娱乐片(类型电影)的关系,李陀自己做出过恰当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种种努力,包括电影观念的变革,包括对电影特性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探讨,包括探索影片的创作一如果没有这些,今天谈娱乐电影就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对电影的基本特性和现代电影语言没有很好的掌握,那么拍娱乐片就是瞎胡闹。”[19]
近年来,谈电影产业化多了,研究电影叙事基本规律的少了。电影叙事规律和手段是永远不过时的话题,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尤为如此。如果没有真正掌握电影叙事基本规律和手段,电影产业化目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类型电影不是救命稻草,今后的类型电影研究,首先要搞清楚哪些问题属于“电影的”,哪些问题属于“类型的”。到底哪些是属于电影本身所普遍拥有的规律,哪些是类型电影所特有的规律。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才能有利于我们吸收美国类型电影的精华。
(五)第一手外文文献引进、吸收严重不足
对于类型电影这样的纯“舶来品”展开研究,尽可能多地占有一手外文资料是重要的前提。在好莱坞电影占据中国电影票房重要份额的今天,总不能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搞一套所谓的中国式类型电影吧。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除了类型影片外,对国外类型电影研究文献的引进、利用存在着译文少、原文利用更少的情况,依赖少数第二手外文文献的研究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较早且较有影响的译文主要有爱·布斯康布《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世界电影》1984年第6期)、查·阿尔特曼的《类型片刍议》(《世界电影》1985年第6期)、达德利·安德鲁的《评价——对于类型和作者的评价》(《当代电影》1988年第3期)以及T.贝沃特和T.索布夏克合作的《类型批评法:程式电影分析》(《世界电影》1997年第1期)、安·图德的《类型与批评的方法论》(《世界电影》1998年第3期)等。以上几篇译文都节选自专着或论文集,其中以查·阿尔特曼的《类型片刍议》一文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该文对类型片娱乐属性的专门论述及对类型片7大特征的简要概括成为后来中国类型电影研究的重要文献,被引用与被评述的频率都高得惊人,对中国类型电影研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关于各个具体类型片的研究文章,不过比较零散,在国内影响不及上述文章。
王志敏、陈晓云联合主编的《理论与批评:电影的类型研究》是一部论文集译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书中所收集翻译的8篇喜剧电影研究文章,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而美国学者托马斯·沙茨的类型电影研究专着《好莱坞类型电影》中译本直到2009年才面世,对于已经走过二十个年头的中国类型电影研究来说,可谓姗姗来迟,它一面世就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外来文献参考书。当然,在《好莱坞类型电影》中译本面世之前,其主要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早已通过郝建、杨勇等人的引介进入中国类型电影研究领域。除此之外,国外研究类型电影的绝大多数经典着作及最新代表作,如Baxter,John的The Gangster Film(1970)、Stuart M. Kaminsky的American Film Genres(1974)、Stanley J. Solomon的Beyond Formula: American Film Genres(1976)、Barry Keith Grant的Film Genre: Theory and Criticism(1977)、Barry Keith Grant的Film Genre Reader(1986)、Rick Altman的Film/Genre(1999)、Barry Langford的Film Genre: Hollywood and Beyond(2006)、Ira Jaffe的Hollywood Hybrids: Mixing Genres in Contemporary Films(2007)等,很少出现在国内类型电影研究专着的参考文献目录中。英美自二战以后就开始了对类型电影的肯定性研究②,至今积累的论文及着作不计其数,有选择性地、系统地增加翻译相关的论文、论着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类型电影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任务。可喜的是,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收藏了少部分国外类型电影专着。
(六)研究视角单一
欧美的类型电影研究基本上经过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一文本到社会整体、从形式主义到文化研究的转变过程,这种研究视角的变化既是学术研究自身的逻辑演变规律,也符合社会思潮变化的实际,使得欧美类型电影研究得以一步步走向深入。达德利·安德鲁指出:“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类型问题便始终是电影理论中一个持续存留的问题,它还是形式主义者保卫他们的具体作品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的战场。诺思罗普·弗莱的分水岭式的着作《批评的解剖》(1957)在所有艺术的批评家中形成敌人和友邦,因为他的这本着作要求对于文学整体的系统观点,而不是把焦点集中于单一的本文。”[20]中国类型电影研究基本上截取的是后一阶段,即侧重于宏观的、整体的、文化研究的研究视角,托马斯·沙茨式的宏观社会文化学研究广受欢迎就是明证。这种视角不但因应了中国电影界津津乐道的类型电影本土性、民族性、意识形态性诉求,而且比较契合时下动辄进行体系建构、惯用宏大叙事的学术取向——我们向来缺少西方学界那种自下而上的、细读式的“新批评”传统。事实上,对于真正的专业研究来说,任何时候文本细读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的类型电影研究不但需要补上这一课,而且需要长期坚持下去,脱离文本细读的类型电影研究往往容易导致脱离电影作品的实际,托马斯·沙茨式的宏观文化学、社会学视角只是类型电影研究中的一种,决不能替代多种视角特别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内部研究。
(七)未能正确理解类型电影重复与创新的有机关系
英美类型电影研究中固然强调所谓的“惯例系统”,强调其稳定性、可模仿性及重复性,但是并不否认类型片自身的创新能力,往往特别注重二者的有机联系。如英国学者爱·布斯康布一方面指出“一部类型片的存在基础是新鲜的东西和熟悉的东西的结合。类型的种种惯例是观众熟而能详的,而这种熟识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化艺术实际上常常是以此为基础的。”[21],同时不忘提醒“如果一个导演只是一味照搬而不是利用惯例,我们看到的将是一部故事和形象看了上文便知下文的影片,而好莱坞甚至直到今天还常常被说成是专门生产这种影片的。”[21](50)事实上,美国类型片长盛不衰的最大秘密并非恪守陈规,而是在遵从惯例基础上的不断创新。美国学者珍妮·贝辛姬曾以西部片中的比利小子这个人物形象的变化为例,说明西部片是如何通过不断创新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她指出:“在不同的影片版本中保持一个一贯的比利形象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比利仍然保持着30年代影片中那种快乐直率的英雄形象,那么,他对70年代或80年代的观众就没有吸引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这个故事和典型的西部片模式中,巧妙地反映新一代人的态度和观念”[22],从性格塑造上来看,1930年版是一个在牧场工作的自由快乐的比利,1941年版则是一个从坏孩子转变为好孩子的少年违法者,1958年版中则是一个被扭曲的青少年,1973年版则是一个被官方出卖而有可能成为正经男孩的比利,直到1988年版又变成一个天生喜爱暴力的小流氓。[12](277)从西部片中的第一个比利到最后一个比利,涉及影片50多部,时间横跨60年,但观众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个故事,这绝非墨守成规所能做到。
虽然也有少 数学者注意到类型电影中惯例与创新的有机联系——如郝建、杨勇就曾提到“类型电影理论从纵线上注重发展和继承的关系,注意作品对既成艺术元素、叙事模式、造型语言的继承,注意遵从观众的审美心理和社会情感,注意在渐变中发展艺术语言,给艺术品注入新观念”[23]——但中国类型电影接受在总体上倾向于甚至是乐于用一种机械的、静止的、急功近利的眼光来看待类型电影,潜意识中存在把类型电影的“惯例系统”当作现成货,拿来就用的取巧心态,这种心态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类型电影观念固化成一套僵死不变的东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类型片拍摄热中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有人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尽管人们在分类标准上还十足地处于混乱状态,但那种给一部电影戴上某一类型的帽子的观念却毫无疑问地已经建立起来了。”[24]当时拍摄的大量动作片就突出地存在这样的问题,王海洲评价道:“即使有人观摩学习国外类型片,也大多限于盲目的模仿,而很少去思考叙事的角度、叙述的方法以及人物的刻画、节奏的把握,更遑论将成功的类型元素与中国的主流价值相结合,可以说,面对市场压力,创作者急功近利、饮鸩止渴者众,为成熟类型做长远计议者寡。大多数动作类型片在叙事与动作语言探索方面不够,但对血腥暴力与色情诱惑却展示颇多。”[25]在理论研究中把类型电影的某些规范当作教条来进行理论演绎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上述硬伤在21世纪的中国武侠大片中也频频出现,被汪献平指责为“类型创作多为重复与模仿,缺少创新意识”[2]。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机械模仿、创新乏力的忧虑。
美国类型电影观念中国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异不仅仅违背了学术的逻辑,而且也违背了电影产业自身的现实逻辑,从而可能危及中国类型电影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应当引起我们及时而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