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篆书法创作网友谈
时间:2022-09-03 07:5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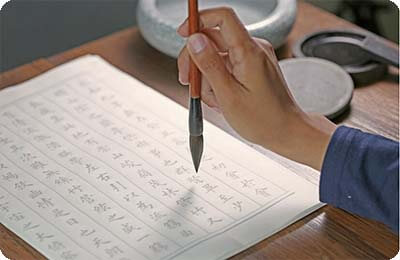
主持人谷松章谷国伟
太室尊者:金文形成是铸造形成的,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经过两千年的流传,随着时代的变革,岁月的历练,时间这个魔术师把金文变得高古端庄。学习金文,用毛笔去表现,我想还是用启功先生的话“透过刀锋看笔锋”,虽然是说魏碑的,用在这里还算实用。书法的书写性质是最关键的。
至于字法问题,还是要从众,从现有的资料里提取,自己创造的字,在展览时代,评委是不认可的。
当代金文好手不少,北京王友谊算一个。年轻一代中,河南刘颜涛算一个。刘颜涛的金文创作从甲骨发轫,得力于吴缶老,自成面目,多有人学之,难得。
medialei:应该说,金文给后人提供的形式营养,主要是视觉的、空间的、结构的。从这个角度看,对金文的开掘当然应该首先关注构成。但辩证地说,仅仅关注构成的开掘,而不去注入时间因素,又难免千人一路,陷入俗格。但有一点,空间性的构成是基础。
对于金文中还保留着一些象形余绪,今人(包括一些现代书法)有将其夸大者,但都比较恶俗。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不可取。原因很简单,挖掘形象,有许多现成的、更有效的表现手段。这个思路,俗就俗在误解了书法的审美特征。
艺术创作,可以将时代不同、派系不同的金文在一幅作品中混用,但跨度不能太大。否则很难不成为专业界的笑柄――这点我建议学学梅兰芳改唱腔的招数。金文之美就在于诡而凝。
谷松章:金文历时较久,派系众多。以往严谨的文字学家反对将时代不同、派系不同的金文在一幅作品中混用,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这在篆刻中已经解决,不成为问题。但是书法作品字多,对整体统一的要求高。大篆在书坛的兴起也比较晚,至少是在乾嘉学派之后。大篆从晚清就开始被书坛关注。吴昌硕、吴大徵、罗振玉、黄士陵等的成就都可观。稍晚的黄宾虹更是独出机杼。一些文字学家的书法水平也很高,如容庚等。
当代的大篆书法也有高手,但是偏重于楚简,金文倒在其次。是源于书写方式易于开掘?还是新资料的新鲜感的吸引?似乎都不全是。
丰富的金文书法风格给我们留下的开拓空间极大,但是对其开掘的文字学修养等要求比较高,所以总体创作态势不很理想。
medialei:梅先生的戏班子,首先是个经济实体,所以艺术创作、戏曲改革绝对得尊重受众(衣食父母)的态度。不像我们写字的,自视清高,可以不管受众的感受。暂时看,是比梅先生的戏曲改革自由,但梅先生看似不自由的小步试探,却能保证不跌跤。而我们看似自由的随意组合,很可能经不起行家和时间的检验。
竟庐:金文质朴的象形意趣和现代图形的简化特征有很多相通之处。
许江涛:当大篆的如北京的王友谊、河南的刘颜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年轻作者写大篆的也不少,只是由于风格不是很突出或大篆不是其专攻等原因而未能被书界广泛关注。另外,已经作古的老书家、原陕西省书协主席刘自椟的大篆有自己的鲜明风格,开一代新风,不愧为一代篆书大家!
真名是梁磊:像其他艺术一样,我们应该发掘它的语言,然后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先当它是一门技巧,然后才是艺术。技进乎道!
朴聋:金文尚象,甲骨、大篆、楚简错证、未证的文字尚多,用以集联作文空间远比小篆小,模棱两可为之,不过炫人之技以显独能耳,故写金文应慎之尤慎;
金文滥觞之时,尚无书法载道意识,然地域风格已显,先民崇天地敬鬼神,风气淳厚,其字自得自然之气,翻刻、风雨侵蚀等内因外因造成今日所见金文之古气斑斓,离金文墨迹面貌已远,透过刀锋看笔锋固对,但难显今日所见金文身上其他负载因素与信息而容易流于平滑,故须以后世之“法”做之、变之、增之、损之而又一一自然;
北京王友谊先生当世写金文翘楚。已故书家中,潘天寿先生所作甲骨、金文无俗气,尤可贵;
淳风堂:大篆的创作,应该说要感谢战国时期的多国并存,诸侯相互割据一方,因而形成了这一个时期的地域文字书风的丰富性、多样化。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甲骨文、金文、漆器等铭文、竹简、帛书、陶文、封泥、石刻、玺印文、货币文字等,都是书法、篆刻家们要研究的很好的范本。假若是文字都像秦以后统一的模式的话,我们今天也只许照就着一个模式发展下去了。那该会是多么寂寞郁闷的事啊。
长久以来,铸造、刻画于鼎之上的文字,如何利用柔软的毛笔进行表达,也是让许多的书印家们头疼的事,对于古篆文字夹杂着许多象形图案的文字,仅属于文字过渡时期的一个过程而已。随后也被渐渐地由符号化的实用文字代替了。创作中亦是尽量可以避免使用的。但是,若是以图案文字创作小品形式的作品,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可以从一些长沙帛书、包山楚简等大批楚文字的大量出土中,充分领略真正意义上的对大篆书写的感觉了,对钟鼎文字的线条特点的认识也渐趋深入,同时简帛文字承袭了许多商周以来的篆书文字写法,通过偏旁部首的比较也使得一批罕见字、疑难字得以顺利破译,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积累,拓展了视野,为解读更早的文字充当了钥匙。金文富于装饰可以用端庄、奇瑰集众美于一身来概括。不是连奥运会设计图标也使用了“篆书之美”了吗?
大篆的创作不难于单字的笔法问题,创作中的通篇布局应该算是一个难点。再有就是文字的数量上的不足,使得创作仅限于小篇幅的文字创作了。而许多小篆文字就比较多。这就非常考验作者对文字的造型能力的把握了。八宝粥是要煮烂了才好吃的。在大幅的作品创作中,北京的王友谊先生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最近的巨幅作品问世,使得集字书法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乐之山馆:对于丰富的金文书法风格,我们首先要学会选择,取其“适己”之处,怎样灵活运用这些“丰富性”是考验我们自身创作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一味地简单复古,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在这个取舍的过程中单纯地强调以形制的“出新”和视觉的“冲击”来获取受众的审美愉悦似乎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试看一些以大篆字形为创作母体的“现代书法”作品冠以“无题”、“NO.-001”等等莫名其妙的名称,言其书法倒不如说是打着书法的招牌进行后现代抽象美术创作(姑且以此名之),借鸡下蛋而已。毋庸置疑,金文的范铸、凿刻等制作形式极大地丰富了笔墨线条的多元性,作为当代纯艺术创作状态下的书法艺术,字形的多元、线条的丰富、字体的时代派系等等已经不能在学术背景下来看待,“书法艺术,艺术书法”,不言而喻。“朴拙的字形和唯美的结体”是大篆吸引我学习创作的魅力所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怎样借鉴战国简牍、帛书、盟书等多种书体字形来丰富我们的创作并有所创见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就,书外求书,印外求印,在书法创作的高层阶段,综合学养的提高是决定自身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提高的难点在当代显然已经不在手上功夫了,在这方面,当代书家尤以王镛等做出了表率。
唐长老:我觉得金文丰富性包含两个意义,一是表现在时间跨度和地域跨度造成的形象的丰富性上;二是相对小篆而言,其丰富性表现在自然天成、可塑性极强的字形和线条上。这也是大篆在艺术创作的层面上让人大力追捧的原因之一。丰富性同时也带来操作上的复杂性。这是不少书家没有认真面对的问题。大篆是广义的,涵盖的内容太多。存在时间不同、地域不同、不同、形成过程不同(铸凿之分等等)、书风不同等问题。要在一件书作里和谐统一地运用这种丰富性极大的书体,首先还得有积累有分析地审视大篆。对金文的范铸、凿刻的效果相信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但同是铸或同是凿,也有不同的滋味,还须细辨,并不断尝试。将时代不同、派系不同的金文在一幅作品中混用,的确要注意。但有时跨度不大、书风相近、糅合得当的话,也是可以的,毕竟大篆在数量上有局限。而且,近代一些文字修养很高的篆书名家也是如此。把帛书等糅合到大篆或其他书体的创作中,当代有人在做。但我以为金文是金文,帛书是帛书,表现时不可不区分。譬如写魏碑一路,不因新出的资料而更易笔法。金文创作的难点在学养。糅合依靠学养,线条得于学养。当今的大篆书家我比较认可的,已故的蒋维崧先生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