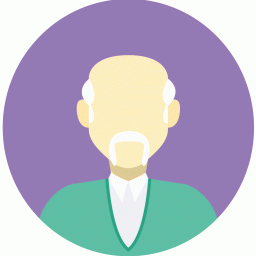孤独与梦幻的挽歌
时间:2022-05-06 08:13:44
比较契诃夫的《海鸥》和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这两部剧作,我们会发现它们在主人公塑造与主题上惊人的相似之处。《海鸥》的背景和氛围是俄罗斯民族那种特有的永恒的忧郁而富有诗意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底色所映衬出的是社会表面规则下的私人欲望,是人的微妙的情绪和情感。在剧作中,契诃夫关注的是那些破碎的肉体和心灵,他们沉迷于往事的回忆,为那些无法实现的梦想和未酬的热情而倍受煎熬。在《玻璃动物园》中,威廉斯也旨在描述那些破碎生活中残留的诗意,人物也时常专注于往事和回忆,在他们阴暗的动机和生存策略中,我们看到了灵魂的孤独、遗弃了的希望的残片和褪色的自我怜悯。
与《海鸥》相比,《玻璃动物园》的人物关系相对简单,只有母亲、儿子、姐姐和吉姆四个人物,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他们与《海鸥》中人物的渊源关系:两个家庭都没有父亲;儿子(特里波列夫和汤姆)都是未来的作家,他们都无法挣脱家庭的羁绊和社会背景的束缚;母亲(阿尔卡基娜和阿曼达)都是自我中心的女人,只是靠回忆当年的风光来慰藉自己眼前的落寞;都有一个外来的“闯入者”(特里果林和吉姆)唤醒了年轻女主人公(尼娜和罗拉)失意而孤独的灵魂并使之对外部世界产生期待和向往;但随之带给她们的是更大的迷茫和失落。
先看两个年轻的男主人公:特里波列夫和汤姆。在《海鸥》中,特里波列夫和特里果林代表着人生的两极。前者是成名之后的作家,所到之处是鲜花和掌声,是类似尼娜一样的年轻崇拜者们的艳羡和倾慕的对象(虽然在他自己看来成功后的生活并非是那样诱人的);后者是还在艰难跋涉的文学青年,他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但却苦于找不到表达自己思想与情感的形式,周围大多是母亲那样的人的嘲讽和挖苦。这个被母亲称为“基辅的乡下人”和“寄生虫”的青年,几乎与周围的每个人都格格不入,别人也几乎很难理解他的行为和艺术。在他的戏里,那段“人,狮子,鹰和鹧鸪……”的大段台词,只是引起了大家的哂笑,连自己的爱人尼娜也说“你的剧本很难演,人物没有生活”、“缺少动作,全是台词”。在那个被淡淡的忧郁笼罩的庄园里,特里波列夫没有知音,他的内心是孤独的,空有一腔热情却壮志未酬。《玻璃动物园》中的汤姆与特里波列夫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他的文学梦想和鞋店仓库、母亲的聒噪以及家庭的郁闷格格不入,“我想停留下来,但总有什么东西在追逐着我”,这是内心的冒险的激情,这种激情如暗潮涌动,使他欲罢不能。他不顾现实生存的尴尬,用电费缴了海员商会会员费。最终因为在鞋盒上写了一首诗而被解雇。与其说汤姆是被迫离开,不如说他是主动告别,与那个生活的泥潭和沼泽主动告别。
特里波列夫和汤姆的内心都有两方面的激情,一是艺术之爱,一是女性之爱。前者在特里波列夫表现为对戏剧的探索,在汤姆表现为对诗歌的狂热;后者在特里波列夫表现为对尼娜的执着爱情,在汤姆表现为对姐姐罗拉深深的眷恋和怜惜。这两种爱可以说是他们在心灵上的两个顶峰,是他们梦幻的根基,也是他们孤独的源头。
特里波列夫渴望创造崭新的艺术形式,认为“现代的舞台,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和一种格式……当他们从那些庸俗的画面和语言里,拼着命要挤出一点点浅薄的、谁都晓得的说教来……”。特里波列夫一开始写的那段独白,尼娜先后两次提到,第一次是在第一幕的表演中,我们读后几乎与他的母亲一样的感觉:矫揉造作和莫名其妙。但在最后一幕,当这段独白再从尼娜的嘴里说出时,却让我们有深深震动的感觉,它变成了一首对易逝青春和热情的忧伤的安魂曲。直到此时,我们才理解了特里波列夫和他的艺术。成功后的特里波列夫并没有从孤独和忧郁中走出;他始终害怕陷入艺术的陈规旧套,对自己也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他发表的和他理想与梦幻中的东西是不同的,别人也无法理解他。他依旧是一个失败者和失意者。爱人尼娜的最后出现加速了特里波列夫的这种幻灭感,最终,他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特里波列夫先后自杀过两次,如果说第一次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艺术遭到误解和嘲讽,那么第二次,则是艺术与爱情的双重幻灭,而且,这次的艺术幻灭不再仅仅是不被人理解,而是对无法企及的艺术理想彻底地绝望。但,特里波列夫自杀的枪声是不妥协的,他宁可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被庸俗的现实和艺术溅一身污浊的泥点。这最后的一枪,是绝望,更是对抗。
《玻璃动物园》中的汤姆是个诗人,在仓库工作清闲时就偷偷地躲进盥洗室写诗,而且被人称为莎士比亚。但汤姆的性格特点,更多表现为他的诗人气质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他虽然表面上昏昏噩噩,但内心多愁善感,热血沸腾,“每当我拿起一只鞋,想到人生的短促和自己无所作为就感到不寒而栗”。和特里波列夫一样,汤姆对自己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和我想要做的有多大距离!”两个人在苦心经营的同时,都感到了精神上的孤苦无依。汤姆对罗拉的爱是姐弟之爱,这有别于特里波列夫和尼娜。这种姐弟之爱剧本没有刻意渲染,但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姐姐罗拉是汤姆最终的牵挂。在第三场,汤姆因为和母亲吵架,不小心打碎了姐姐的玻璃动物。当看到姐姐伤心地哭了时,粗暴的汤姆一下子变得温顺异常,双膝跪地去捡跌碎的玻璃。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汤姆对罗拉深厚的感情。在剧本最后,汤姆梦想着在一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与罗拉意外相遇,四目相对,汤姆深情地说:“哦,罗拉,罗拉,我想把你丢下,但我比原来更忠于你。”这多么像特里波列夫对尼娜所说的话:“我骂过你,恨过你;我撕过你的信和照片,然而我时刻都知道我的心灵是和你在一起的。”《海鸥》里波列夫留下了,离开的是尼娜;《玻璃动物园》中罗拉留下了,离开的是汤姆。但无论谁去谁留,横亘在心里的,都是那青春的孤独和梦幻,是那热情燃尽后的忧郁和凄楚。
《海鸥》和《玻璃动物园》中还有一对相似的人物关系:特里果林与尼娜,吉姆与罗拉。
特里果林和吉姆是两剧中最具清醒的自我认识的人。特里果林表面上春风得意。但心里有一个柔弱的点,这就是对尼娜所向往的那个艰苦世界的真实情况的清醒认识,他真诚地对自己感到不满和忧虑:我生活在一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我时常不懂自己所写的是什么。这种关于创作和生活的独白并非是成功后煽情的卖弄,而是对这种生存状态的悲剧性的真切体会。据说对《海鸥》并不欣赏的托尔斯泰却极喜欢特里果林的这段独白,认为这是该剧中写得最好的地方。在《玻璃动物园》中,汤姆一家三口都生活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最现实和最清醒的人是吉姆。正如汤姆在开场白中所说的:“他是现实世界给我们这一家脱离社会的人派来的使者。”吉姆真诚热情,对罗拉的关心和帮助是毫无恶意的。当他发现他和罗拉的关系有可能使彼此尴尬时,便果断而理智地抽身而出。我们无法对吉姆提出任何责备。
尼娜和罗拉都是剧作家极钟爱的女性,对她们的美丽都极尽描述。尼娜的美是热烈奔放。即使整天自我欣赏的阿尔卡基娜也承认她有那么美的容貌和声音,认为埋没在乡下是犯罪,甚至连老索林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而罗拉的美是娇弱超俗,“象一块在阳光照耀下透明的玻璃,放射出一种不真实的瞬息即逝的光辉。”在特里果林和吉姆进入她们生活之前,尼娜和罗拉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私人世界里。但在这个私人世界里,都有一个男人隐身其中。尼娜是那么崇拜特里果林,在成熟、沉稳有充分自知之明的特里果林面前,特里波列夫的冲动、嫉妒乃至热情显得十分幼稚可笑。特里果林说,尼娜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梦,是一个温柔而甜美的梦在支配着他。尼娜的到来使他暂时淡化了创作的痛苦和生活的烦恼。尼娜的青春、热情和美丽恰恰击中了特里果林心中的那个柔弱的点,使他有重获新生的感觉。特里果林和尼娜是在互相救赎。特里果林对尼娜而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通过他,某种未知的无人走过的美妙新路铺展在她的面前。
就像尼娜在心里暗暗崇拜特里果林一样,罗拉也一直在暗恋着中学时代的同学吉姆;就像尼娜记住了特里果林的所有作品一样,罗拉也珍藏着和吉姆有关的文章、节目单和剧照等等。在吉姆到来之前,罗拉封闭、自卑、敏感,像保护着玻璃动物一样保护着自己孤独的内心世界,使它免受外界侵袭和干扰。是吉姆让她认识到自己的美丽和与众不同,就如吉姆所言:“他们平平凡凡―――象野草一样,而你―――你是蓝玫瑰!”吉姆给了罗拉自信和勇气,罗拉不再羞涩了,罗拉会跳舞了,罗拉会幽默地说话了。如同特里果林给了尼娜一个演员的梦想,吉姆也给了罗拉一个现实中的爱情的梦想。
但梦想毕竟是梦想。当特里果林的感情冲动化为乌有后,当吉姆承认了自己的冒失后,尼娜和罗拉面临的是梦想破灭之后的更加深重的孤独和失落。很明显,“海鸥”和“玻璃动物园”在这两出戏里都具有象征意味。尼娜说:“我像只海鸥,被这湖水迷住了……”在最后一幕,玛莎说:“湖里整个起了大浪头了。”这不单单是这一幕的背景,而且也是人物生活的尤其是尼娜生活的主旋律。或许“海鸥”的象征意义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的命运,但我们却能从中更多的看到尼娜的形象。她就像那只海鸥,试图高蹈于波浪之上,却被沉重的生活剪断了翅膀。但尼娜并没有绝望,在梦幻的碎片中尼娜仍能看到亮丽的光泽。她更加成熟了。她对特里波列夫说:“我思想着,思想着,于是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一天比一天坚强了……在我们的职业里……主要的不是光荣,也不是名声,也不是我所梦想过的那些东西,而是更有耐心。要懂得背起十字架来,要有信心。”尼娜离开特里果林,从另一方面说,难道不也是种解脱?
“玻璃动物园”也极具象征色彩。罗拉一开始对玻璃动物极其敏感,汤姆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玻璃玩意儿就让她大哭起来。但到了第七场,当吉姆同样地不小心打碎了个玻璃动物时,罗拉却说:“我并不太偏爱这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一件小事。玻璃本来就容易打碎。”玻璃动物是摆在罗拉面前的一面镜子,罗拉对玻璃动物态度的变化折射出自己心灵的变化―――她不再像蜗牛一样缩在自己的壳里了。吉姆的离去也同样使罗拉失望,但作者写到,“她咬紧她那颤动的嘴唇,然后勇敢地笑了。”人生是易碎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一场情感风暴的罗拉,会像尼娜那样,勇敢地走出自己的玻璃人生。
在《海鸥》和《玻璃动物园》中,最具相似性的两个人物还是母亲的形象:阿尔卡基娜和阿曼达。在和儿子的关系上,他们各自都有深深的隔膜,两出戏最尖锐的冲突都是发生在母子之间的。在精神上,阿尔卡基娜始终在嘲讽特里波列夫的艺术探索,而阿曼达对汤姆的文学理想也是嗤之以鼻,没收了汤姆带回家里来的“劳伦斯的”。在物质上,在特里波列夫眼里,母亲阿尔卡基娜自私、吝啬,自己有七万元的存款却说给儿子买一身衣服的办法都没有;而阿曼达与汤姆的冲突也时常是围绕着房租、电费等经济问题。最终,她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特里波列夫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痛苦人生,而汤姆远走高飞,彻底摆脱了环境的拖累和约束。在爱情上,这两个女人也有类似的经历。阿尔卡基娜虽然不再年轻,但在卖弄风情方面仍乐此不疲。她心里清楚,特里果林被尼娜的俘获只是暂时的,她的怀抱仍是特里果林的最终归宿。阿曼达虽也深谙“女人是一个美丽的陷阱”的生活哲学,但仍旧挡不住自己丈夫远走他乡。他虽走了,但阿曼达却自认为仍在精神上占有他,那挂在壁炉上的温菲尔德先生的照片,那穿在身上的不合身的温菲尔德先生的宽大的浴衣,与其说是阿曼达对丈夫的怀念,不如说是对自己已逝美丽青春的怀念和永久确证。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相同点,两个女人都有表演天赋,只不过阿尔卡基娜是真演员,她的表演的地点是真的舞台,而阿曼达的舞台是在现实生活中。阿曼达为女儿戴上的“快乐的骗子”,她在吉姆面前不分场合令人肉麻的卖弄风情,实在是具有表演风格。但无论是前者的真表演还是后者的假表演,都已成了让她们伤感的过去。阿尔卡基娜和阿曼达生活中最大的慰藉就是回忆了。前者是咀嚼当年舞台上的风光,后者是回味当年一个下午接待十七个男客人的“辉煌壮举”。她们,是彻底地活在过去的人。
《海鸥》和《玻璃动物园》中的人物,都是一些精神上孤苦无依的人。他们站在生存的悬崖边,看到了脚下的深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幸福的虚无。《海鸥》中,玛莎一开场便说:“我在为我的生活戴孝”;索林说:“我觉得自己象一只旧烟嘴儿似的,已经满是污垢了。”阿曼达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前途是什么?”阿尔卡基娜、阿曼达、尼娜、罗拉,还有特里波列夫和汤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和无奈。失败在毁灭一个人,可成功也同样让人无法满意。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体生命的欠缺和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那些热情和愿望都是徒劳的,人是如此地在受苦、悲观和绝望。但在这种受苦、悲观和绝望中,个体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他们既不逃避也不企图超越人生的悖论,在各自的旅途上哼唱着一曲孤独与梦幻的挽歌,抱慰个人在生命悖论中的挣扎。
契诃夫站在一个超出一般个体的高度,俯视众生。他看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弱点。他带着幽默和同情,坚持对人类的弱点进行挽歌式的描述。这种契诃夫式的同情和嘲讽的混合,深深影响了威廉斯,这便形成了《玻璃动物园》中哀婉和喜剧兼具的风格。这种风格成为威廉斯作品延续多年的一个标志。
注:本文所引剧本原文皆出自《契诃夫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外国当代戏剧选(3)》(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