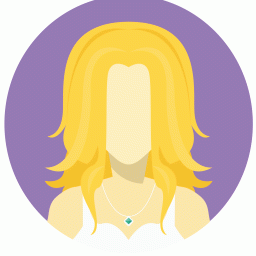对话海因茨·布德:没有阶级张力的阶级社会
时间:2022-10-02 10:13:50

德国《新社会》杂志(Neue Gesellschaft)2012年第3期刊登了该杂志主编托马斯·迈耶尔(Thomas Meyer)采访德国社会学家、卡塞尔大学教授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的文章。布德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是社会排斥问题,他在访谈中认为,不平等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并且在不断发展,它首先表现为职能性分工的变化使职业结构内部发生分裂,造成社会意识的缺失。他提出,可以用“碎片化”(fragmentiert)这个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而要改变不平等的结构不能指望政治措施的干预,而是迫切需要复兴属于公共财富的文化。
迈耶尔:布德先生,您如何描述不平等现象在最近的演化趋势?
布德:不平等在一切社会,至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的社会中,表现突出,尽管严重程度不一,但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同样有所发展。首先,职能性分工发生了变化。我不是指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再加以细分的传统分工形式。确切地说,我们正经历着传统的职场、常常是工业职场内部发生的一场能力革命,其根源在于知识因素和劳务因素的介入。这种情况在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职业结构的某种升级换代上,因为在所有层面上技能水平都提高了,特别是在生产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营部门中。在德国,汽车集团、机械制造业和医药技术领域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服务业领域情况也类似。例如,一个向多种族房客提供合租服务的房东懂得,为了解决每天碰到的各种难题,参加多文化社交培训班并获得结业证书是十分明智的。
职能性分工的变化在下述两类人之间划出了新的、严格的分界线:一类是能够满足这些新的知识与劳务要求的人,另一类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人。对于后者来说,过去毕竟还有一系列就业机会,因为那时更注重奉公守法,而不是能力,而现在这样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了。这就是说,在职业结构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换言之,无产阶级化的间题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去当保安、清洁工和佣工以外无事可做。
况且,在开放的社会中,这类工作由于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而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例如,从事全天24小时护理工作,在正常的雇佣条件下每月大约可挣5000-8000欧元,而在非法条件下只能获得1500欧元。
工作本身产生的上述不平等现象加剧,除此之外,移民是造成新的不平等的又一根源。问题并不在于移民本身,而在于移民成功者和移民失败者之间的分裂。移民失败者会失去同移民成功者的联系,也就是说被成功社团排除在外。
迈耶尔:除此之外,社会不平等是否也在向社会高层加剧扩散?不断增加的、过头的高额收入和财产以及整个高层脱离社会的现象是否存在?这一切现象的根源是否应当到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金融资本主义)中去寻找?另外,社会最高层排斥其他阶层的原因是什么?
布德:事实上,这正是在新的全球性的阶层队伍中出现的一种自我排斥的形式。货币财产的所有者和为其提供劳务的那些来自金融业、“律师事务所”或“主流媒体”的人心安理得地逃税,却道貌岸然地以“慈善名流”自居。这些人妄自尊大,知道怎样拿自己的钱更好地投资,以“造福人类”。
迈耶尔:那么可以用一个怎样的简明概念来概述时下的情况呢?现在流行许多概念,但多半只表征了这一情况中的个别要素,而不是整个新的不平等现象。
布德:用“碎片化”这个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的不平等结构或许比较恰当。但重要的是应搞清楚该怎样理解这个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碎片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面对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漠不关心。赢者通吃——无论是那些颇有影响的人,还是那些什么也没捞着的人,都怀有成为赢家的梦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团结成了稀缺品。
迈耶尔:我们是否可以断言,现在存在着社会意识缺失的问题?
布德:是这样。大家相互之间都缺乏打交道的意愿。在下述情况下恰恰就是如此。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研究所曾报告说,2011年德国经济增长率达到3%,即使如此,仍存在着对糟糕的现状越来越感觉不满的现象,这种情绪正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这与社会道德感失去了生命力这一事实有关。罗伯特·卡斯托(Robert Castel)提出的“松绑”概念在我看来用在这里很贴切。
迈耶尔:在“碎片化的社会”这个概念下,不平等的因素不会消失吗?分裂的问题、冷漠化的问题都可以融合到碎片化的概念之中,但下述模式不是依然存在吗?即:社会分为上层和下层,即不平等现象仍处于上升趋势。那么,该怎样同时阐明不平等这一因素呢?
布德: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论点。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平等的概念只有在下述条件下使用才具有合理性:在存在着系统化不平等的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可以设想,我们自身的地位同他人的地位具有可比性,或者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共同的规划和全社会的行为来消除这种不平等。而碎片化则意味着失去了这种联系的意识。
迈耶尔:今天,我们刚刚目睹了全世界范围的抗议浪潮,人们抗议被置于无权地位,抗议遭到排斥,抗议不被认可,抗议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们也知道,我们从来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毕竟还存在着共同的合理性观念,存在看认为公正会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信念,存在看公正的分配,以及对公正的认可。我们也向来相信我们取得的成就是有价值的,相信生存的机会会得到公平的分配。须知,社会靠的就是合理性,不可能离开它而存在。
布德:这些都是对的。问题在于合理性的形式是不是变得更加抽象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罗尔斯颇有分量的正义理论。正义这个概念已经变得如此抽象,以至于难以再被视为一个社会的伦理经济学的经验性认识,也决不可能再成为理论前提。这种道德哲学的论据既不能使我们强化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也不能对此作出说明。因此,仇怨情绪和蛊惑宣传往往比公众激情和社会移情更加接近政治。
总的来说,我有这样的印象:我们走过的这个世纪或多或少都充满着社会一体化的理念。极权主义者把这一理念夸大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但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丢掉这种理想。
迈耶尔: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分裂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碎片化现象。在现实讨论中具有某种影响的大多数社会学模式将这种状况大致勾勒如下:如今出现了一个新的上层阶级,它日益加强着自我再生产,只允许自己的后代跻身其行列。这一阶层不存在地位下降的情况。中间阶层已经四分五裂,一部分人的生活相对而言还有保障,而大部分人则越来越陷入衰落的恐惧和衰落的危机之中。至于底层阶级,他们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丧失了一切上升的希望。这样一种封闭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严酷的阶级社会的一个典型样本。
布德:你说得对。我也认为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他认为会有这样的时期:等级问题和法律地位问题处于中心地位;也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裸的阶级利益牢牢抓住了人们。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正朝着某种阶级社会前进,因为阶级利益比等级利益更占主导地位。
同时,重要的是弄清下述群体的状况:他们使现今的图景显示出一种无序的状态,因为他们建立起来的新联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令人捉摸不透。请你们接受这个所谓有创造力的阶级!这个群体在生活方式上完全拥有自己的模式。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似乎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我不需要规范化的雇佣劳动关系,我鄙视领薪水的人,我是发薪水的人,因而我高人一等。
现在,这个以能力、交际、谋划为生活信条的群体试图把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引入社会。他们可以说构成了社会内部一个不安分的阶级,因为他们是在不再共享同样的社会道德感受力的情况下建立社会联系的。
迈耶尔: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是可以提出异议。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从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或环境的某种纯粹的差异化出发来观察问题,那么他就会说:不错,这个社会已经碎片化了。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们毕竟还面临着生存机会和生活保障的差异化问题。这里可以提出许多实在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如何才能重新获得保障?须知,保障是一项基本的要求。
布德:您说的完全正确。我认为,确实存在着复兴属于公共财富的文化的需求。同20年前相比,人们对此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感觉到,公共财富能使他们不折不扣地作为人而生活。同时,新型的公共财富起着某种作用,为了说明这种作用,福柯(MichelFoucault)发明了生物政治学这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它涉及美餐、清新的空气、对噪音污染的治理、对公共绿地的修建,还涉及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关怀儿童以及开展促使老年人增强活力的活动。
此外,福利国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后时期传统的福利国家以劳动这一主题为中心,关注的是在劳动者生病时继续发放工资,以及劳动者在企业经营上参与决策的权利。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福利国家把重心放在教育问题上。这不仅包含提供保障的理念,例如在出现失业、丧失劳动能力和陷入贫困时提供保障,还包含提供机会的理念,例如通过教育来获得机会。当今福利国家的鲜明特征是突出健康这个主题。就不平等这一难题而言,上述这一切都十分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群体,他们把劳动当作福利国家各种成就的基础。同时,我们的社会中也有上升中的群体,他们非常重视教育。在我们的社会中,正有越来越多的人相对来说享有特权,他们认为健康是他们在福利国家条件下首要的利益。人怎样在高质量的生活中逐渐衰老,怎样有尊严地死去,对这个群体来说,这些比劳动权利或大学学费问题更加重要。
迈耶尔:在学术性的政治语义学中,用来描述不平等社会秩序的一些宏观概念总是和某种评价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做。当人们谈起环境或社会时,听起来的弦外之音是各群体相互之间似乎漠不关心,分层的社会虽然强调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看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阶级社会这个概念听起来颇有对抗的意味,甚至是斗争的意味。那么应当怎样说明“碎片化的社会”这个概念呢?
布德:我想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张力的阶级社会中。之所以没有阶级张力,是因为再也不存在通俗的追求政治目的和社会伦理目的的集体化理念了。
迈耶尔:但是在如今的大讨论中,不是又产生了这种思想吗?
布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反对“斯图加特21”(Stuttgart 21)的抗议活动就是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一个实例。因为利益的诉求,包括共同利益的诉求,如今显然是以一种完全独特的能力结构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在抗议活动本身中的确有某种排他逻辑在起作用,一边是有能力的、发出抗议呼声的群体,另一边是没有能力的、只能低声抱怨的群体。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主席贝尔托德·胡贝尔(Berthold Huber)早就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他面对提出抗议的斯图加特市民发问说:在劳动领域和就业领域是否已根本不存在问题?这个关于自行架构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新问题甚至又被一些群体提了出来,这些群体觉得自身得不到保障,但是在提供劳务的无产者面前却不加掩饰地吐露出自负的言辞。
迈耶尔:您的著作《被关在门外的人们》选择了“告别希望”这个副标题。您是否仍旧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或者其意图不仅仅是在于煽动情绪?
布德: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煽动。因为我认为,在今天,社会公正的问题才在难以满足的意义上被提了出来。在整个战后时期,我们曾以为我们已实现了某种社会公正,因为我们社会的中间阶层已经日益巩固并日益扩大,至少在德国是如此。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的就是社会学所说的在雇佣制社会中起调节作用的道德。有了权利的普遍化,同时扩大了物质上的保障机会,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公正。
现在应当清醒地指出,这个模式之所以碰壁,首先是由于有些群体同生存机会分配的上述这一逻辑长久地和越来越严重地脱节;其次是由于出现了中间阶层向社会边缘发展的无序现象,有人尝试运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把握这一现象。
迈耶尔:如果不考虑通常的不平等和差异化问题,难道我们不应当尝试通过公众参与以及为所有人提供一定的基本设施来实现社会公正吗?
布德:是应当这样。社会公正的问题必须以下述根本思考为出发点:我们怎样在不平等已成顽疾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公正?战后长期推行的那种战略,也就是在人们面前掩盖不平等的那种战略,如今已经行不通了。
问题在于,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却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教诲:某些不平等的结构无论如何是不能通过政治措施而发生重大改变的。因而,越是如此,就越是需要复兴一种属于公共财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