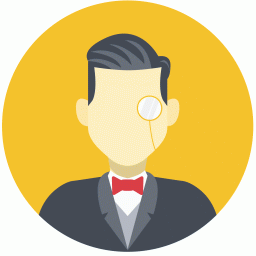告别夏楚二物:中国教育废除体罚的百年努力及论争
时间:2022-05-26 07:57:19

摘 要:“朴作教刑”是中国先民提出的,尔后成为教育上的一种指导思想;汉儒又从实践中总结出“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经验;宋儒再提出“教不严、师之惰”的绝对论调,经过历代的传诵,以至于传统教育离不开体罚,似乎无体罚则无教育,不知误导了多少家长,害苦了多少儿童。这一切到了清末兴学,才有些许改观,此后民国,进而共和国,民主教育的实施使其越发消退。从“倚重”到“怀疑”,从“收威”到“示威”,从“可施”到“不得”,是体罚与中国教育这百年来变化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它的所指也在不断扩大,证明人们观念的不断进步。简而言之,这一路走来步履有点蹒跚,颇为不易。
关键词:传统教育;朴作教刑;夏楚二物;体罚;民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55-05
资料表明,自清末兴学,中国教育就想与体罚说声再见,只是告别演讲做了多回,演词也在不断修饰,怎奈“有为在歧路”,加之“祖宗之法不可废”,这条路走得特别艰难。
一、传统教育体罚之盛
记载中国先民活动的典籍《尚书》中关于教育的笔墨并不多,在《舜典》篇却留下了一则影响千年的命题,即“朴作教刑”。汉时郑玄注:“朴,榎楚也。”唐时孔颖达又疏:“朴,榎楚也。不勤道业则挞之。”“榎”或作“夏”、“槚”,均同音假借字。《礼记·学记》中又有“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告诫。这样,中国教育便与“夏楚”脱离不得了。
家庭教育方面,自不待言,汉时司马迁就主张“教笞不可废于家”(《史记·律书》) [1 ],民间口头世代相传的“不打不成才”、“不打不成器”、“棒头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等训子箴言,《红楼梦》中宝玉挨贾政大板伺候的情节等等,都是这种教育哲学的注脚。
学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汉时王充曾回忆幼时在书馆中学习:“8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滴,或以书丑得鞭。”(《论衡·自纪》) [2 ]唐时刘知几也自述:“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论衡·自纪》) [3 ]宋时丁谓,祥符年间(1008~1016)做了大官,衣锦还乡时特地去拜访授业先生,告白道:“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 [4 ]这则成功育才的故事,似颇能证明“夏楚”之必要,在当地也成为美谈传诵一时。明清之时,风气似乎更甚。如王阳明对当时的教育深感痛心:“近世之训蒙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打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 [5 ]清时王筠对此也有怀疑,他认为:“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但当世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的,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呼,其果无罪耶?” [6 ]
然而这样的怀疑和担忧并没有促使教与学的方式有所改变,江苏无锡一带的学生们私下里会的传唱:“先生教我人之初/我教先生鼻涕拖/先生教我天地人/我教先生肚子疼/先生教我大学/我教先生赖学/先生教我中庸/我教先生屁股打得绯红/先生教我公冶长/我教先生睏在大坟上。” [7 ]浙江绍兴的周作人幼时曾熟唱:“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种葱。” [8 ]还有的地方则说:“上孟子/下孟子/打得学生钻凳子。” [9 ]个别学生也会起而“造反”,但也只是乘先生不在高声叫喊:“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干。” [10 ]家长们对学生的挨打,虽然也会心有不舍,但并不怨恨,反而很赞同,有的甚至表态:“先生,您打得好,不打不成才!” [11 ]因为自宋儒提出“教不严,师之惰”的推断后,通过民间的不断传诵,至明清已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于是“课少父兄嫌懒惰”,另一方面自然的“功多子弟结冤仇” [12 ]。如何化解这个矛盾呢?很少有塾师意识到通过改进教法来改变,而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们会在戒尺上刻上“一块无情木/单打书不熟/诸君若护短/希望莫来读”,另有版本为“一片无情竹/不打你不读/父母要纵容/莫要送来读”,虽然有的是竹板,有的是木板,用词上也有些许不同,但要表达的含义却是一致的:为体罚寻求合理性。
蒋梦麟自述幼时恨透了这种生活,曾有一番“壮语豪言”:“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待他至中年时再回首,觉得这种传统的教与学的组织方式“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如果不是东西交汇,被迫门户开放,这么一个安定的社会,恐怕很少会自发地发生变革。这种依靠体罚的教育,“给小孩子添些无谓的苦难,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 [13 ]
二、从“收威”到“示威”
东西交汇之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贤们对此情此景有了新的认识,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1896年)中就指出:“中国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缠足,毁其肢体;男者扑头,伤其脑气。”他认为“古之听讼,犹禁笞楚”,今“鼓箧之始,而日以囚虏之事待之”,这种“但凭棒喝”的方式使得学生“视黉舍如豚莅之苦,对师长若狱吏之尊” [14 ]。然而实践方面,注重体罚的理念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此前,清政府曾特地为首批留童举办过一所“预备学校”(1871年),据温秉忠回忆当时学校的监督是位“暴君”,力主体罚且严格执行。多年后,幼童们尽管怀念他,因为他强令读写中文,幼童中断留学回国后在交流上没有什么障碍,但仍然恐惧他手上的竹板 [15 ]。等到清政府立志兴学之时,对于这种传统、这种教与学所倚重的方式,也开始有了怀疑,只是前后态度有点微妙,见表1。
管学大臣最初拟具的兴学计划中,在蒙学堂(名为“蒙学”,按年龄计实已入小学阶段)章程地提出,教授儿童,应当“循循善诱”,不当施行体罚。整个计划由于年限过于冗长,未能实施,但这一要求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欲一扫千余年来的积弊。王阳明、王筠、梁启超身处各自的时代,对这种陋习能够有怀疑,已属非常难得,但怀疑和劝诫似乎并没有促使事情有所好转。如此,直言一声“不施夏楚”,其进步之大,可想而知。
只是真正实施的计划,即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对此进行了分解,提出夏楚对“13岁以上”不可再用,而13岁以下不用最好,用的话也不要轻易地用。至于“罚站”、“剥夺假期”、“剥夺自由”、“替代劳动”等后来被认为是体罚之列的,在当时则是允许的。从倚重夏楚到摈弃夏楚,变革的幅度可谓非常大。美好的理想若无法实现难免会变成画饼,或许是出于这种顾虑,管学大臣们的态度前后有了变化。即便如此,从“收威”到“示威”,也可以算作有比较大的进步。
三、从“可施”到“不得”
辛亥革命之后,政体有所变更,由专制走向共和,教育上亦有很大变化,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也废除了奖励出身制,还禁用了前清学部颁教科书等等,以便适应于新时代。对于体罚这个“小问题”,也提出了新的主张:“不得用。”见表2。
无论是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小学不得体罚的规定一以贯之,然而这并不表明,体罚彻底离开了教育实践。据孙钰的考察,当时教师对于儿童施行体罚,并没有城乡之别,乡间的私塾和新式学校沿用传统,自不待言,城市里颇具盛名的附属学校或实验学校亦不能免俗。只因法有禁令,故而体罚呈现出新的变化来:公开施行变秘密执行,杖打板击变拳捶脚踢,面向多数变针对少数 [16 ]。据李楚材讲,1932年间杭州一小学教师实施体罚,不甚酿成惨祸,把学生打死了,家长随即向法院进行了控诉,教师也被拘禁 [17 ]。这是最极端的,家长、教师和学校都不愿见到的状况。吴鼎将他见到的一般教师所施行之体罚,分成了11类:一为罚站,站在教室门口、课桌旁边或教室后面等;二为面壁;三为罚跪;四为打手心;五为捏耳朵;六为关饭学,中午放学不允许回家吃饭;七为关夜学,下午放学时,迟放儿童回家;八为罚做工,如抄写小字、罚做值日生等;九为罚黑屋;十为罚对面抵手,用于两儿童相打或相骂;十一为罚背红布条,于布条上写明犯错缘由,如“我迟到”、“我打人”,令儿童在学校或教室内走一圈或数圈 [18 ]。
从历史意义上而言,从“不可轻施”到“不得用”,可谓又有了一大进步。但是希望凭借这一条规定而能一扫积弊,却是万难的。总有家长对老师会这样说:“我的小孩子脾气太坏了,请先生们多加管束,他要是不听话,你们打好了,我决不责备你们的。” [19 ]这种性质相近的话传承了很多代。檀传宝老师上学第一天,他的父亲也很郑重地对老师交心:“调皮就替我好好打他!打他就是为他好,打他就是瞧得起我!”他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一位研究生的家长对他说了一段几乎同样的话,而家长还是位高级知识分子 [20 ]。21世纪尚存这样的观念与交代,更遑论20世纪及之前了。
整个民国时期的学校,与前清的相比,在对待体罚问题上,自然有不小的改进:“从前教室里摆列许多体罚的刑具,如戒尺、杖板之类,现在觉得这些陈列是与学校不名誉了” [16 ],但体罚还屡见不鲜。30年代儿童年实施委员会向教育部提出“小学废止体罚苛罚及解除一切束缚”的建议,引起教育界的共鸣。上海的《教育杂志》曾做了一期专题,收集了教育界孙钰、吴增芥等11人的意见,多系赞同废止,并提出替代训练的方法。教育部方面,于当年9月(1935年)以第13 361号训令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转知各地小学教育研究会,加以研究,并将结果呈报,至次年4月,苏浙湘鄂鲁晋豫闽陕9省和平津沪宁青岛5市都进行了汇报,教育部方面共收到170多份研究成果,但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依旧持保留态度,认为“根据事实,有时不得不体罚”。
教育部最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总结报告,对众人所理解的“体罚”(如上述11类)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将其分成体罚与苛罚两部。至于何谓体罚,部方认为“凡是制裁儿童,使身体受痛苦,促他改过自新的手段,都可以说是体罚”。依据工具的不同,可分为两种。见表3。
教育部研究报告指出,以上所列各种措施,大多直接有害于身体,应绝对废止。但“罚站”一项须具体分析:第一,教学时,教员提问,令某儿童站起回答;第二,儿童站起回答不出,教员让他先站着,且注意听别人如何答复(回答完毕久不令坐者属体罚);第三,儿童在排队行走时,某儿扰乱秩序,教员叫他站在队旁,等全队走完再叫他随队行走;第四,其他为维持秩序,偶然提出特殊儿童暂立在群外,不久就恢复他的自由。报告认为这些都不能算是体罚,属于现实情境中需要者 [21 ]。
至于苛罚,是指“凡制裁儿童,过于所应受的惩罚,使儿童受严重的刺激,都可以说是苛罚”,可分为4类。见表4。
研究报告指出,上述这些大多间接有害于儿童的身体精神,也应设法废止 [21 ]。对照清末的章程,“罚站”原不在体罚之内,现已涵盖于其中;“禁假”、“禁出游”、“罚做工”原是认可的,现也建议取缔。另外,教育部关于体罚的分类也不同于吴鼎的认识,如“挂红布条”,吴鼎认为属体罚,部方则认为属苛罚。此词建国后弃用,而改称“变相体罚”。
报告还分析了体罚产生的原因和对儿童的影响,以及取而代之有效训练方法等。随后教育部将报告印成小册,分发教育行政部门,同时通令“转饬各公私立小学,一体遵照” [22 ]。
四、从“部章”到“国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体罚也是坚决摈弃,为此中央教育部于1952年特下发一通知,表示:“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希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照指示,严格执行。”由此拉开共和国拒绝体罚的序幕,见表5。
指示下发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了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集中学习,并讨论所得。然而对于这一项国家政策,有些教师还认识不清,于是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之一《小学教师》开辟专栏进行了讨论。首先刊载了吴正礼的《我不同意绝对废止体罚》,理由有三:第一,施行轻微的体罚易使儿童改正错误;第二,家长方面要求严格管理;第三,便于维持课堂秩序组织教学。此后,全国有不少读者对此表达了意见。6个月内,编辑部收到1 749封信,除小学教师外,还有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教育行政干部、师范学校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其中主张废止体罚的有1 687封,同意体罚或“轻微体罚”的有62封。可见对这一问题,公意之所在。此后,编辑部刊发了讨论结束语,建议依赖体罚的教师们注意研究怎样培养儿童的自觉纪律,还应该好好研究在必要时如何适当地运用惩罚,以及好好学习书刊上介绍的教导儿童的方法 [23 ]。
这是“前十七年”间的努力及成绩,“”期间可谓毁于一旦。“拨乱反正”以后,学校重新恢复正常的教与学的秩序,随着入学人数的激增以及学校规模的逐渐扩张,借助体罚以维持课堂纪律的现象又重新抬头。此时,一方面是国际的潮流,另一方面是国内的要求,政府先后出台了《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一再明确表示“不许体罚”。由此,“废除体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部门之章到国家之法。前清的章程是“奏定”的,也就是经过“谕批”的,在“朕言即法律”的制度下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它主张“可施”。在《义务教育法》实施之前,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都是主张“废除”的,只是都由教育部出台章程或指示加以规定。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政策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是经过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的,此后教师运用体罚,不再是违规之行,而是违法之行。
五、应然与实然之间
只是,法律的出台并不意味着行为的立刻消失,因为它表示的是一种“应然追求”,而不是“实然状况”。笔者入学时,《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三法均已出台,然所见所闻及所体验之“当头棒喝”的经历十分寻常,即便到了初中,也有个别教师“心狠手辣”,时隔多年同学相聚仍能成为大家的话题——当时打得太多、太狠了,厌恶之情尤未减少。清末时期就说“13岁以上不可再施”,而我们当时早就过了13岁了,可还是难以逃避“夏楚二物”的威力。原本做研究不应该掺杂个人经历,为防止臆造而失去纯正,可挨打(或因行为表现、或因学习表现)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幼时读书的共同经历,或许城市里的学校会好一些。
随着法律的普及,意识的灌输,以及经过严格训练的师范生加入教师队伍,还有个别案例的警示,特别是因体罚而造成的故意伤害致使师生对簿公堂,共和国的学校与体罚可谓渐行渐远。这是莫大的功劳,自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另一方面却又难免矫枉过正,加之社会舆论的误导,形成了“学生不好管、教师不敢管或不愿管”的尴尬局面。一直以来的“教不严、师之惰”,如今成了“教之严、师有错”。新世纪以来教育界一直在讨论“教师有没有惩戒权”,以至教育部于2009年特地出台通知告知“班主任有批评权”,应该都属“过正”的表现。
纵观百年来废除体罚的进程及努力,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凝集了多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实现。从中亦可见“进步”的中性含义,当借助棍棒的方式被认为不够人道时,人们借用以手脚代之;当借用手脚亦被认为不合时宜时,人们发明了代替方法,民国时称苛罚,今日称变相体罚。只是“变相”一词过于含混,加上体罚的内涵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丰富,含义本身也在变化,如此“变相体罚”有时实在难以界定。而教育行政部门包括学校行政,对于此类现象往往只看结果,不管过程,责任很自然地落在了相对处于弱势的教师肩上。不管课堂纪律难以维持,并且妨碍其他同学的学习;管了又容易触犯红线,轻则受处分,重则丢饭碗,对教师来说,真成了一个两难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要为体罚唱颂歌,事实上唱的是挽歌,体罚当在淘汰之列,只是“变相体罚”的所指应当精确,教师的哪些行为属于“变相”,哪些并不属于,应当有一个精确的研究与划分,否则笼而统之,束缚了教师。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王 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龚育之.中吴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A].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6]璩鑫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7]无锡民歌.先生教我人之初[A].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8]周作人.父亲的病[A].周作人.知堂回想录[C].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
[9]刘金魁.私塾忆趣[A].政协洛阳市委员会,学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洛阳文史资料[C].洛阳:编者刊,2007.
[10]王建功.九十年间——王建功回忆录[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11]王质如.当年的私塾学馆[A].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崇文卷)[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12]郑板桥.教馆诗[A].郑炳纯辑.郑板桥外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3]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14]璩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15]温秉忠.一个留童的回忆[A].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童书信集[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16]孙 钰.对于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提倡小学废止体罚的我见[J].教育杂志,1935-12,25(12):87-88.
[17]李楚材.对于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提倡小学废止体罚的我见[J].教育杂志,1935-12,25(12):94-96.
[18]吴 鼎.对于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提倡小学废止体罚的我见[J].教育杂志,1935-12,25(12):96-100.
[19]吴增芥.对于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提倡小学废止体罚的我见[J].教育杂志,1935-12,25(12):88-90.
[20]檀传宝.论惩罚的教育意义及其实现[J].中国教育学刊.2004,(2):20-23.
[21]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国“小学废止体罚苛罚及解除一切束缚”的研究报告[J].基础教育,1936-11-1,1(12):674- 693.
[22]江苏省教育厅.废止小学体罚苛罚[J].江苏教育,1936- 09-15,5(9):178.
[23]本刊编辑室.体罚问题讨论会结束语[J].小学教师,195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