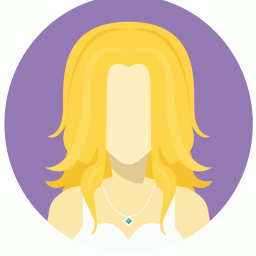文言文教学就是教学文言文
时间:2022-04-21 06:54:08

一、是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该怎么教,方法会有很多。但我想都要基于一个事实:这是文言文,而不是白话文;是中文,而不是外文。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是文言文,意味着文章是古代的,远离现代的,至少跟现代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跟中学生的关系是隔膜、疏离的,换言之,功利性差。而白话文跟生活关联度极高,如按照“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广阔”的理论,学生每天都在学习白话文,都在学习语文。至于外语,这完全是一种陌生的语言,没有生活基础,只有书本、课堂,实践性极低,但因为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诱惑,向往,使国人有了跟外国人交往的冲动,有了奋不顾身地去学外语的热情。文言文跟白话文和外文相比,难学、失落成为事实。
但文言文要考,这也是事实,并且占的比重还不低,约占基础分的四分之一。文言文的存在只是为了考试吗?肯定不是,有传承问题,有文化问题,有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等等。作为教师,你必须去教文言文,并且尽可能地去教好文言文,让学生能愉快地接受文言文。为了教好文言文,有些教师进入了误区,把文言文课上成历史课,上成思想课,如上《六国论》时,竟大讲战争形势和赂与不赂;上《陈情表》时,竟大谈孝与忠对现代的意义,至于“文言”和文章的主旨都成了附庸。课的可听性是强了,但课的“文言”性就弱了,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大概就是如此。虽然一篇文章可以从语文角度讲,也可以从历史角度、思想角度来讲,但前提是你是什么教师,你是语文教师,还是历史教师或政治教师。
如2004年上海高考历史卷中有一题: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期间,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清末诗人丘逢甲《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问题:(1)这首诗写于哪一年?(2)为什么“四百万人同一哭”?(3)“春愁”是中国古诗词中常见的词语,作者以此为题抒发了怎样的情怀?
这道题告诉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读诗词,但这是历史教师的事。如果一堂文言文课,你过多地担当了历史教师的角色,这不是对我们语文教师的强化,我以为恰恰是对我们语文教师的弱化。
我们要明确文言文和文言文教学这个事实,我们要明确自己所担当的角色。
二、我们需要共识
要教好文言文,我想要达成一个共识:充实和扎实。文言文的用语很简约,但内涵很丰富。教师要讲的很多,字词句、语法修辞、篇章结构、思想情感、历史文化,等等。如苏州大学陈国安教授所说:“丰满语言的两翼,绕到文字的背后,教会文学的思考,理解文化的人生。”文章是既定的,怎么教,其实也是教师学识修养的体现,因为这不仅是传授知识的问题,也是人格修养的问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非是讲教师对学生影响的深远。什么样的课才是丰富的,譬如说《春秋》是简约的,《左传》是丰富的,因为《左传》的丰富和引人入胜,人们自然地喜欢上了简约的《春秋》。也因为你的丰富充实,让学生喜欢上了简约的文言文。教文言文,要你懂得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的道理。
有教师在上《五人墓碑记》一文时,问学生:“呼中丞之名而詈之”中“詈”字从课本注释看是“骂”的意思,那么如果换成“呼中丞之名而骂之”行吗?有学生说:“‘詈’字比‘骂’字更文雅一些,更符合文言文文体特点。”但有学生表示反对:“‘骂’字好,‘詈’字虽然文雅,并且符合文言特点,却不符合人物身份。”为了让讨论能进一步深入,教师让学生在《词语手册》中找到了两个字的辨析:“詈”和“骂”是一对同义词,但本义有差异。“骂”指恶言侮辱人,《广韵》上这样解释:“骂,恶言。”“詈”表示在骂别人时罗列对方的罪状或缺点,《正字通》上这样解释:“詈,罗织其言以相谤也。”显然,用“詈”,意在显示了他们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和誓死不屈与之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此讨论分析,自然可谓丰富“充实”。这样的丰富“充实”,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更达到了理解课文的效果。
教师教文言文要充实,学生学文言文要扎实。学生学文言文很需要学外语的精神,通假字、实词意义、虚词用法、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等古汉语知识,都需要你花工夫去记。如果充实是内容的话,那么扎实是效果。说实在话,我们的扎实是不够的,在高一、高二,学生除了课堂上读了几篇文言文外,另外还读了几篇呢;要学生买一些课外书,大多是现代的小说、散文和所谓的满分作文,至于古代的,基本没有。这看上去是学生的问题,其实是教师问题,认为文言文花时多见效慢,现代性差,实用性低,学文言文不合算,等等。我想充实和扎实是学好文言文的两面,教师上课充实了,学生课后自然会扎实。如果教师上课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既不讲实词虚词,也不讲文言句式,那么如何让学生去学扎实呢!
三、“文”和“言”的思考
曾有相当长的时间,文言文教学是重“言”轻“文”的,但也不可否认,新课程推进时,在一些教师中出现了另一种情况,重“文”而轻“言”。这两种情况,其实是重工具性还是重人文性的问题。那么,文言文到底该教什么呢?我以为教“文”和“言”,即语言、文章、文化。具体说来,在文言文教学中既要重视基本的古汉语字词句的知识;又要注重文本的整体把握,赏析文章的篇章结构和写作技法;更要强调理解文本之后的思想情感和古代文化的传承和熏陶。以文章为中心,结合文章语境积累文言,进而体悟文化,使文言、文章、文化融为一体,使“文”“言”不分,“文”“言”并重。
“文”“言”并重,是一种理念,而不是教条。你想一下,一篇文章要讲字词句等语言知识,又要传授文化常识,还要教给学生一定的阅读技巧、写作方法等等,如果不分轻重,这肯定是不可行的。你应把“文”“言”并重这种理念贯穿在整个文言文教学过程中,课文有难易,年级有高低,任务有轻重,关键是灵活运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传记文,字词句相对容易些,可以少花一些时间;而牵涉到的人物可能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内涵,可以作一些发挥和联系。讲《鸿门宴》,文字上应该没有多少问题,其他方面教师大可以作些补充和延伸,刘邦、项羽的性格、作风等。如写景散文,字词句上的变化会多些,教学时就不宜快速,对有些词义的理解会出现见仁见智。讲《滕王阁序》,仅是文字疏通上就要花不少时间,因此教师在“言”上有必要加强。再如高中三年,也不宜一刀切,可分成三个学段进行,高一年级着重培养、提高释义能力,将重点放在文言文的词语、句子的准确理解上。高二年级重点放在文章的体悟和鉴赏上,高三年级则重在强化应试能力的培养。从现行的人教版教材来看,必修一至必修五是第一层次,更多的是在语言知识上;选修《论语》和《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是第二、第三层次,重在文章鉴赏上、作者理解上、文化传承上,其人文性也体现得最为充分。
落实在课文上,我想比较理想的文言文教学,理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废谁都不行,重谁也不行,至于把握的度,是一个教师的思想认识和教学水平的问题。
《赤壁赋》是一篇人文性很重的课文,如果弃掉人文性,而只讲字词句,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篇文章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看到乐观旷达的苏轼。同样,在这个板块中后一篇文章,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也是一篇人文性很重的文章,前些天就听了一节公开课,要求是一节课上完,他大概花了一半时间讲字词句,另一半时间讲人文,一半对一半,我以为这不是并重,并重是根据课的情况作恰如其分的安排,正如“折中”不是“中庸”。这堂课人文明显重于工具,是有失偏颇的。重人文并非是弃工具,工具是基础,人文是升华,是水到渠成。因为是同一板块,还可以让学生思考板块标题“感悟自然”的意义,这两篇文章都是写景散文,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我们在文章中读出了作者:一个是乐观旷达的,一个是执著孤傲的。联系这两人之前之后写的一些诗文,就会明白,苏轼在离开黄州到庐山时,写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如果联系一下苏轼的生活遭遇和他的生活态度,就不难明白写这首诗的用意了,你们怎样看是你们的事,可以看高,可以看低,我还是我,苏轼还是苏轼。柳宗元写《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千万孤独”,跟《始得西山宴游记》一脉相承,所谓“不与培为类”。两篇文章一比较,就会发现,同样的遭遇,不一样的反应,因为性格、气质、修养不一样,但都不影响他们的伟大。正如屈原在楚国灭亡时选择死,司马迁在受腐刑时选择生,我们不能因他们的不同选择否定他们的伟大,他们同样伟大。
四、于丹讲《论语》是特例
在我们那么看重“文”和“言”的时候,于丹讲《论语》,讲“文”而不讲“言”,竟大行其道,一时让语文教师瞠目结舌。有人说为文言文教学开了一个好头,因为这样教学,文言文的可听性绝对没有问题;也有人说为语文教师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不可能放弃“文言”而追求所谓的效果。我想于丹讲《论语》,正确地说不是在讲文言文,更不是在讲文言文教学。于丹一时红火,只是一时,不会像《论语》本身一样经典,可以千年而不朽。有人戏称她为“超女”,我想多少包含着对她的评价。于丹讲《论语》是特例,不能归到文言文教学,我想作为语文教师还是应该有明晰的认识。我们不因于丹讲《论语》而喜,也不因于丹讲《论语》而忧,文言文就是文言文,文言文教学就是教学文言文。
我们用文言文来教学,要让学生掌握通假字、实词意义、虚词用法、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等古汉语知识,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达成语文课程的教学目的。于丹讲《论语》,只是阐发己见,引发电视观众去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她的落脚点是观点而不是知识,是娱乐而不是实用。我们用文言文来教学,教材是例子。《师说》《六国论》《过秦论》等都是经典,学生学了这些文章,能有举一反三的功效。于丹讲《论语》是演说,所用材料是“引子”是“由头”,为了自己随心所欲地演绎和发挥,而真正的《论语》被异化,被“泛文化”。我们用文言文来教学,有对话场,可以多元解读,可以独立思考。一篇《赤壁赋》可以引起学生大讨论,对“主客对话”可以作不同的解读。“主客对话”是虚拟的,代表了作者思想中两个不同侧面的矛盾斗争;也可以说是实有的,“客”是道士,是杨世昌,说“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自然是最符合他的身份与性格。于丹讲《论语》是“独语”,有听众而没有对话,有独立性而没有多元性,有随意性而没有严肃性。中学里有选修《〈论语〉选读》,出版社编《教师教学用书》,或教师写《论语》方面的文章,引用的资料有朱熹《论语章句集注》,何晏、邢《论语注疏》,康有为《论语注》,程树德《论语集释》,南怀瑾《论语别裁》,等等,但没有于丹讲《论语》,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没有史料价值。因此,文言文只能是文言文,当文言文成了于丹讲《论语》时,已不具备文言文的本质;文言文教学只能是教学文言文,当文言文教学成了一个人演说时,已异化为娱乐和“泛文化”。我们的文言文教学可以多样化,诵读的串讲的,工具的人文的,传统的现代的,等等,但本质是不变的:这是文言文,这是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不是白话文,它比白话文更经典;文言文不是外文,它比外文更文化。文言文教学理应是语文教学中最受追捧的篇章,理应是课堂上的一份精美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