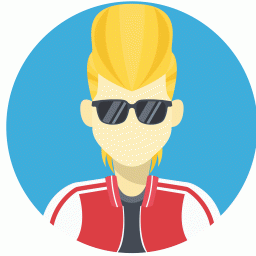自然是否享有权利?
时间:2022-10-07 08:30:24

摘要:通过对哈尼族《苦扎扎》等民间传说的现代解读,我们便能窥知,哈尼族传统自然权利观主要体现为一种动物权利观,换言之,哈尼族是“动物权利论者”,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具备权利主体资格,享有与人类类似的权利。哈尼族传统自然权利观奉行的是一种“基于差异性的公平原则”。
关键词:哈尼族;自然权利观;动物权利观;“基于差异性的公平原则”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自然权利”才进入环境伦理学的话语系统中。然而,现代人类只是自然权利理论的首创者,却非自然权利观念的最早拥有者。自然享有权利的观念很早便深植于像哈尼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的信仰体系中。通过对哈尼族《苦扎扎》等民间传说的现代解读,我们便能窥知哈尼族传统的关于自然的权利观念之大端。
一、自然享有的权利
在哈尼族的传统观念中,自然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生存权利、环境居住权利、法律和道德权利。这可从对哈尼族民间传说《苦扎扎》的现代解读中获得相关信息。
《苦扎扎》传说讲述的是哈尼族从游居到定居,从采集狩猎生产方式到农业生产方式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与动物界之间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
最先,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单方面地行使了自己的生存权利:“传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哈尼人从老林里走出来,在半山腰安下寨房,为了养活儿孙,就到山上去烧山开田。哈尼是勤快的人,早上烧山,烧出的山是九架;晚上开田,开出的田是九块,一天不歇地烧山,一刻不歇地开田。”
农业的出现是由于人口压力造成的文化适应,当人口发展到攫取性经济无法支持时,稳定的食物来源成为大的问题,正是这种需求导致了农业的产生。农业文明取代攫取性的采集狩猎生产方式是哈尼族文明史上的巨大飞跃,它使哈尼祖先拥有了比较稳定和充足的食物来源,告别了“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正式跨入文明时代。然而,农业文明的诞生和演进是以砍伐森林资源为代价的,从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第一次大破坏。在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比较发达的哈尼族先祖看来,这种破坏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侵犯和剥夺了动物兄弟的生存权和环境居住权:“烧山烧黑了九十九架大山,开田开红了九十九座山坡”;“这些动物被烧得脚跛的脚跛,手断的手断,糊头糊脑的。”由于人类生存权的满足是奠定在侵犯和剥夺动物的生存权和环境居住权的基础上,“就得罪了住在山上的大大小小的动物。”于是动物开始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通过法律的程序和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动物们依照普通程序将人类告到大神烟沙那里:“它们一窝一伙地挤到大神烟沙面前去告状。”大神烟沙隐喻的是仲裁人与动物冲突的一审法院的审判长。大神烟沙按照人世间通行的审判程序,认真听取了“方”――动物们的申诉:
住在洞里的老熊和野鼠说:“啊――阿波!这些哈尼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孙,不烧的山一架也没有了,不开的地一处没有了。烧山烧倒了岩洞,老熊没有住处了;开山挖坍了地洞,野鼠没有在处了!”
住在老林里的野猪、狐狸也说:“大神啊,我们受了无穷无尽的苦,哈尼烧山的火烟,秋得野猪一家老小去跳崖,哈尼烧山的大火,烧死了狐狸家的七个儿子!”
住在土里的蚂蚁、蚯蚓也来告:“阿波,阿波,我们死的时候到了!哈尼挖田,挖倒了蚂蚁七代的老窝,从今以后,蚂蚁天天搬家的日子来到了!哈尼挖地,挖断了蚯蚓的脖子,从此蚯蚓脖子上留下了褪不掉的印子!”
老鼠罗,蚂蚱罗,竹鼠罗,箐鸡罗,个个都来了,哼的哼,吼的吼,都说哈尼人要不得,要治治他们才行。
最后大神烟沙当庭作出宣判:“听着,九山九箐的动物们,我大神烟沙来下判断了:哈尼这样整你们,叫他们拿命来赔!从今以后,一年叫他们杀一个男人来祭你们死掉的兄弟,你们这些活着的动物,一年四季可以到哈尼的大田里去,拱通了田埂不要赔,踩倒了庄稼不要还!”于是,“动物们听见烟沙开了口,喜喜欢欢地去了。”
然而,一审判决是建立在哈尼族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同态复仇”的法律理念之上的,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它鼓动动物对人类实施以牙还牙式的疯狂报复:
从此以后,哈尼人倒霉了,大田里的庄稼天天被野物偷还不说,每年要杀死一个男人祭被烧死挖死的动物,从此哈尼的寨子里再也听不见笑声,老人为死去的儿子悲伤,女人为死去的男人痛哭。
在另一传说《兄妹传人》(二)中,哈尼先祖同样赋予自然以“同态复仇”的权力,并以自然实施了“同态复仇”的权力来建构和解释洪水神话:远古的时候,有一年天大旱,哈尼先祖为了度日活命,在树皮快剥尽、野兽快打光的情况下,下龙潭打鱼,几乎将鱼、虾等水生动物捕杀光。有一天,人们又将龙潭中一条大鲤鱼捕杀吃掉。第二天,天上下起了从未有过的暴雨,龙潭掀起一层又一层的恶浪,恶浪顶端出现一凶神恶煞的龙王,对着全寨人吼叫道:“你们吃了我的子孙,害了我的水族,我要让你们遭水灾,我要你们偿命!”暴雨下个不停,洪水淹没了大地,人类都淹死了,只有一家兄妹俩,哥哥叫者比,妹妹叫帕玛,钻进葫芦中逃过厄运。后来兄妹成亲,才使人类得以繁衍下来。这则传说中的“龙王”,实则是自然的代言人。
这种自然对人类实施报复的活剧在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上演。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论述的: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迭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对于自然的报复行为,世界各个民族有各种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自然通过报复行为表达出的权利诉求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结果人类与自然“两败俱伤”,最终“导致了奠定文明基础的自然资源的毁灭”,“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巴拉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是典型例子。另一种是尊重自然的权利诉求,与自然“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哈尼族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在行为文化层面,他们通过在刀耕火种农业中实行有序的垦休循环制、在梯田农业中保护神山和水源林,让森林植被得以恢复或保存;在观念文化层面,他们拟构出最高
的天神阿匹梅烟,并赋予其调解人与动物冲突的最终裁定权,其角色相当于终审法院的最高法官。
《苦扎扎》接着讲道:“哈尼的哭声和怨声传上了高天,震动了最高的天神阿匹梅烟。”她来到世上,调查取证,倾听当事双方的意见。她先到哈尼寨子里问明了原因,又到山上问那些动物。动物中分两派,一派以巴布腊西(鼹鼠)为代表,属反人类的强硬派,主张把哈尼人杀光;另一派以燕子为代表,属亲人类的和解派。燕子认为:“啊,不合不合,哈尼人是好人不是坏人。我在他们的墙壁上做窝,在他们的屋檐下梳头,他们从来不骂我,因为我帮他们捉拿田里的虫虫,让他们得丰收。你们才是害人的。泥鳅土狗,你们天天在哈尼的田里拱庄稼,哈尼人怎么会喜欢你们?老鼠,人家的谷子还没有饱满,你就去偷吃,人家怎么会不恨你?你们这些野物啊,哈尼人杀你们也是应该的!”阿匹梅烟在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辩论后,作出终审判决。他向动物宣判了惩治人类的办法:
好嘛,你们实在讨厌哈尼人,我就帮你们治他们。他们的谷子二、三月栽上去,五、六月间青黄不接,在谷子还不熟的时候――谷子一熟,他们吃饱肚子,你们就斗不赢他们了――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吊起来,拴在半空中打,把他们打得叫‘不敢了,不敢了’才饶……
又悄悄告知人类:
你们到了六月,就支起高秋,架起磨秋来,老老小小伙子姑娘穿起最好的衣裳来打高秋、撵磨秋,你们一面打,一面叫,叫得箐沟、老林里的动物们都听见,这样你们就可以不杀人祭祀,动物也不会来怪你们了。
在哈尼族看来,阿匹梅烟想出的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办法”,做出的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因为“一审判决”中采用的“杀人偿命”的裁量标准只适合于人类社会,并不适合于人与动物之问。而“终审判决”采用了一种新的裁量标准,即“基于差异性的公正原则”(下文将详述),从而使人类与动物皆大欢喜。从人类来讲,他们将杀人祭祀改为杀牛祭祀,同时将原本是惩戒性的、充满悲伤的“受罚”活动变成为欢乐的节日:“过苦扎扎的时候,人们穿上新衣裳,成群结伙地来到秋场上打高秋、撵磨秋,打秋的人一面打,一面欢乐地高喊:‘哦嗬!哦嗬嗬!哦嗬嗬!……’”。于是,“哈尼人吃也得吃了,欢乐也得欢乐了,就把苦扎扎定做自己的年。”从而维护了人类的生存权和合理利用自然的权力。从动物来讲,它们“看见哈尼人一个一个吊在半空中,被阿匹梅烟打得飘过来荡过去,像干天的树叶一样,站都站不住,哈尼人痛苦的叫声把大山都震响了。动物们非常高兴:‘嗯,还是阿匹梅烟的办法好,哈尼人啊,也给你们尝一回受苦的味道吧!’它们喜喜欢欢地回到各自的洞穴,不再来要哈尼人的人头。”从而满足了动物们惩治人类的权利诉求,从形式上和道义上主张了动物的法律和道德权利。
二、哈尼族传统自然权利观的现代解读
我们可以运用环境伦理学中的自然权利理论,对哈尼族传统自然权利观作如下两方面的解读。
其一,哈尼族传统自然权利观主要体现为一种动物权利观,换言之,哈尼族是“动物权利论者”,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具备权利主体资格,享有与人类类似的权利。这样的观念在对自然赋权范围及逻辑推理上与西方“动物解放论”或“动物权利论”有相似和相通之处。
自然能不能拥有权利?这是现代环境(生态)伦理学讨论的核心课题之一,“其中动物的权利问题又是环境伦理学试图打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体系的一个突破口”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旨在维护动物福利的“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皮特・辛格(Peter Singer)于1973年发表一篇题为《动物解放》的书评,从动物的感受性或者说感受苦乐的能力出发,推出了动物应享有道德权利的结论。他采用的是简单的三段论式推理:“大前提:凡是拥有感受痛苦能力的存在物都应给予平等的道德考虑。小前提:由于动物也拥有感受痛苦的能力。结论:所以,对动物也应给予平等的道德考虑。”韩立新先生进而将辛格的观点总结为:“既然动物也具有同人一样的感受苦乐的能力,那就应该享受同人一样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人这一特殊的物种作为一物是否享有生存权的指标。”该文从哲学上第一次论证了动物的权利问题,被称为动物权利运动的《圣经》。另一新型动物保护主义者雷根(T.Regan)认为,动物之所以能够拥有权利,是基于以下推论,“即人之所以具有权利是因为人拥有‘固有价值’,而人之所以拥有‘固有价值’是因为人是‘生命的主体(Subject of life)’,而动物也是‘生命的主体’,所以动物也具有‘固有价值’,因而动物也拥有受到道德关怀的权利。”他“并不认为所有的动物个体都是‘生命的主体’。按他的说法,一个个体要成为一个‘生命的主体’,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确信、欲望、知觉、记忆、对将来的感觉、偏好、苦乐、追求欲望和目标的行为能力、持续的自我同一性、拥有不依赖于外界评价的自身的幸福等等,尽管要依照这些条件对所有的动物进行划分、判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一般来说可以把‘生命的主体’限定在‘一岁以上的哺乳动物’这一范围内。”
以上基于人与动物在欲望、知觉、记忆、感觉、苦乐等感受能力或曰“感受性”的相似性来推演动物拥有与人相似的权利的逻辑推理路径,与哈尼族有相似和相通之处。
哈尼族传统的逻辑思维是一种“原始逻辑的思维”。他们最初并没有“把自己与自然分开,因而也不把自然与自己分开,所以他把一个自然对象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了对象本身的性态。……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亦即必然地,……――将自然的东西弄成了一个心情的东西,弄成了一个主观的、亦即人的东西。”他们心中的世界具有如苗启明先生所概括的如下规定性:
(1)万物具有人一样的生命,即“万物有生”,世界是个生命化的世界。动物、植物、山川星汉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类生命观支配着原始人的头脑。
(2)万物具有人一样的生活与活动,即“万物有行”,世界是活动化、生活化的世界。一些较原始的观念把这点表现得很清楚。这是一种类人行为观。
(3)万物具有人一样的心理、感情、观念和意图,世界是人心化、情意化的世界。这可概括为“万物有情”。
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祖”,自然万物是人类的亲人和伙伴;在自然万物中,动物是与人类最亲近、最相似的一个种群,具有与人相似的意识、需要、愿望和,是人类的亲兄弟。于是哈尼族在“将心比物”、“物我同一”的类比思维的驱动下,赋予动物权利主体资格,承认动物享有和人相似的权利,并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所形成的道德关系、法律关系投射到人与动物之间。
在对自然赋权的范围上,哈尼族有别于以克里斯托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为代表的“自然物的
法的权利”论以及以阿伦・奈斯(Arne Naess,也译作阿恩・纳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斯通于1971年撰写了《树能站到法庭上去吗》一文,首次从法律的角度探讨了自然物的权利问题,主张:“应该赋予森林、大海、江河和其他的所谓环境中的‘自然物’以及整个自然环境法的权利。”而深层生态学则主张将权利赋予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
其二,哈尼族传统自然权利观奉行的是一种“基于差异性的公平原则”。
尽管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自然权利的论证角度、理论预设和推理逻辑各有不同,从而形成各种理论流派,但有一点却是趋同的,那就是都强调自然权利与人的权和的平等性。如雷根和泰勒(paul W.Taylor)“分别从‘生命的主体’和‘生命的目的’的角度论证了动物或生物拥有被平等对待的可能性,并从‘权利论’和‘尊重自然’的角度推出人和动物之间或人和生物之间的平等性”。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又译阿恩・纳斯)将“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作为深层生态学理论的两个“最高规范”或“直觉”之一(另一个是“自我实现”)。“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的基本要义是:“在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有一种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有一种在更大的自我实现的范围内,达到他们自己的个体伸张和自我实现的形式的平等权利。”但这种自然享有与人平等的权利的理论却在实践层面面临严峻的困境:“如果严格地贯彻平等原理,人是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杀害其他生命的,更极端一点,由于人是惟一可以意识到道德责任的存在物,那么也许饿死会成为人的义务。结果是为了人的伦理成了杀人的伦理,这显然是违背了康德所建立起来的对人格的尊重原理,在现实中也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尽管自然权利论者给自己的理论加入相关“补充规定”,如雷根提出人类的生命优先原则,泰勒提出人类5个优先原则(自我防御原则、对称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补偿正义原则)等,但仍然无法使自己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其中最棘手的难道是如何协调人的利益和动植物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而遭到学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
哈尼族传统自然权利观奉行的是什么原则呢?让我们再次回到该族的民间传说《苦扎扎》上。天神阿匹梅烟对人类做出只有形式上惩罚而不用杀人偿命的“公正”判决,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哈尼人栽田种地是我教会他们的,人不吃饭是不会活的,不叫他们烧山开田,哈尼人不是要饿死了吗?”这其实反映了哈尼族在处理“人的权利”与“动物的权利”关系上所奉行的“基于差异性的公平原则”,即当人的基本生存权与动物的基本生存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人类可以依据食物链中的层级关系,为满足生存权而有节制地利用自然,包括猎杀动物。由于人类与动物间在利益诉求、情感表达、思维能力、行为能力、认知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先天性的差异,决定了人的权利与动物权利两者间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然而,哈尼族却力图在人的权益与动物权益之间寻找一种相对公平的解决路径,即在维护自己生存权的同时,通过各种禁忌(如忌食某些动物的肉、忌猎杀某些动物等)、仪式(如“苦扎扎”中将人类“吊起来”、“昂玛突”中的祭寨神仪式等)和行为(如旱地农作中的轮作垦休、保护神山等),表达对动物生命足够的尊重及内心深深的歉意,尽力取得被害方一动物的谅解(从上述“苦扎扎”传说中看,动物们也的确谅解了人类的施害行为,不再一味坚持“杀人偿命”),从而体现出哈尼族心中人与动物之间在权利上的公平观念。哈尼族的这种观念在另一民间故事《猴子敲石生火》中也得到反映。该故事讲:从前,人和动物是好朋友。当时人们住在深山密林里,靠采集野果充饥。后来一个叫盘赌的人,带领大家到大石洞里住。与人相伴的一只猴子无意地用石头相互不停地敲着敲着,被溅起的火星烧着了洞旁的枯叶。霎时,整个大地烧起一片火海,大树全被大火烧死,地上到处躺着被烧焦了的动物。“为了生存下去,盘赌对大家说:‘没有果实吃啦,大家还不如干脆吃地上的动物肉。’这时,一个叫玉兴明的人一听,就气愤地指责他:‘我们怎么能吃动物的肉,这跟吃我们身上的肉有什么不同的。’无奈,盘赌只好一个人从地上撕下一只被烧得黄黄的麂子的大腿,闭上眼,狠狠心就猛咬了一口。嚼着嚼着,他直觉得不怎么恶心了,相反越吃越香。因为人们都不同意吃动物肉,所以,盘赌也生气地低下头,一个人悄悄地吃着。人们开始时,都很厌恶地望着他,可是见他越吃越香,就迟疑地像盘赌的样子,撕下动物的肉,塞进嘴里吃起来。这样,人们才知道用火烧过的动物肉是那样的美味可口。这时,一群没被火烧死的老熊、老虎、麂子、马鹿刚路过,看见人正在吃它们同类的肉,就生气地问:‘你们为什么吃我们动物肉?’人们无奈地回答:‘唉,没有办法呀,果子搞不到啦,不吃你们的肉,我们人就要灭亡啦。’动物一听,吓得离开了人群。从此,动物看见人就怕去伤害它们,吃它们的肉。”
可见,哈尼族传统的自然权利观(具体而言就是动物权利观)既不指向“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指向“自然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而是指向了第三条道路,我们称之为“基于差异性的公平主义”。其基本要义包括:
(1)人类和生物(动物)都不是世界的“中心”,两者之间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并存的、互容的关系。世界真正的“中心”是制约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用老子的话讲就是“道”,用哈尼族的话讲,其代言人就是天神阿匹梅烟。
(2)由于生物(动物)与人类是同源共祖的兄弟姐妹和朋友,因而享有与人一样的权利主体资格,享有与人类相似的权利。
(3)动物的权利与人类的权利存在差异性,并不是绝对平等的。
(4)人类依据自然法则所确定的食物链中的层级关系猎食某些动物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但这种行为要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即遵守自然法则,合理地利用自然。
(5)人类应对自己对自然(包括动物)实施的伤害行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愧疚和不安,并通过各种方式(无论是行为层面的还是观念层面的)表达这种愧疚并尽力弥补这种伤害,以求得受害方一自然的谅解,最终与自然和解。
进而言之,公平正义的观念不仅应在人类社会中扎根,而且应该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