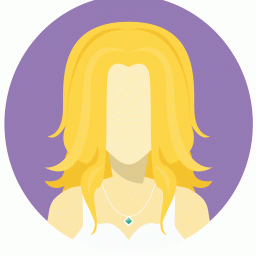国内生育立法的哲学诌议
时间:2022-09-03 11:44:15

作者:姜大伟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英国学者霍布斯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4]p31以卢梭、洛克、霍布斯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人都有使其生命、财产、人身平等受保护的权利,它不因年龄、身份、种族、社会地位而改变,只因出生这一自然事实而发生,这是一种绝对权,不受任何约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天赋人权”,又称“道德权利”、“自然权利”。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亦趋增强,一部分学者并非认为权利是自然的理性规则,相反他们认为,权利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则。英国学者边沁认为,权利的享有应该以法律为界限,道德本身对权利提出的主张并非权利。德国学者耶林认为,只有法律所认可并给予保护的利益才能称之为权利,权利就是法律上的利益。奥地利学者凯尔森则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规范“是一般权利的总和。权利仅仅是规范,它不是主体源生性能力,而是法律赋予的”[5]p9。他们认为,权利是实在且实际的,并非道德或自然的,那种“自然权利”永远只能存在空想与虚幻之中,权利只能由法律规定,它只能存在法律规范之中,于此才具有正当性,是谓“法律权利”。从表面看来,学者们关于权利是“自然权利”抑或“法律权利”的争论似乎不可调和,二者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实际上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二者仅是从价值层面对权利现象作的区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胜利的同盟国开始对法西斯德国的暴行进行深刻反思,发现违反人性、粗暴的法律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问题,于是又开始关注自然法,关注法律的道德性。美国学者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指出,法律具有自身的道德,他提出法律的内在之德”与“外在之德”的观点,若法律背离其“内在之德”即为恶法。[6]p32此后,无论立法者还是学者都以正义的观点来审视法律,这就为自然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创造了理论条件。就连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奥地利学者凯尔森亦不得不承认,“自然法秩序,果真存在的话,在其适用于具体社会生活条件时,必须要使之成为实在的,因为自然法的一般抽象规范通过人的行为只能成为具体的个别的规范。”[7]p433诚如其言,在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度,一个人在当他因其自然本性本应具有的权利在未被法律化之前,他不能主张这是他享有的自然权利而恣意妄为。换句话讲,即自然权利是权利的存在状态,它仅仅预示着成为现实权利的可能性,若想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就必须转化为法律权利,获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这种转化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从相对到模糊、松散和同质的状态向明确、紧凑和异质的状态转变的普遍过程。”[8]p102总之,在崇尚法治的文明时代,权利是一种观念(idea),也是一种制度(institution),[9]p2-3并且这种观念或者制度始终伴随为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然权利向法律权利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寻求自我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一言以蔽之,在文明的法治社会里,权利就是主体享有法律认可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自由和利益。
生育:从自然权利走向法律权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自然权利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于主体的相互交往活动所形成的权利要求之中,是社会物质关系阐发的法权现象。[10]p64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中,单一主体要想生存和发展,仅仅依靠个人有限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他必然参加并融入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同时在与该社会关系中其它主体交往过程中,主体的自我价值亦能显现。久而久之,单一主体便会意识到自己各种利益诉求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活动中才能满足,于是一旦其有利益诉求,便会求诸社会活动。由于这种目的性的存在,当单一主体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后,他必然要求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推而广之,当社会成员都有此种意识并将其付诸实践时,这种行使自己利益需求的表达方式,便形成了朴素的自然权利。由此可见,自然权利并非想当然地主观臆造,而是有其根源,它存在于活生生的物质生活中,是社会主体间物质关系的生动反映。从这种意义上讲,生育就是一种自然权利,是人类为了获取某种利益的自觉行为。从人类诞生之日起,生育便天经地义是人类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11]p87,在其诞生之初,生活环境异常恶劣,仅凭个人是不能抵御自然灾害的,人类为了生存,便成群结伴,共同生产,共同防御猛兽侵袭。此时,人类亟需扩大种群规模,于是,生育就责无旁贷地充当繁衍后代、充实种族的角色,尽管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性与生育的关联,但并不能否认生育是性活动的客观结果。生育为了满足人类生存需求而成为朴素的自然权利,但由于当时社会的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尚未形成权利意识,更不会认识到生育是基于人的本能可以满足包括生存需求在内的不同层次需求的自由决定行使的权利,生育权实际上处于无规范阶段。历史的车轮进入到私有制产生、家庭出现的农耕社会,一方面人类为了战胜自然、发展生产,亟需扩大人口规模,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分化、国家的出现,统治者为了加强与巩固自己的统治,迫切需要增殖人口,千方百计地鼓励生育、增殖人口,于是生育便成为法律调控的对象。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生育成为一种义务,夫妻实际上成为生育的工具,毫无自由选择可言,出于本能的生育权利被压制,我国有学者称之为生育义务阶段。[12]p36尽管如此,这仍是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是人们为了满足与当时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利益需求的客观结果。19世纪40年代,人类开始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使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在社会获得巨大的物质财富、人类物质需求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亦悄然改观。人们不在满足单一的物质需求,而更多的是利益追求多元化,人类并不必然为生存而积极追求生育,相反的是,对是否生育有了更为广袤的选择空间。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人类最主要的利益需求就是生存,通过不断地人口再生产来推动物质再生产以满足物质需求,而要进行人口再生产就必须依靠生育来完成。此时,生育的最大利益就是生产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维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生育权就是生存权,为了生存,必须积极生育,而且是尽可能多的生育。然而,在物质充裕的工业时代,人类物质需求可以不通过大规模地人口再生产而得到满足,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生育利益(效益)主要包括: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消费享乐效益、维系家庭地位效益、承担家业兴衰的风险效益、扩展家庭的效益。[13]p223-225然而,物极必反,生育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就不可避免地在生育主体间产生利益冲突,滋生矛盾。这种生育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下详述之。第一,生育利益的外部冲突。所谓外部冲突是指于生育主体之外的客观因素对生育主体的生育意志产生的影响和制约。19世纪40年代,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标志着人类步入了工业社会。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恩格斯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在过去二百年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任何时代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惟其如此,人类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生活方式得以改善,生活质量亦随之提高。但我们必须看到,科技的发展在赐予人类福祉的同时,亦带来了诸多至今都未能解决的难题。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4]p519诚如其言,人类在享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亦置身于发展所带来的困境之中。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近代以来,由于生活医疗卫生水平的大幅提高,人口死亡率大为降低,导致即使在人口出生率并未明显上升到情况下,人口数量亦呈自然增长的态势。一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人口从10亿增长到20亿花了100年(1830-1930年);从20亿到30亿用了30年(1930-1960年);从30亿到40亿仅用了15年(1960-1975年);从40亿到50亿只花了12年(1975-1987年);从50亿到60亿花了12年。[15]p260-261在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全国总人口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增长3.2%;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增长11.66%;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较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增长12.45%;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较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增长45.1%,这些足以说明人口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由于过度消耗却在日益锐减,生态环境亦在不断恶化:在资源方面,由于人类过度开发和利用,全球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在减少,土地沙漠化十分严重;森林大面积锐减,物种资源濒临灭绝;水资源出现严重危机。在生态环境方面,近年来,由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日益增加,向环境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亦明显增多,这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还导致了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下降,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和人口规模的膨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显而易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使得本已相对不足的资源愈为稀缺,因此只有统筹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才能破解难题,走出困境。据2009年召开的第26届世界人口大会证实:目前,全球人口增长的出现不平衡现象,90%以上的人口增长出现在欠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却在持续下降,特别是欧美和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已处于人口生育低水平。这将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人口处于持续增长的欠发达国家将会背负粮食供应、教育和公共医疗等多方面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加速全球气候变化,破坏地球生态系统,导致饥荒,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加贫困;但另一方面,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的发达国家将面临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现象严重等人口危机,对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因此,面对全球人口问题带来的各种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根据不同的国情,制定正确的人口政策,以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关系。然而新的问题随即出现,人口乃生育之结果,抑制或鼓励人口增长无异于干预生育。于此一来,普遍受社会尊重的生育权从此不再自由,因为它要受到政府抑制或鼓励人口增长而采取的一切公权力手段的干预。于此情形,“人口政策可能会将最隐私的个人行为置于政府的干预之下,从而使个人的自由与政府干预的权力相抗衡”,[16]p2生育利益的冲突随之而起,那种人类生育史上普遍受社会尊重的生育权将要受到公权干涉,甚至被侵犯。在法治文明的时代,为了使生育权不致遭受更大程度的侵犯,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给予其必要的保护是必要的,那么这种必要的保护手段就是使自然的生育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第二,生育利益的内部冲突。所谓内部冲突是指因生育主体的不同的生育观念对其生育意志产生的影响和制约。生育观念是人们对于生孩子的目的、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孩子的质量、生育孩子的性别选择、生育孩子时间选择等方面持有的情感、意识和信念的有机组合。[17]p202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它当属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生育观念亦应是对其生活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深刻反映,并且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以我国公民生育观念的变迁为例。在农业社会,一方面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科技发展更为缓慢,加之为了寻求生存,只能依赖生育繁衍种族以此增加劳动力的数量。然而,由于当时生育医疗水平相当落后,加之分娩知识十分缺乏,导致产妇与婴儿的死亡率畸高,人口规模难以扩张,因此人们就以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作为人口增殖的方法,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增殖工作,鼓励人们多生多育,并且规定最低婚龄,强制婚育;另一方面,浓厚的儒家文化刺激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儒家思想崇尚“孝”道,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如果无子嗣,就是不孝子孙,让祖上蒙羞。在这种“孝”道文化的熏陶下,生育成为传宗接代的桥梁,而尤以崇尚生男丁为盛。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一个家庭男丁愈多,威望愈高,它是人丁兴旺的标志。因此,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中国传统家庭无限向往的生活模式,甚至在时下的中国农村地区,这种生育观念依旧有着广阔的市场,深深地左右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在工业社会,生产力飞跃式的发展使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就为人类不必再为想方设法增加劳动力而积极追求生育创造了前提条件。相反,生产方式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现代社会,人们更加崇尚自由,价值观念亦趋多元化,不同的主体对世界、社会、人生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是非对错,每个人都有一套衡量的标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育观念亦由过去的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变,在地区之间、不同年龄层之间悄悄地发生变化。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早已改变了传统的生育观念,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依然相信多子多福,依然相信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在中年以上的年龄层中间,他们依然固守“生儿为了防老”的观念,而在年轻一代,则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有的人甚至认为,生男是名气,生女是福气。[18]p208我们知道,生育观念是生育利益的主观反映,主体生育观念不同意味着主体对生育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当生育主体之间对生育利益有着不同追求时,必将酿成冲突。例如,一对育龄夫妻,一方有生育意愿,而另一方则不想生育,在崇尚法治的文明社会里,强制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公允的。于此情形,生育利益发生冲突,如何解决?当权利主体内部发生冲突,欲求解决,非法律上之力不可,生育权由自然权利向法律权利转变,是彰显法律正义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生育权主体对生育利益有着同一诉求之时,生育权便平安无事,尚能得到生育主体的普遍尊重。但当权利主体对生育利益有不同诉求时,生育权便是矛盾斗争的统一体,生育利益便很难得到同时保障:在生育利益遭受外部冲突情形时,生育主体往往受到公权力的诸多限制,非但生育利益不能行使,而且若敢“越雷池一步”,超出限制时,便会受到相当严厉的财产或人身的惩罚;在生育利益遭受内部冲突情形时,往往一方丧失生育利益而保全他方,或一方采取非法手段迫使他方就范而成就自己之生育利益,诸如此类侵权情形,不断出现。我们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法治的文明社会,当朴素的自然权利尚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之时,可以全然不顾,但当它普遍受到社会随意凌落,侵权案件随处发生时,法律就不能袖手旁观了。生育权就是这样一种权利。在生育利益趋于多元化、生育利益冲突频然发生的今天,为了矫正生育利益,规范生育行为,保护生育权利,法律应当确认其为法律权利,将其纳入法治轨道中来,使合法的生育权益受到法律保护。总之,生育权应为法律权利,法律应当对这一法权予以确认,这是保护主体生育利益的必然要求。
我国生育立法之评析
我国生育立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1978年《宪法》首次将“生育”载入其中,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开生育立法之先河。紧接着为贯彻宪法的基本精神,1980年《婚姻法》第2条明确规定夫妻要“实行计划生育”。1982年修正后的《宪法》第25条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进一步明确,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亦有相同表述。1992年颁布实施、2005年修正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另外为有效贯彻施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我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都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如2002年《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颁行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也对保护妇女的生育权作出明确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经过近几十年的法律实践,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基本法,以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配套规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体系。这一方面不仅确认了我国公民享有生育权,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公民行使生育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生育利益。然而,我国生育立法仍然存在亟待完善之处。生育权是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我国生育权立法却显得较为滞后,长期以来,都是从计划生育的角度对公民生育进行管理与规制,直至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国家才从形式上肯定了我国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然而,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让人颇为遗憾。它一方面片面地强调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即妇女有中止妊娠的不生育权利;另一方面使生育权不具可诉性,仅作为一项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法定事由,使男性生育权无法得到保护。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是我国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规定片面保护妇女的生育权,似有违男女平等原则之嫌。同时,毋庸讳言,公民自然包括男、女性公民,该司法解释似乎违反了我国男性公民一样享有生育权,在生育权遭受侵犯时理当得到法律保护的规定。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男性公民的生育权益在遭受损害时得不到合理保护,那么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的明确规定,岂非具文?
余论
生育,从微观上讲,是个体实现自我繁衍和种族延续的前提;从宏观上讲,是人类进行人口再生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法制日益健全的权利时代,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生育行为理所应当成为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即凡公民,无论男女,都享有生育的权利,生育权应当得到平等保护。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对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作出修正,即建议修改为:“夫妻双方就生育问题应当协商一致,生育权平等地受到保护。夫妻双方因生育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各自采取措施,恶意促成违背对方生育意志之结果,造成对方生育或不生育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构成夫妻生育侵权;夫妻之间生育侵权,除应当按照《婚姻法》有关规定处理外,加害人在因侵权行为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