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肥瘾”的人类学研究
时间:2022-05-24 04:4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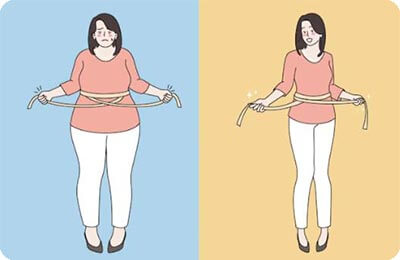
【摘 要】本文考察汉人社会的“减肥瘾”的表征特点,呈现“减肥瘾”者可能遭受的身心健康损害。通过对比“减肥瘾”与厌食症的异同,剖析“减肥瘾”的成因及“减肥瘾”者的群体特征。最终在于说明中国的各种减肥现象依然源自古典的“自然”观,却终因个人与群体的内在心理与外在实践之“整合”,产生了地方人们认可或不认可的多种身体文化展示。
【关键词】减肥瘾;厌食症;“自然”观;文化展示
【作 者】毕达,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专业博士生。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011 - 010
在信奉女子以“贞顺”“卑弱”为美的汉人社会,“瘦”自古就是评判女子身材的主流审美标准。从战国时宋玉邻家女的“肩若削成,腰若素束”① 到汉宫飞燕的“掌中起舞”② ,从宋代柳永笔下的“柳腰花态娇无力”到风靡明清时期的“扬州瘦马”③ 。即使是在千古闻名的以胖为美的唐代,也有“抱月飘烟一尺腰”④ 的美人。“减肥”因而成为一件令女子流血流泪、却至死不悔的要紧事。素爱排场的土豪石崇曾将沉香屑铺于象牙床上,令众姬妾踩在上面,体重轻盈的留不下脚印,就赏赐珍珠,而留下脚印者则命其节制饮食,以致闺中争相减肥,戏言“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真珠”⑤ 。春秋时期的楚灵王更是好瘦到了变态的地步,除了耳熟能详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楚灵王还以“细腰”命名章华宫⑥ ;其口味甚至从后宫蔓延到前朝,为了受到宠信,大臣争相节食,以至面黄肌瘦⑦ 。
如果说在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传统规制下,古人在求瘦的同时还不得不维持一定的理性,那么在消费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减肥”已经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宣扬中成为一种最普遍的身体实践方式。就如克里斯・席林在《身体与社会理论》,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安东尼・辛诺特在《社会身体》中指出的,在当代社会,作为个体主义的主要遗产,自我规划已被转变为身体规划。如今,“要么瘦,要么死”依旧是爱美女性的“座右铭”,“瘦”甚至逐渐成为女性获取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一种执念。因而,大多数减肥者的忧虑无外乎减肥无效或是体重反弹,对于瘦身成功者,则钦羡其成果、佩服其毅力、引以为偶像。殊不知,在瘦身成功者看似风光的“功成名就”下,很可能埋伏着减肥成瘾的隐患,因疏于防范而茁壮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贻害无穷。
学界尚未明确“减肥瘾”这一概念,笔者在本文中将“减肥瘾”界定为“强迫性减肥行为”。
一、研究方法
笔者采取了田野调查的办法,在健身房、美容院、大学、专业减肥中心、医院等现实场所,并辅以网络论坛,通过访谈的方式,访谈对象包括减肥者、医生、健身教练等,在共计83位减肥者中,发现了33位减肥成功者(成功的判断标准为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体重,且保持三个月未发生体重反弹)。男性减肥成功者7位,均未发现“减肥瘾”;女性减肥成功者27位,16位减重较多(大于5公斤)。这16位减重较多的女性又恰恰经历了较长的减肥时间(达到初始目标体重三个月以上)。令人心惊的是,其中12位都出现了程度轻重不等的“减肥瘾”。且“减肥瘾”难以轻易摆脱,在12位“减肥瘾”者中,迄今只有梓云、Lucky、宋思静成功戒瘾,而她们都是在饱受其苦之后才幡然醒悟的:梓云经历了一年的闭经,迄今未愈;Lucky出现低血糖、糖尿病倾向和皮肤过敏的症状;宋思静的膝盖受到不可逆转的磨损。这12位“减肥瘾”者的基本信息收录在表1中。
通过总结根据“减肥瘾”者的经历,笔者发现“减肥瘾”的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如下阶段。
在减肥者初次成功达到目标体重后,并不终止减肥,而是不断下调目标体重。
而后,减肥成为生活常态,减肥的手段成为强迫性的生活习惯。
最终,“减肥瘾”者对“瘦”的偏执性追求陷入“减肥瘾”无法自拔,导致包括身体机能失调、社会关系失常、精神状态失衡等后果。
二、“减肥瘾”的特征
(一)“减肥瘾”者偏执性求瘦
“减肥瘾”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减肥瘾”者在达到初始目标体重后,非但不停止减肥,反而不断下调目标体重。尽管理智的减肥者也可能下调目标体重,但“减肥瘾”者下调的目标体重与初始目标体重差别幅度大(5公斤及以上),或多次小幅度下调目标体重(3次及以上)。
就像布鲁赫(1978)、克里斯卜和汤姆斯(1972)以及拉塞尔(1970)指出的那样 [1 ]270,不顾一切地“求瘦”是与“怕胖”相联系的,担心体重回弹是下调目标体重的初衷。
然而,“减肥瘾”者从“为回弹留些余地”的心态逐渐演变为对“瘦”狂热的追求。心态健康的减肥者将体重作为衡量形体美的客观指标,清醒地认识到过瘦并不美,故而在追求低体重的过程中能够适可而止。然而,“减肥瘾”者的愉悦却直接来自于体重降低本身,形体美反而并不十分要紧了。尽管一些“减肥瘾”者也声称自己不断减重是为了“更好看”,其实却是她们自我欺骗地调整了形体美的判断。就像一度深陷“减肥瘾”的梓云,在最终走出这个心理误区之后承认的那样:“我那会儿只有79斤,骨头都突出来了,有点恐怖的哦。可是我那会儿真觉得这就是美,人家说(我)像骷髅,我就是不信。”“减肥瘾”者对体重的关注是过分而病态的,梓云告诉笔者,她曾经“每天都要至少称两次(体重),反弹了0.1公斤就痛心死了,这一天都脾气特别大,搞得家人莫名其妙的,而且一口(饭)都不会吃了。更可笑的是,要是轻了一点,还是什么都不吃,怕又长回来。”
在崇尚“自然”为美的汉人社会,减肥本是为了摆脱臃肿身材引发的愚痴、懒散的人格联想,然而“减肥瘾”者在追求“纤合度”的自然身材的过程中,却逐渐背离初衷,在对减肥本身的过分执着中演变为不合乎自然审美、过于骨感的形态。“减肥瘾”者逐渐脱离了理性控制,减肥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减肥瘾”的重要特征之二,即强迫性的生活习惯。
(二)“减肥瘾”者的强迫性的生活习惯
为了保证体重持续下降,减肥不再属于特殊阶段,而成为生活常态,减肥者开始养成“减肥式生活习惯”,主要包括运动习惯和节食习惯。
1. 强迫性的运动习惯
依靠运动减肥的“减肥瘾”者坚持高频率(一周五次以上)运动。尽管心态正常的健身爱好者也可能保持高频率运动的习惯,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运动并不能给“减肥瘾”者带来快乐,她们甚至可能认为运动是痛苦的。然而,运动却能够给她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安慰,一旦得不到这种心理安慰,她们就会产生罪恶感,被抑郁情绪笼罩。
宋思静在2015年8月初次达到目标体重后,非但没有降低运动的频率,反而增大了运动量。因为,“……就是害怕反弹,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不能前功尽弃。”
2015年12月10日,由于运动过量,宋思静膝盖劳损,然而,她并未遵照医生“休息几天”的嘱咐。12月12日,笔者在健身房又遇到她,她解释说:“昨天没来,我感觉自己肚子都凸出来了。”笔者问:“那你体重反弹了吗?”“没有反弹,反而还降了点儿,因为不运动,不敢吃东西,就吃了一片面包和两片柚子。可是我就是觉得肉脬脬(即松而肿的意思)的,可能是心理作用。反正不运动一下我就不安心。”
与宋静思的经历类似的“减肥瘾”者不在少数,她们都承认,自己“被运动绑架了”。坚持运动看似无伤大雅,盲目、过量的运动却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在笔者陪同宋思静就医时从医生处了解到,因运动导致的韧带损伤、软骨发炎、软骨撕裂、髌骨软化、骨关节炎等并不少见,不仅会妨碍患者的正常运动,在阴冷天气、酒精等的刺激下,也会隐隐作痛,这种运动损伤俗称“跑步膝”。笔者在访谈中还辗转了解到,因一意孤行跳绳减肥,一位高度近视的减肥者最终视网膜脱落,造成失明。然而,许多“减肥瘾”者对运动减肥效果的关注却远远高于对运动损伤的提防。就像梓云说过的:“我只担心运动得还不够拼命,就没办法燃烧热量了。”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减肥瘾”者还会刻意尽可能多消耗热量。小萱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2015年9月3日,小萱在赴与笔者的约会时略迟到了一会儿,她解释说:“我看时间还早,就绕了个大圈子,多燃烧些脂肪嘛,结果就迟了。”随后,小萱又充分利用笔者去洗手间的几分钟,爬了几趟附近的楼梯。从小萱的朋友处了解到,她平时“能不坐下就不坐下,站累了就靠着”,“晚饭吃好一定要出去溜达个把小时,大冬天的冻得都感冒了也不能例外”。小萱自己也承认,她坚守“能站着绝对不坐着,能走路绝对不坐车,能跑步绝对不走路”、“饭后一小时绝对不敢闲下来”、“坐下都不敢靠着椅背”的信条,否则“就觉得在浪费生命,很不安”。这样的运动习惯令小萱自己觉得“心很累”,而他人眼中的小萱已经“有些神经质了”。
2. 强迫性的节食习惯
“减肥瘾”者的强迫性节食习惯大多从过分关注卡路里开始。许多“减肥瘾”者都声称自己“由于经常计算食物卡路里,都成了数学高手”、“对各种食材的热量倒背如流”、“看到一盘菜下意识就开始算卡路里和营养成分”、“去超市买吃的,有包装的一定会本能的翻过来看营养成分表”。伴随着对卡路里的斤斤计较,一些“减肥瘾”者开始“挑食”:或是拒绝卡路里高或升糖指数高的食物,或是增加低卡路里食物和蛋白质(因蛋白质可以增加人体代谢水平,相比于其他营养素更不易令人长胖)的摄入。与一般减肥者不同的是,“减肥瘾”者以非理性的方式极端严苛地遵循自己设定的食物选择标准,一些“减肥瘾”者甚至依赖某几种特定食物或采用一成不变的食谱,这种偏执的进食方式被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描述的厌食症少女形象地描述为“仪式性的”:“我的食物被称量,依照热量多少来进行控制……我恐慌商店是否没有我要的那种牌子的脆面包,我恐慌我是否不能在同样的时刻,仪式般地进食……”[2 ]81“减肥瘾”者严格执行这种强迫性的进食规则,一旦被打破,就会恐慌、焦虑、不安。
安易的进食原则是“高蛋白”,即使是在旅途中,也不惜代价遵循:“去旅游什么的,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哪一餐没有蛋白质,比如前两天去黄山,山上伙食好贵,一只鸡卖三百多,他们好多人就点个素菜下饭,我还是得每餐都吃蛋白质啊,结果算下来旅游一趟钱都花在吃饭上了。”
Sally的进食原则是“无油蔬菜”,为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她甚至无法正常交际。因餐馆少有符合原则的食物,她“饭局能推就推,推不掉的之前要纠结好几天”,以至“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因为跟朋友出去都不吃东西,久了朋友就觉得反正你也是不吃的,干什么都不用叫你,叫你就是扫兴,甚至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不存在的”。长此以往,“减肥瘾”者越来越难以融入社会。甚至令常人感到愉悦的消遣也不再带给“减肥瘾”者快乐。她们“害怕逢年过节”,因为“每逢佳节胖三斤”,本来兴致勃勃的旅游她们也开始瞻前顾后,因为“伙食没办法安排,怕破功”。减肥已经成为她们的心理负担,剥夺了大部分生活乐趣。
强迫性的生活习惯除去带给“减肥瘾”者运动损伤、营养不良的身体损伤,还会令她们沉浸在抑郁的情绪状态中难以自拔。
就像约翰・洛克所谓的“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3 ]1,持续性的挨饿本身就会激发负面情绪。就像梓云说的:“我几乎被食欲折磨到走火入魔,每天满脑子都是食物,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逛商场时路过飘香的面包坊,或是隔着玻璃看到餐厅里别人有说有笑、大快朵颐。我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四肢无力、出虚汗、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简直如同一个每天都在强颜欢笑的小老太太。”
Sally也说自己:“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看到有人吃蛋糕,觉得她们才是幸福的,是完整的,而我就是个残废,多吃一口苹果都觉得犯罪……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盘算转天早上吃什么,饿得睡不着觉,睡着了做梦都在吃。”
“减肥瘾”者在这样的情绪下,大多有过“不喜欢斤斤计较的自己”,“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减肥这件事儿上,甚至忘了怎么好好爱自己”的描述,陷入抑郁中,而她们唯一的快乐来源唯有体重降低带来的满足感。于是,“减肥瘾”者越来越痴迷于此,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三、深度“减肥瘾”的恶果
(一)“减肥瘾”伤害女性的生育能力
女性在体脂率过低的情况下,会发生月经不调甚至闭经的情况。22岁的梓云在持续节食9个月后,开始月经不调,3个月后闭经。经诊断,梓云的闭经正是因节食导致子宫缩小,子宫内膜变薄。梓云对节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表示不可置信,医生的解释非常通俗:“你身体燃料不够用,要活下去就要牺牲某部分功能,可以说,你的子宫被‘分解’了,保证其他功能正常。”在使用芬吗通(一种刺激子宫生长的激素药物)两个月无效后,医生成倍增加了药量。对于梓云对副作用的担忧,医生说:“副作用肯定会有的,但是这样下去你的子宫会萎缩,最终失去生育能力。”历经5个月的西医治疗,梓云的病情却丝毫未见好转。医生解释说:“你(病情)的根源是太瘦,你要是一直不肯长胖点,就一直都好不了”。最终,梓云只得转向中医。同时,在家人的强迫下,梓云不得不开始增肥。2015年7月,梓云开始服用中药,此时体重为43公斤。2015年12月,梓云的体重上涨到49公斤,在药物和营养的双重作用下,她的病情终于初见起色,尽管B超结果显示内膜厚度仍旧只有0.1mm,子宫却终于开始变大。至此,梓云的闭经已经整整一年,这对于一位育龄的女性来说,损伤是难以估量的。
在陪同梓云就医的过程中,笔者从医生处了解到,因减肥导致闭经的年轻女性并非个例且 “有的(患者)为了怕雌激素长胖,居然不治了”。笔者还邂逅了另一位因“减肥瘾”闭经的少女,在使用激素类药物几个月后仍旧没有效果。医生给她开出“益母草颗粒”试图改善她的病情,她询问医生药里是否有糖(因为冲剂一般都是甜的),且因而犹豫再三才去拿药,当看到上面写着“无糖配方”后,她才舒了一口气,并表示如果是甜味的冲剂,她不会使用。
(二)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
从心理层面讲,“减肥瘾”引发的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是难以摆脱的梦魇。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医生科普项目的定义,神经性厌食症指个体通过节食等手段,有意造成并维持体重明显低于正常标准为特征的一种进食障碍,严重患者可因极度营养不良而出现恶病质状态、机体衰竭从而危及生命。
神经性贪食症则指反复发作性暴食,并伴随防止体重增加的补偿及对自身体重和体形过分关注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进食障碍。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不可控制、冲动性地暴食,继之采取防止增重的不适当的补偿。
“减肥瘾”引发神经性厌食症,并同时引发神经性贪食症的过程,循着梓云的经历可见端倪:“我只喝清粥配咸菜……五六天之后,我的食欲却越来越大:我从小不喜欢蛋黄,但那个时候看到放置太久已经风干的蛋黄都会馋到想哭。我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从两碗白粥就能饱到四碗、甚至六碗,明明对粥已经没有任何胃口,也撑到胃痛,还是停不下来。可同时,当体重没有变化的时候,甚至控制白粥的量,最苛刻的时候只喝一碗飘着几颗小米的米汤。”
后来,梓云放弃了 “清粥减肥法”,转而较为温和地控制总卡路里摄入,却开始出现厌食症:“吃什么都要想一下热量,就算饿得不行了,想想少吃这一口就能瘦得快一点,就一点儿都不想吃了。这样发展下去越来越夸张,索性什么都不敢吃了,只敢吃蔬菜,不然就会被罪恶感折磨,一定要剧烈运动和断食。”
然而,食欲是人的生理本能,尤其是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食欲和理智的抗争也不是每一次都是理智获胜:“就开始‘偶尔’控制不住吃好多,有一次,我居然忍不住吃了两整包白面包片,其实吃到半包的时候就已经饱了,但知道热量已经超标,脑子里就只有‘之前的努力全毁了,明天重新来过,今天先吃个痛快’的念头。”
为了不妨碍减肥的效果,梓云也选择了最“有效”的补救手段,即催吐:“有一次去吃火锅,就控制不住了,回去后撑的好难过,觉得自己好失败。就催吐了。催吐之后罪恶感没那么重了。谁知道催吐才是噩梦的开始。后来我就依赖催吐,本来暴食次数没那么多,现在想着‘吃多了就会去吐’,反而暴食次数越来越多。”
阿雅对自己神经性贪食症的描述则更为形象:“每天吃了吐、吐了吃,不是馋,不是饿,就是一种依赖,不用嚼,直接塞就可以了。我每顿都吃很多,到后来去厕所一弯腰就吐了,吐了觉得好饿,又继续吃,恶性循环。在人前,我又瘦又漂亮,伪装得像个正常人,可是我从来不敢跟别人一起吃饭。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难过,说不出的难过,除了吃,我对什么都没有热情。”
戒不掉的贪食症令她们困惑,进而产生“害怕这样的自己”“很难过”“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恨自己”“讨厌自己”甚至“想去死”的情绪。暴饮暴食再催吐,首先失守的是自制力,接踵而至的是自我否认和自我批判。这与“减肥瘾”者追求的自我认同感南辕北辙,对于她们而言无异于心灵的煎熬,长此以往难免自暴自弃。
1.“减肥瘾”与学界的“厌食症”存在相通之处
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从各个方面解读过厌食症。学术界一般并不严格区分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以“厌食症”一并涵盖。费纳将“厌食症”的临床症候和症状规定如下:第一,发作年龄在25岁之前;第二,体重至少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第三,没有可以解释厌食症的病例;第四,没有其他已知的情感性心理紊乱表现;第五,至少有下列病症中的两种――闭经,胎毛症,心跳缓慢,行为失常,贪食,催吐。[4 ]
与“减肥瘾”类似的是,厌食症也基本上是女性特有的,只有十分之一的厌食症者是男性[5 ],且厌食症发生在女性发育期和绝经期之间,更准确地说,厌食症发作的典型年龄是15岁,大部分病例都在25岁之前。[1 ]269
可以看出,厌食症与“减肥瘾”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学界对厌食症的一些解释同样适用于“减肥瘾”,尤其是二者高度相似的成因。
“减肥瘾”的成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追溯。
一方面,激发“减肥瘾”者减肥动机的直接原因就是改善外形,从而获得社会认同。
古时美人务必骨骼清奇、细颈削肩就与父权制社会下女子以“专以柔顺为德”① 的“卑弱”社会定位有一定关系。尽管现如今,弱不禁风的病态瘦已经被灵动窈窕的健美瘦代替,但“胖”被形容为“痴肥”,而“瘦”意味着开朗好动、不贪口腹之欲,已经成为共识。因而“瘦”不仅是“美”的重要标志,还与人格魅力发生了联系。“妇女的形象象征她的性格。肥胖的女人不仅仅外形臃肿,也说明她失去了控制。不受约束的身体就是不受约束的道德的表现。控制妇女的身材就是控制她们的个性,是一种权威行为,旨在维护父权制社会下理性的公共秩序。”[1 ]279
与之相似的是,厌食症的成因之一也是求瘦以获得社会认同:以父权制价值观的支配地位和父权制对女性的压制是公认的引发厌食症原因之一 [6-8 ]。
特纳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自我是一个再现的自我,其价值和意义通过个体的身体外在形态和形象,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个体的身体形象,被归因于个体。”[1 ]34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外在美一向受到更高的关注。尤其是苗条身材这一标准,对女性的要求也比男性更严苛。这也是“减肥瘾”者和厌食症患者绝大多数为女性的原因之一。
尽管社会认同可能是减肥者开始减肥的初衷,却并非“减肥瘾”和厌食症形成的直接原因。因为,在过度减肥的情况下,病态的“皮包骨”身材已经不再符合社会主流审美,无法带来社会认同。
另一方面,“减肥瘾”和厌食症都应追溯到更深入的原因,即征服和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
Lucky的“减肥瘾”经历就是个极好的例证。Lucky是某直辖市的外企高管,已逾不惑之年。在健身教练的鼓励下,她于2015年4月尝试学习游泳,历时12天就基本掌握了要领。得益于对运动的不懈坚持,尽管期间出现几次波动,Lucky的体重整体呈下降趋势。
在学会游泳之后,Lucky开始出现“减肥瘾”的征兆。尽管她的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她表示:“现在健身是我的第一要务,今天午休只有一小时,但我还是去游了泳。”
最初,Lucky的成就感不仅来源于体重下降,还来源于掌握一门新技能:“我曾经以为我不可能学会游泳。我都四十好几了,事事都开始走下坡路。可是我居然学会了游泳,我战胜了我自己,我的人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可能超越现在的自己,我的生命还有可能更加大放异彩,我可以继续接受新事物,我可以继续前行,而不是被岁月淘汰。”
2015年6月中旬,Lucky出现了皮肤过敏的情况,经诊断与泳池消毒成分有关,因而不得不暂停游泳。游泳不再能带给她成就感,但体重不断下降更长久地满足了Lucky的自我掌控欲望。因而,她“反而比以前运动得更多了”。
于是,Lucky也越来越着迷于减肥。“除了健身房,我还爬楼梯上十五楼,因为怕别的(即除去游泳之外的有氧运动)运动量不够,会反弹。如果哪一天没有成果甚至略有回弹,我就会很不开心,想尽办法也得降下去。” 减肥后期,由于其他有氧运动方式收效甚微,Lucky不顾皮肤过敏的风险,又开始坚持游泳,爆发了更严重的过敏,出现水肿,由于喉头水肿甚至无法正常讲话。
令Lucky深陷“减肥瘾”的正是那种“掌控自己体重、佩服自己毅力”的感觉。这同样也是厌食症的成因之一:Lawrence指出,“厌食症患者试图通过对身体的压抑以‘达致一种精神境界或至善’”[6 ]。
希拉・麦克劳德的自传《饥饿的艺术》也记载了自主选择的饥饿如何在早期引发一种昂扬和独立的感觉,厌食症患者沉迷于自我控制的中。然而,身体却会随着厌食的进程产生新的自主的自我,从而越来越难以控制,随着对身体的愈发苛待,终至厌食症产生。[9 ]就像Hepworth和Turner将厌食症与儿童一丝不苟地遵从强加于他们的礼节仪式和道德准则类比得出的结论:二者给自己定下的规则都是无法胜任的,因而势必会导致自我放纵,随后又难免产生一种罪恶感,反而更想严格遵守,引发更加强烈的饮食控制和锻炼。[10 ]137
之所以厌食症患者和“减肥瘾”者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特纳给出的解释是:“现代文化可以描述为自恋文化……厌食症患者对外观的耿耿于怀完全可以看作一种极端形式的现代自恋症。因此,厌食症是一种神经官能症式的普遍的‘生活的方式’,专注于跑步,健美,饮食保健,监视体重,以及精打细算的享乐。”与厌食症相似,“减肥瘾”者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将减肥这场痛苦的持久战坚守下去,得益于她们痴迷于“苦中作乐”的“精打细算的享乐”――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她们津津乐道的“精明”的“高品质”生活方式。即使她们在生理上是不适的,在心理上却能得到满足。[1 ]292
然而,这种心理满足感仅仅是假象。摩格尔通过对比佛教的禁欲与厌食症中发现,身体的苦行并不是由它的需要引向个人的自由,而是导致精神的奴役。[11 ]“减肥瘾”者也是从征服身体开始,当身体越来越难以掌控,“减肥瘾”者过度关注体重,终至被身体左右,精神上反而越来越空虚、抑郁。
2.“减肥瘾”与厌食症的区别
尽管厌食症与“减肥瘾”关系紧密,却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减肥瘾”发展到深处可能引发厌食症,但并非所有“减肥瘾”者都一定出现厌食症。即使是深度“减肥瘾”引发的厌食症,也并不一定如学界研究的厌食症一样,既囿于理智而缺乏食欲,又抵不住天性而暴饮暴食,同时伴随催吐等补偿。
一些“减肥瘾”者单纯地拒绝食物,而未并发暴饮暴食。笔者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口中得知,一位年仅16岁的小姑娘通过节食的方式瘦到不足40公斤,由于体重过低,严重威胁到健康,无法正常生活,医生的鉴定结果是“如果再不吃东西,她会死掉的”。然而,在病态的减肥心理趋势下,她却仍旧不肯正常进食,甚至连医生开出的药丸,她都要端详再三,询问“你们的药丸是不是含有面粉,如果是的话我不能吃”。医生只好通过给她注射营养液的方式维系她的生命,至今无法正常生活。
另外一些“减肥瘾”者暴饮暴食却并不需要催吐等补偿。例如,刘曦晨因节食而食欲旺盛,但她的解决办法不是催吐,而是选择能量密度低的食物满足食欲:“我只吃蔬菜,生吃或者白煮,煮都不敢煮太过了。但是我一开吃就停不下来,跟上了发条一样。昨天晚上我吃了一头西兰花、四个西红柿、一大颗白萝卜,都是煮煮吃或者生吃,算起来热量只有200多卡,可是你知道我胃撑的有多大吗?像怀孕一样大,吃过饭我站起来都觉得一坨铅块坠在那里,都痛。镜子里面光剩下一个肚子了。那些东西好吃吗?其实不好吃。我就是管不住自己。”Ellen与刘曦晨类似,都属于食量超常、热量偏低型的贪食症,她说:“我的暴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改不了了。”“忘了七八分饱是什么感觉,脑子里面已经没有‘饱了就要停下来’这个指令。”
食量过大而不催吐表面看来并无大碍,然而“减肥瘾”者大都是爱美女性,而饥不择食、暴饮暴食本身就是不美的行为,所以《论语》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正折射出所饮所食之物以及饮食的仪态都与人的风度气质挂钩。因此,“减肥瘾”者的心灵实则饱受煎熬,甚至产生自厌自弃的情绪。Ellen说:“我曾经家教很好,吃饭很优雅。可有一次我跟我爸吃饭,后来他犹豫了好几分钟,还是问我,‘你现在吃饭怎么那个样子’?然后模仿我,狼吞虎咽的,很夸张。我当时很生气,可是自己心里知道我就是那样,那么丑,那么恶心。”
第二,厌食症和“减肥瘾”者的高发群体不尽相同。
刘艾梅的自传《孤独》[12 ]认为厌食症高发群体为社会上很成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她们因对自己的无权无利状况感受尤深,常常感到不能承受的个人失败感和欠缺感。刘艾梅正是她们中的一员,而饮食控制是她“第一次展示完全独立的力量”。因“我的饮食是我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生活的一部分”,她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无独有偶,布鲁赫在《金笼子》中也将厌食症解释为中产阶级家庭内的一种斗争,受到过度保护的女儿力求更大程度地控制自己的身体进而控制自己的生活 [13 ]。她将厌食症女孩比作“金笼子里的一只麻雀,太平淡、太简单,不足以享受家里的奢华,而且被剥夺了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因而试图通过饥饿逃出“笼子”。然而,出于反抗父母控制的节食却导致受制于身体的结果。
然而,“减肥瘾”者绝不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年轻女儿,而是涵盖了更广的年龄层和社会阶层,如Lucky就是一位事业风生水起的独立女性,控制体重绝非“减肥瘾”者唯一能够自控的。
厌食症患者之所以多为年轻女性,与她们社会经历少、生活单调无趣有关,但“减肥瘾”循序渐进、不易察觉,即使是比较理智、年龄较大、社会阅历深的减肥者也并不一定能够幸免,这就使得“减肥瘾”格外难以提防。
李铭芝已介知命之年,是国内某著名高校图书馆系的大学教授,她的专业背景决定了她对信息非常敏感,善于也乐于汲取知识。无论从学识还是从阅历来推断,李铭芝都应当是一名非常理智的减肥者。诚然,在减肥的初期,她既没有迁延不前,也没有急于求成。在决定减肥后,她首先利用各种渠道获取了足够的相关知识,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目标后,她制定了结合运动和饮食调控的非常合理的减肥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体重从未发生意料之外的反弹。
然而,在达到目标体重后,李铭芝也不能免俗地陷入了“减肥瘾”。2015年8月16日,李铭芝开始减肥第20天,她的目标体重是55kg,即使是对于这个目标体重,她当时也并未抱有完全的信心――“我今早的体重只是略有下降,60.3kg,终于有望进入60kg以下了。我的目标希望到55kg,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年纪大减肥就比较困难呀。”
随着时间的推进,李铭芝在减肥上越来越得心应手,解决了许多曾经看来难以克服的难题,比如食欲问题。“记得上次和我的一个学生聚餐,她为了保持身材一口甜食都不吃,我当时钦佩她的自制力,可是心里认为‘她那个样子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反正我做不到,也不想做’。可是到现在我也很排斥甜食,是一种本能的排斥,甚至一点也不痛苦。”(2015年9月27日)
“今天在H市开会,晚饭是宴席,吃完饭不久又被拉去宵夜,我基本不吃,但看其他同志吃得欢,感慨这就是世间胖子那么多的原因啊!”(2015年10月20日)
至此,李铭芝开始出现习惯性节食,且她十分热衷和享受节食的过程――当然,这种享受并非生理上的,而是心灵上的。
“我们学校后门外有条小吃街,目测各店铺卖的吃食都是些香气四溢的高卡食物。在这里吃东西绝对属于堕落行为。我中午吃食堂,下午讲台上站三节课,其实肚子已经有感觉了,但我对这些吃食毫无吃的欲望。注意,我说的是吃的欲望而非食欲,这是两样的,吃的欲望受理智控制,食欲是生理反应。我就目不斜视地穿过后街来到K蛋糕店,买了一个全麦吐司作为明天的早餐,为自己的不堕落mark一下。”(2015年12月11日)
可以看出,李铭芝从为了减肥拒绝甜食、宵夜,再到将这种拒绝本身当作个人品质的体现,并且从自我认同中得到乐趣,已经将注意力从保持身材转移到了减肥本身。即使是在平素冷静睿智的大学教授身上,“减肥瘾”的苗头也已经初见端倪。“减肥瘾”难以察觉,直到“减肥瘾”者的身心出现了明显的损伤,才得到重视,此时却往往已经为时晚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性别上看,“减肥瘾”者与厌食症患者仍旧几乎都为女性。尽管女性在当下的社会地位已经显著提高,控制体重早已不是她们唯一能够左右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社会影响力依旧难以与男性相提并论,控制体重因而仍旧是女性满足征服欲的手段之一。这很可能是“减肥瘾”和厌食症一味纠缠女性的合理解释之一。
四、结论
通过对“减肥瘾”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获得社会认同往往是减肥的初衷。与欧美多元化的审美标准不同,“瘦”几乎成为当下汉人社会的审美文化,“锥子脸”“马甲线”大行其道,“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更是成为全民参与的“炫瘦游戏”。因而,虽然关于厌食症等的研究始见于欧美,在如今汉人社会几乎人人都曾试图减肥之际,却有相当一部分的欧美人士对自己的身材听之任之。
然而,通过控制体重满足控制欲则是减肥成瘾更根本的原因。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即使在欧美,关于罹患厌食症的少女骨瘦如柴,几乎难以维持生命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尤其对于社会话语权较弱的女性,在减肥中尝到成就感的甜头之后,难免迷失理智。因而,无论中外,无论老幼,“减肥瘾”群体始终与将女性定位为弱者的文化认知相伴相生。
第二,同为使用后天手段改变外貌的身体实践,不妨将减肥与整容进行类比。就像求美者虽诉诸非自然的整容手段改善外貌,目标却是美得“自然”一样,减肥者的出发点本也是追求纤合度的自然美。这里的自然不单单是指不加人工干预,还是“某种秩序”的体现,如和谐、对称和合适等美学标准。因而,“通过整容改变身体,旨在对失序的不自然身体进行矫正,却无意挑战既有的身体秩序”。[14 ]“减肥瘾”者的初衷也是合乎一般审美认知的“自然”身材,在实践过程中却因种种社会和个人原因产生偏执心理,审美尺度逐渐背离健康的自然美。正所谓“物极必反”,过分的瘦削是病态的,不符合审美秩序的,也就不再是“自然”的。 至此,“减肥瘾”者的外在和内在都陷入畸形之中。
就像洛克说的:“凡是身体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3 ]4不过,文化的限定作用,最终在于说明中国的各种减肥现象依然源自古典的“自然”观,却终因个人与群体的内在心理与外在实践之“整合”,产生了地方人们认可或不认可的多种身体文化展示。一种学术介入性的观点由此认为,“减肥瘾”者以极端的方式保持了完美的身形,但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受到损伤为代价,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文中访谈对象均采用化名)
参考文献:
[1]布莱恩・特纳. 身体与社会[M]. 马海良,赵国新,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2]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3]约翰・洛克. 教育漫谈[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4]Feighner,J. P.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use in psychiatric research[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72(26):57-63.
[5]Palmer,R. L. Anorexia Nervosa[M]. Harmondsworth,1980.
[6]Lawrence,M. Anorexia nervosa―the control paradox[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79(2): 93-101.
[7]Chernin,K. 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M]. New York,1981.
[8]Orbach,S. Fat is a Feminist Issue[M]. New York ,1978.
[9]Macleod,S. The Art of Starvation[M]. London,1981.
[10]Hepworth,M. and Turner.B.S. Confession:Studies in Deviance and Religion[M]. London,1982.
[11]Mogul,S. L. Asceticism in adolescence and anorexia nervosa[J].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80(35):155-175.
[12]Liu,A. Solitaire[M]. New York,1979.
[13]Bruch,H. The Golden Cage:The Enigma of Anorexia Nervosa[M]. Cambridge, 1978.
[14]方静文. 变身――现代中国美容整形的人类学研究[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4.
A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O THE
WEIGHT-LOSING ADDICTION
Bi Da
Abstract: “Weight-losing addiction” refers to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losing weigh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ing pursuit of low body weight, exceedingly strict diets and excessive exercise. People addicted to losing weight a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physical dysfunctions and mental disorders, such as amenorrhea, anorexia and bulimia. By comparing the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weight-losing addictionand anorexia nervos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weight-losing addiction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addicted to this symptom. It aims to address eventually that the various phenomena of weight-losing in China come from the classicalconcept of natural beauty. Although initially triggered by this concept, the unique Chinese culture of body including “weight-losing addiction” is shaped by their special psyche and practice.
Keywords: weight-losing addiction; anorexia nervosa; concept of natural beauty; cultural dis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