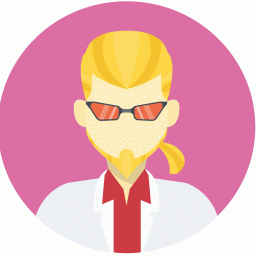电影《白鹿原》的历史空间与身体叙事
时间:2022-10-19 02:33:34

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讲,电影所表现的物理空间与背景设置并不局限于本身意义,必然会与社会、历史、政治等相关,因而创作者对空间的多层面处理和表现,必定以与之联系的深层文化意义提升作为旨归。电影《白鹿原》就具这种明显的空间意义提升特色,作为地理空间意义的白鹿原被引入历史空间意义构建;同时,电影中作为欲望与社会双重属性的身体,在与空间的相互关系中显现出独特的叙事意义生发与深化作用,成为解读电影《白鹿原》电影叙事的两个重要角度。
一、安置过去:作为历史空间的白鹿原
空间作为电影叙事的载体,是“它总的感染形式”、“最重要的东西”,不仅涉及故事的背景,而且往往与形象塑造、主题思想联系在一起,正如多宾所言“凡是影片中围绕着人的那些东西——大自然、实物、环境——有时只不过是动作的地点,是影片中事件展开的真实的背景。但是环境又往往担负着另一种更为广泛的形象和思想的任务。人的周围环境以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整个影片或影片个别场面的主题”①;同时,由于空间表意的多层面性,电影空间的分析往往不局限与自然的物理空间层面,在更大的程度上与文化层面相结合,因此对空间的研究也往往与空间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重点。电影中的白鹿原,是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的统一体,见证、经历与安置在时代洪流发展中的事件与记忆。
与原著更为宏大和广阔的故事背景相比电影《白鹿原》将封闭的地理空间作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一方面集中表现白鹿父子两代人间的故事关系,对原著的复杂人物关系进行了约束与凝练,另一方面将原内外的历史事件以一种经历和见证的姿态予以展示,更符合了电影视觉形象要求,也成为对历史和过去的“安置”空间。白鹿原作为一个承载的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在电影中显示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封闭性,第二是典型性。
首先,白鹿原是一个封闭空间,这个封闭空间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与承载者,也是传统文化下影响下的待开发空间。电影中对原内与原外的标志十分明显,白鹿原的牌楼、河流成为电影叙事空间表现的标志物。电影对白鹿原封闭空间内的建构是电影塑造的主体,对原外空间的描述相对较少,但内外的对比是其叙事张力之一。相对于外来力量,自上而下的力量而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鹿原与族人是被动的,片中诸如民国建立消息的得知、军阀的进入等外面的世界对白鹿原的冲击都是以与空间的标示紧密相关。而以鹿兆鹏、黑娃等人为代表的源自白鹿原内部的力量也是从空间层面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挣脱,原著中白孝文对自己的后来的妻子说过这样的话“谁走不出这原一辈子没出息”可视为白鹿原作为文化空间挣脱的一个注脚。电影中鹿兆鹏、黑娃、白孝文都以不通过的方式离开白鹿原这个封闭的文化空间。此三人作为先进文化追求者、普通农民、封建宗族继承者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对白嘉轩、鹿子霖为主要代表的父辈传统封建宗族文化进行自觉的或被动的反抗与背叛,而这种反抗与背叛又被置于历史发展的舞台,因而形成白鹿原作为叙事空间上的巨大张力,也成为电影重要的着墨构建之处。
电影中对原内外空间的意义开掘十分明显。原外空间虽未重点描述,但作为原内空间的对立空间含有有着重要意义。不论是同质还是异质,空间都是身体与思想的安置与归宿。鹿兆鹏两次离开白鹿原都是从河水为界,第一次是对抗封建婚姻、找寻自由而离开,原因被鹿子霖分析是由原外求学导致;第二次是国共合作失败“血换来的明白”后暂离国名党势力占据的白鹿原,在影像表达上,河的存在成为他离开白鹿原的地理分界,从画外音的隔河相对到与黑娃的河边话别,作为空间隔离物的河流在电影中多次出现。黑娃对父辈鹿三生活模式的反叛也是以空间的背离开始。他不愿像父亲一样做白家长工而选择离开白鹿原去做麦客。在另外一个空间里,以卧羊(与白鹿原牌楼相对)作为标志的原上又是同质的封建礼教文化空间。黑娃以对白鹿原的背离而得到了与田小娥的结合,却因另外一个空间同样的封建文化压迫而回归白鹿原,他们的婚姻不为正统封建礼教所容,于是就寄身于远离村庄的窑洞空间。白孝文离开白鹿原是同白嘉轩决裂之后,先是败家,变卖了自己在原内的立身空间——房屋和田产,后来是卖身当兵被拉走,他的离开也是以河为地理背景。他们的背离成为对以白鹿原为主体空间自我审视与反思的建构,也是白、鹿、黑娃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历史语境中对传统封建宗族文化的不同角度的冲击。
其次,对白鹿原原内的表现上,电影的空间设置有着典型性场所特点。祠堂、牌楼、戏台等场所成为具有明显的隐喻意义的历史文化空间,容纳了电影叙事结构中的主要事件。新近的空间叙事转向为场所的历史叙事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菲利普·J.埃辛顿认为“历史是过去的地图,其基本单位是场所”、“‘场所’以种种方式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它们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它们只能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以发现、阐释和思考”②通过关注“曾经发生过的”空间来“安置过去”,场所成为历史叙事中构建过去的重要空间。从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为混乱与隐晦的阶段,各种势力对封建制度倒塌的舞台上争相上场,对于电影白鹿原来说,事件的发生在哪些空间存在物中生发意义成为电影叙事构建的重要部分,电影通过祠堂、牌楼、戏台的歌典型的场所的展开,将历史叙事与宗族空间联系在一起,也就将人的存在与历史进程共通置于特定空间之下。于是“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③”电影中牌楼、祠堂、戏台为标志物的空间反复出现,成为历史的场所来完成影片的整体构建显现出巨大的叙事张力。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对场所空间的强调及其内部意蕴的挖掘都被放在重要位置。对白鹿原内部空间的开掘上,作为仪式性与公众性的场所(以祠堂、戏台、牌楼为代表)往往成为故事的张力空间。在电影中,白鹿原的牌楼电影中多次出现。所起的作用与转场的段落衔接相关,是时间流逝和白鹿原空间存在的标志物,也是白鹿原历史承载的视觉表现者,作为场所的白鹿原安置了1912年到1938年间的历史,其中对祠堂和戏台的空间建构充分体现了场所作为安置过去的叙事功能。影片中戏台及其前面的广场空间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如皇粮被抢回原、鹿子霖“革命”当官回原、军阀征粮、农协审判乡长、田福贤回归、日本轰炸白鹿原等均是从这个空间中安排事件、生发意义。无论是台上还是台前,戏剧式的将白鹿原经历的各种历史事件和力量交替予以集中、形象的展现,颇有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势头,与历史发展进程遥相对应,成为家族版的近代史。祠堂这一场所同样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作为封建宗族伦理的建筑存在,乡约碑前集体朗诵、白孝文身体两次受罚、黑娃捣毁祠堂、白氏父子谈论生育、族人探讨为小娥修庙等均是在这一场所展开,通过这些事件的安置,从侧面对历史和个人的经历与记忆进行空间化处理,集中表现封建宗族文化与人性间的压制与冲突关系,成为叙事意义构建的重要场所。
通过白鹿原封闭空间的构建与典型场所对历史事件的安置。电影《白鹿原》通过空间设置完成对故事背景的交代与叙事张力的生发。当然,这种空间的安置最终还是以事件本身的呈现来展开故事,而在电影《白鹿原》的故事结构中,有关身体的叙事贯穿在场所安置中,成为该片叙事的另一重要特征。
二、身体叙事:作为人欲望和社会属性的双栖地
除了场所对历史的安置,电影中人物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也是该片叙事意义构建的重要层面。相对原著而言,电影淡化了白鹿两家的恩怨对立,却将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封建制度倒坍的背景之下,丰富了电影的意义内涵。对空间的突出是以典型场所作为重点来展开的,而对人物、事件的意义构建则是以身体叙事作为主要手段来进行的。
身体是欲望的合法空间存在④,也是环境中的主要表现对象。故事的展开离不开环境和人,从身体叙事的角度来说就是离不开空间和身体。这里的身体意义已不是先前人们认为的意识的附着物,不是低下的应当被压制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身体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属性,而理性和信仰才是身体上的附着物。身体通常以欲望作为实践的动力,只要有身体就有欲望,它无处不在发挥着作用,无时不在生产现实——包括精神意识和思想感情。不难理解,‘思想感情的主人是身体’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它还给每个人欲望的身体以合法性”⑤如此以来,身体与欲望结合在一起,成为身体叙事分析的必须,人物情感的产生也与身体欲望密切相关。片中白嘉轩直且硬的腰杆、被吊在戏台上的肉身、鹿三的辫子等等都因与“身体涵义”而充满了隐喻意味。电影《白鹿原》中欲望、身体、文化空间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制约关系,一方面身体作为社会的存在与所处空间在文化层面上要保持一致,空间成为身体存在的地理、文化依托;另一方面,欲望的身体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空间压制下的身体在涵义上不相一致,身体叙事层面上展现了欲望与文化空间的对抗与挣扎。身体对电影空间建构的叙事张力因而得以表现。《白鹿原》中,作为欲望与文化承载的双栖地,身体的空间关系处理是电影叙事的一大特色。祠堂、窑洞、身体(或附属物)等都成为欲望与文化争夺、制约、对抗的空间所在,尤其是田小娥,成为盘活和贯通整体电影叙事的关键架构。
先看作为公共空间的祠堂与身体之间在叙事处理方面的设置。作为封建宗族文化的化身,电影中仪式性的事件完成均是在此空间内完成,当众性与对肉体施刑是它作为封建制度下惩罚的特点,祠堂成为公众性和施威的场所;同时,这个空间排斥对离经叛道者身体的进入,借以制约、边缘异己的观念与主张。比如其中祠堂内白嘉轩对白孝文的两次体罚。第一次是儿童时候因看动物,因为违反了“非礼勿视”,被体罚的白孝文被白嘉轩训以“啥叫礼义廉耻啥叫仁义”;第二次是因为与被宗规所不忍的田小娥私通。两次受罚成为孝文身体与封建礼教间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儿童时因顽劣无知犯诫,身体遭受痛苦并被封建文化空间所压制,欲望身体不能得到满足与延续;成年时因欲望驱使而与小娥私通受罚完成对封建文化空间的决裂,田小娥的怀孕标志着对他欲望释放了的身体存在的肯定。作为封建时代末世衰落涵义外在表现,电影对白嘉轩这位“腰杆很硬很直”的封建族长延续自己时出现了问题是通过白孝文作为家中独子的身体存在强调的,也是在祠堂倒地的乡约碑前,白嘉轩希望白孝文要继续香火,在得知白孝文使不出男人的“豪狠劲”时建议用冷先生开药来完成身体延续,因为孝文当时的社会身份既是自己独子也是白鹿原的族长。而白孝文“不能”的身体的问题正是源自封建礼教的心理问题。“裤子”成为他封建礼教观廉耻的遮盖,当他时则不能完成男人欲望的满足。他对裤子的依赖成为最明显的隐喻,这种被羞耻道德所压抑的身体成为其欲望的障碍,也使得他的身体在空间中不能继续延续自己。而在与白嘉轩决裂之后,“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放弃了传统封建道德约束的身体成为反叛传统礼教压制的象征,同时也从身体上找回了自我——田小娥怀孕了。同样的制约与对抗也体现在黑娃和田小娥身上。田小娥因为欲望而放弃自己举人妻子的社会身份与黑娃结合,也承受了作为夫权的的身体酷刑(夹手、吊打),他们的婚姻不能进入祠堂这个公共空间,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得不到封建宗族礼教下的社会空间的承认。他们所安身的窑洞在这里成为被打压、被边缘同时又是与祠堂相对抗的一个空间所在。故在“革命”后,黑娃带领田小娥等人最终进入祠堂并捣毁它的乡约碑身,完成自由的身体存在对封建礼教文化的破坏。在祠堂空间的体罚和排斥体现了封建时代惩罚的特点:在公众空间对肉体惩罚,以示宗族礼教规约威严;同时在公共空间内,排斥个人的合法性,完成对个体空间的威胁与压制。而影片中的故事发展正是从封建礼教空间中的个人身体的欲望挣扎和对抗来完成的。
再看对田小娥身体的叙事设置。田小娥作为电影盘活整个整个叙事关系的人物,因身体欲望而推动故事发展。不想跟鹿三一样命运的黑娃觉得走出白鹿原并与田小娥相遇。对两人描写在电影中同等场景相比占据了更大的篇幅,是对田小娥身体描写中最为华彩和浓重的一部分,二人从相遇到在结合,电影通过身体在不同空间(房间、田间)的描写,展现了逃离白鹿原封闭空间的身体与被封建婚姻制度所压抑的身体之间浓重的。作为自由恋爱的代表,黑娃和田小娥的结合被新文化的化身鹿兆鹏所赞扬与接受。两人安身的窑洞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田小娥的身体空间的延伸。在这里,黑娃与她精心维持彼此间的存在,黑娃以出卖体力来维持生活,而田小娥对黑娃说“即使你开窑子我也跟你去”;黑娃离开后,鹿子霖作为“匪属”能够脱掉保障所相约的面孔在小娥的炕上哭泣,也试图在她身上寻找慰藉,田小娥的身体空间成为他欲望的避难所和反击工具,凭借小娥身体对白孝文的吸引鹿子霖完成了对白嘉轩的道德攻击。而对白孝文来说,窑洞是田小娥的身体引导下自己身体欲望实现的空间。这个空间成为身体对封建宗规的对抗,当看见孝文从小娥窑洞里走出后,白嘉轩挺直如同牌楼一样的身子轰然倒下。白孝文进入窑洞空间导致自身肉体的惩罚以及与父亲的决裂。他对父亲的反抗也是以自己在封建宗族空间的退出来实现:他不再是族长,同时变卖了自己的土地和田产,继而将之挥霍与赌博与抽大烟以及与小娥的狂欢之中。在得知小娥怀有自己骨肉之后,为了维系生存,他去要舍饭,向鹿三要馍,继而以15大洋出卖自己身体,希冀在当时得以维系小娥与自己的身体存在。但在封建制度之下这种空间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田小娥最终被自己的公公、主子白嘉轩的忠实长工鹿三所杀,电影中有这样一幕,杀死小娥临走之前的鹿三将嘉轩撑在窑洞上的柱子撤掉,而窑洞这个边缘空间也就轰然消失。田小娥死后,由于忌惮瘟疫,对田小娥骨殖的处理也展现了身体在空间延续的不同理念。乡民由于害怕而顺从,要为田小娥建庙来供奉,鹿子霖则试图以此来取代白嘉轩成为族长;而白嘉轩则从对立的角度来建一座青砖六角塔。庙与塔作为一个空间形象展现了对小娥身体的不同态度:一个是要为之塑像供奉;另一个则是将之烧成骨灰用塔来压制。原小说中并无田小娥怀孕的情节,电影中此情节的设置一方面为白孝文为换取自己骨肉存货卖身离开白鹿原做交代,更重要的是孩子作为身体的延续成为对封建宗族文化的控诉。进入私人身体层面的欲望实现最终使白家香火延续,但却与礼义廉耻无关。在建塔时对嘉轩得知小娥怀有孝文骨肉的刻意强调,也从身体(母子骨灰)与空间(镇压之塔)之间的对立来表现白嘉轩的封建宗族文化本性:宁可影响后代风水(身体、空间)受损也不能对离经叛道身体的容忍与妥协。综观来看,从身体的欲望与社会文化属性出发,田小娥身体不仅构架了影片的主体叙事,还承载了更多的象征意义, “是土地的象征,是地母的象征,代表着受礼教所压迫的一代女性的形象⑥”,深化了影片的内在意义。
综上所述,在电影《白鹿原》中,小说宏大的背景与复杂的的人物关系经过改编得到了约束和集中,凸显了小说《白鹿原》的空间和身体意义并将之作为电影叙事构筑重点。以田小娥作为贯穿故事的主线,通过作为欲望和社会双重属性的身体,电影叙事将小说整体的故事构架连接起来,并赋予了不同人物以性格个性和关系张力;与此同时,电影将个人、家族故事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将白鹿原同代人和两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与历史宏观结合,赋予了白鹿原深层次的文化空间涵义。
注 释
①[苏]多宾著,罗慧生、伍刚译:《电影艺术诗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②菲利普·J·埃辛顿著,杨莉译:《安置过去:历史空间理论的基础》,《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③龙迪勇:《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
④卢衍鹏:《论1990年代中国文学中欲望叙事的多义、异化与悖论》,《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⑤李镇:《一朵芙蓉著风雨——与中国人‘身体’的觉醒》,饶曙光主编《中国电影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⑥赛人:《三种〈白鹿原〉的国族寓言与逻辑》, http:///mtimereview/blog/7465860/2/。
*本文系江苏省2012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CXZZ12_0364)、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度博士学术新人培育计划资助选题“电影叙事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