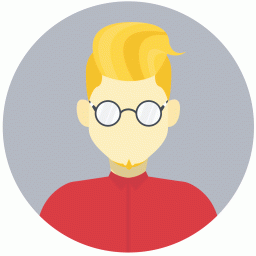这是我的爸爸
时间:2022-10-19 12:14:43
一
天一擦黑,金枪就揣了酒壶往屋后桶壁前走,去打猎。媳妇小满打屋里出来,说,手电筒带上。金枪说,嗯。小满说,小心点儿,莫摔着了。金枪说,嗯。金枪走出好远了,小满又撵上,把件褂子往他身上披,说,冷起来了就喝口酒。金枪说,我晓得嘛。小满扯扯褂子角,抚抚褂子领,说,万一捉不住就算了,莫作难。金枪说,回嘛。小满回了。金枪一步一步往桶壁上爬。
那会儿,太阳已落到桶那边,整个石桶村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只有石桶上空有些暗红光亮。画眉声声叫着,关山,关,关。布谷声声叫着,哥哥,哥,哥。锦鸡声声叫着,扯皮,皮,皮。空气暖烘烘,满是树枝嫩芽气味儿。还有兰草花香味儿。时不时还有剌花香味。各种野花香味。一阵暖风,送来桶里上千亩油菜花香味儿,铺天盖地,一下把兰草花香味儿盖住。把剌花香味儿盖住。把各种野花香味儿盖住。也把画眉叫声盖住。把布谷叫声盖住。把锦鸡叫声盖住。
风忽然停了。又满是树枝嫩芽气味儿。兰草花香味儿。剌花香味。各种野花香味。画眉声声叫着,关山,关,关。布谷声声叫着,哥哥,哥,哥。锦鸡声声叫着,扯皮,皮,皮。
金枪从小道上爬爬歇歇,歇歇爬爬,浑身大汗直滚,像顶着架蒸笼。不知不觉间,天上暗红色光亮没了。天黑定。画眉不叫了。布谷不叫了。锦鸡却叫得更殷切,这边一声扯皮,那边一声扯皮。林子到处都是它们扑棱棱扇动翅膀声音。
金枪边爬边用手电筒照照林子。爬一气,照一气。照一气,爬一气。再照,到桶沿儿了。又照,到日天峰了。
二
日天峰不是一般的峰。
日天峰活灵活现地像个男人身上那物件,雄赳赳,气昂昂,一筒竖在桶沿儿,直朝天空戳。平日在石桶里看时,真像是在日天。色胆包天哩。
金枪把手电筒照照日天峰根部。根部密密麻麻都是灌木。像是男人身上那物件四周的那物件。金枪又自下往上照,圆圆滚滚光光溜溜一筒都是石头。石头尽是些青的黑的筋筋络络,尽是些大的小的沟沟回回,真像男人身上发怒了的那物件。金枪把手电筒灭了。满天星光。日天峰黑乎乎圆滚滚的,像是正在色胆包天地日天,还一耸一耸地动哩,连灼热的骚气都能感觉到。金枪把眼睛狠闭下。金枪把眼睛狠睁开。黑暗中摇摇头,苦笑,然后朝根部灌木丛走去。那里,有个石头长成的小平场。小平场边上有棵多粗的苦楝树。每回,金枪都靠了苦楝树干坐,一坐就是半夜。然后打猎。好多年了。
金枪打猎也不是真打。他一没枪二没刀,用啥打嘛。金枪的打就是小满说的捉。他捉也不捉别的,专捉催生子。催生子就是书上说的飞鼠,吃野果子,也吃金钗,它的屎叫五灵脂,女人吃了怀娃利索,所以石桶村人叫它催生子。医书上还说,催生子的屎还能治好多妇科病,灵验得很。但就是不好捉,一捉它就飞。从这个崖头飞到那个崖头,从这个树梢飞到那个树梢。但金枪还是捉住了。金枪是用站笼子捉住的。就在这个小平场上。金枪用树棍扎了个笼子,笼子放了一大串用绳子串起来的板栗。不用说,这板栗是拴在机关上的嘛。那一夜,金枪就趴在旁边灌木丛中等啊等,到了下半夜,月亮都快落下去的时候,听到催生子叫了,哥哟,哥哟,哥哟。像是小女人偷偷呼唤突然不见了的野男人,嗓子压得低低的,叫得月光惨白惨白的,叫得林子阴森阴森的。接着,金枪看见一张毛毯打日天峰顶上飞了下来。哎哟,那嘴,那脸,那眼,还有那毛色,整个就像个巨大的松鼠嘛。只是爪子不同。催生子爪子简直就跟人的手样,只是多长了毛,月光下指甲都白亮亮的。那会儿,金枪大气不敢出,眼盯着催生子进了笼子,眼盯着催生子用爪子捧起了板栗。接着机关就给触发了,哐哧一下,笼子门就给关上了。
以后,只要有空儿,只要是小满让他去捉,他都来捉。夜夜都不放空,去一回捉一只,去一回捉一只。捉了就带回家,关在笼子里。只是顶多只关得一天,或是两天,三天,过了就跑了。小满问他是不是笼子不牢靠?金枪说不是的,催生子爪子跟人一样灵活,再牢靠它也能自个儿解开跑啊。小满又问他是不是他有意放它跑了,每回捉的咋都一样长相?金枪说哪能嘛,所有野物件不都一个长相?小满就哦,哦过了也不再问,任凭这么捉了跑,跑了捉。也好多年了。
三
金枪靠在苦楝树上坐了。
小平场上依然光溜溜的只有石头,顶多只有石头缝里长些杂草,枯的青的混在一起。金枪是坐了等着捉催生子吗?不大像,站笼子影儿都不见一个,用啥捉嘛?他是准备歇会儿就重新扎站笼子吗?也不大像。他空手两巴掌的,用啥扎嘛?
反正他就那样干坐着。
金枪也不尽然是干坐,他在看,透过苦楝树枝杈看天上星星。天越黑,星星越亮,他就看得越清楚。这一处,犹如一把勺子。那一处,好似一张犁耙。再看那一处,又像个仙女。哦,那密密麻麻像个纺锤的,就是银河了,说是王母娘娘用簪子划成的,把牛郎织女隔开了。还说是每年七月七日晚上,他们就在鹊桥上相会。鹊桥上怎么能相会?不就只是见上一面,啥都做不成嘛。为啥只是七月七日才相会?春天这个时候就不能相会?春天多好,不冷不热的。
又起风了。虽然看不见枯枝动,听不见嫩叶响。但风确实在吹,还是那么暖烘烘的,像是好女人的嫩手在脸上拂过来,拂过去。浑身痒酥酥的。风又送来桶里上千亩油菜花香味儿。虽然不再铺天盖地,但细小,绵长,小蛇样直往鼻孔钻。金枪忍不住看了眼脚下石桶。石桶里一片灯火,像是卧着的夜空。嗯,紧靠桶壁的那盏灯火,就是自家的。都看了好多年了,错不了。
小满这会儿在做啥?
唉,她能做啥?肯定是在吃晚饭嘛。饭是大米饭,白花花的,香喷喷的。菜是家常菜,有腊肉,有野竹笋,野韭菜,还有香椿炒鸡蛋。小满也肯定是一个人在吃,吃两口就朝桶沿方向看看,还叹上两口气。她在想他还没吃,还饿着。也是,出门时她说要做饭让他吃,他却说不饿,等明早回家吃。所以小满要牵挂他。所以小满吃不香。
金枪又想,小满吃过饭后做啥?唉,她又能做些啥?不就洗澡嘛。就在那间支书三德亲自帮忙砌好的卫生间一个人洗嘛。灯是暖烘烘的取暖灯,墙是白花花的瓷砖墙,水是热烫烫的太阳能热水。小满一个人进了卫生间。小满看了看门外,然后打了插闩。小满开始脱衣服。先是一件一件脱上衣,一件件脱下衣。小满把外衣都脱了,脱得只剩下乳罩和裤衩了。最后,小满把乳罩和裤衩也了,成了一条白花花的美人鱼。这时,小满就打开水笼头,热水雨丝样喷到她光溜溜身子上,一会儿雾气就罩满整个卫生间,啥都看不清了。只听得热水沙沙往小满身子喷,只听得热水哗哗顺着小满身子往下流。
金枪接着想,唉,要是自家这会儿在家,小满肯定会在卫生间大声喊,金枪啊金枪,来,帮我搓把背。金枪也肯定会说,好嘛。然后进去帮她搓。搓着搓着,就搓到前面去了,搓着搓着又搓到下面去了。
唉,不想了。不想了。还是想捉催生子那会儿吧。
那会儿啊,金枪就趴在旁边灌木丛中等啊等,等到了下半夜,月亮都快落下去的时候,催生子叫了,哥哟,哥哟,哥哟。像是小女人偷偷呼唤突然不见了的野男人,嗓子压得低低的,叫得月光惨白惨白的,叫得林子阴森阴森的。接着,一张毛毯打日天峰顶上飞了下来。哎哟,那嘴,那脸,那眼,还有那毛色,整个就像个巨大的松鼠嘛。只是爪子不同。催生子的爪子简直就跟人的手样,只是多长了毛,月光下指甲都白亮亮的。
又一阵风起。风暖烘烘的,又送来桶里上千亩油菜花香味儿。唉,洗澡过后小满又会做啥?废话嘛,洗澡过后肯定是一个人看电视嘛,看完电视后肯定是一个人睡觉嘛。那,睡觉后三德会不会来敲她门?嗯,肯定会。但小满才不会开门哩。她才不是那样的人哩。小满肯定不会理他的,还会大声骂一气,一直把三德骂走为止。然后,然后小满就睡了,睡得鼾是鼾屁是屁的,一直睡到天亮时他捉了催生子回去时还没醒。他用手指刮她鼻子,她还在说梦话。嗯,就是这样子的。
四
对面桶沿上渐渐有了团晕黄的光亮。仿佛是桶沿那边正有人架着一笼火。又好像有啥多好的事正在桶沿那边发生。渐渐地,火光越来越亮,能看见桶沿上一块块石头,石头上一排排树了,剪纸样的。还有一群鸟儿飞上飞下。听不到叫声。再过一会儿,一轮老大的月亮升上来,挂在树枝上了。
月亮一升起来,日天峰就格外显眼儿了。月光皎洁得好女人手一样,把日天峰从上到下舒舒服服抚了个遍,抚得更加雄赳赳气昂昂了,好像正在一耸一耸地日天。灼人的骚气更加浓烈。脚下石桶却更加黑了。灯火一盏盏熄了,也跟天上星星一样,稀稀拉拉了。自家屋里那盏灯火,也熄了。
金枪不知怎么地又想到小满了。
金枪想,小满现在熄灯做啥?哼,小满熄灯能做些啥?不就是一个人睡觉嘛。他知道,小满最喜欢裸睡,乳罩也不戴,裤衩也不穿,就那么光溜溜白亮亮的一条钻进被窝里睡。一睡就睡死了,鼾是鼾屁是屁的,不到天亮她不醒。有时候到了天亮也不醒,等他回去刮她鼻子。一下一下地刮。嗯,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了,也说不定,说不定小满睡觉后三德会来敲她门的。因为自家是大明大白地出来打猎的嘛。桶里人都晓得他一打就是一整夜嘛。这是个好机会嘛。小满呢,她会不会开门?嗯,她说不定,说不定会开的。说不定她光着身子坐起来问,谁啊?三德呢,也说不定正嘶声哈气地说,我嘛。小满说,哦,你等下。说完就那么光溜溜白亮亮地下了床,去开门。三德一下扑进来把小满抱住了。金枪使劲打了个冷噤,使劲抖了下脑袋,想跟落水狗抖身上水一样把心里的事一下抖个干净。
呸,呸呸。
金枪在月光里使劲骂了声自家,还想象着使劲抬手抽了下自家耳光。然后,金枪坐不住了,站起在小平场上走。一趟走过去,一趟走回来。眼睛始终盯着脚下桶里。金枪想,小满咋会是那样的人?小满才不是那样的人嘛。小满不就是想用催生子的屎做药引子治她的妇科病嘛,小满不就是想用催生子的屎做药引子才让他再捉一只嘛。这又能咋啦?只怕还能说是故意支他走开好跟三德做那事?才不是。小满才不是那样的人。小满肯定是一个人在睡,一睡就死了,鼾是鼾屁是屁地睡死了。就是三德再怎么敲门,她也听不见。就是听见了,小满也装做没听见,等他敲。敲长了,敲累了,三德肯定就失望了,就走了。嗯,就是这个样子的。
金枪又靠苦楝树坐了。
五
月亮越升越高。天空越来越亮。桶里上千亩油菜花尽收眼底。微风一会儿起,一会儿停,还是那么暖烘烘的。暖烘烘的空气中一会儿是油菜花香味儿,一会儿是兰草花香味儿,猛然间,又是剌花香味儿了。又是各种野花香味儿了。时不时还有锦鸡在叫,扯皮,皮,皮。接着是扑棱棱翅膀扇动声音。嗯,春天真是个好季节,不冷不热的,啥都想往上长,啥都想往外涌。草啊,树啊,鸟啊,虫啊,都在攒着劲儿做那些快活事儿。日天峰也好像显得更粗更大了,一耸一耸地也更加霸道了。这石头。这色胆包天的石头。这活该舒服的石头。
说真的,小满这会儿真的在做啥?难道她真不是一个在睡?难道她真不是一个人在鼾是鼾屁是屁地睡?难道她真的在等三德?难道她这么多年来天天晚上都跟三德做那些事儿?
呸,呸呸。
金枪又使劲打了个冷噤,使劲抖了下脑袋,想跟落水狗抖身上水一样把心里的事一下抖个干净。但无论怎么抖,还是抖不干净。金枪眼前老是出现三德趴在小满光溜溜白亮亮的身子上的样子。
金枪想,这不行,得唱歌。他知道,人一唱歌儿,就把心事忘掉了。起码暂时能忘掉。金枪想着,就扯起嗓子唱起那首他唱了好多年好多晚上的《五更歌》。
一更里呀一炷香,
情哥来到我大门上。
娘问女儿什么响?
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娘,
风吹门铃响叮当。
金枪一唱,又想起他跟小满刚结婚那些日子。那时候小满多满啊,满得他天天晚上都想做那些事。还有一回,也这个时候,老大的月亮挂起在桶中间天上,桶里上千亩油菜花像一张金黄毯子铺着。他和小满打她娘家回来。才走到桶中间,他就想了,就把小满按倒在油菜田里。他记得那时刚好起了风,暖烘烘地吹得一桶油菜一浪地过去,一浪地过来。
金枪眼前又出现三德趴在小满光溜溜白亮亮的身子上的样子。金枪想,难道,难道小满真的在跟三德做那些事吗?他们,会不会也在油菜田里做,也做得一桶油菜一浪过去一浪过来?呸,呸呸,我咋能这样想?我咋能这样想小满?小满根本不是那种人是不是?
金枪又扯开嗓子唱起来。
二更里呀二炷香,
情哥来到我床边上。
娘问女儿什么响?
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娘,
猫子跳在踏板上。
情哥来到我的床上。来到我的床上做啥?废话嘛。金枪又想起小满了。金枪想,小满真只是让他来捉催生子?她真的不是想和三德做那些事?
三更里呀三炷香,
情哥来到我的床上。
娘问女儿什么响?
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娘,
女儿寒冷加衣裳。
呸,呸呸,我咋老往这些肮脏事上想?我咋能把小满想得这样肮脏?小满咋会是这样肮脏的人?再说了,人家三德是经常来帮自家的忙,啥脏活重活都帮忙做,啥好政策都往自家倾斜,但人家那是结对帮扶嘛,再怎么说,人家是支书嘛。是支书总有点德性嘛,咋会跟别人家媳妇做那些肮脏事?
看来光唱歌不行。再怎么唱还是容易往歪处想,一想就没个边儿了。看来还得喝酒,一喝醉就鼾是鼾屁是屁地睡着了,一睡着啥也不会想了。金枪打腰里取下那个三德送的军用水壶,拔掉塞子,凑到嘴边。
金枪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金枪看看月亮,月亮越升越高,月亮旁边星星越来越稀了。金枪看看日天峰,日天峰在月亮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粗大,正不知疲倦地日着夜空。金枪看看脚下桶里,桶里一盏灯火也没了,一桶上千亩油菜花正安静地卧在月亮清辉里。
小满,真的是在一个人睡觉?
金枪索性双手抱着水壶像喝中药那样喝了起来。金枪一气喝掉大半壶酒。
四更里呀四炷香,
情哥爬到我的肚子上。
娘问女儿什么响?
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娘,
女儿口渴吃冰糖。
金枪一口气唱完最后两段,又抱着酒壶像喝中药那样喝了一气。金枪一气把酒喝完,扯开嗓子吼了。
五更里呀五炷香,
女儿送情哥出绣房。
娘问女儿什么响?
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娘,
隔壁王大妈起早床。
六
月亮升到桶中间时,金枪已经醉了。起先,他还断断续续地唱《五更歌》,一边唱,一边在小平场上手舞足蹈。唱了一气后就没声了,一屁股坐在苦楝树下不动了。那会儿,空气也变得凉沁,不再暖烘烘。桶里上下的山啊树啊花啊啥都一起睡着。日天峰也似乎歇息。天地安静。没睡没歇的只有那些出来觅食的小兽,还有专门逮小兽的猫头鹰。小兽们脚步轻轻的,偶尔碰到树枝和枯叶,发出响声。猫头鹰叫突然了,只一声,顶多两声,号哭似的。小兽们吓得大气不敢出。天地更安静。金枪的鼾声也更响。
金枪一直睡到五更时候,梦见一个男人朝他走来了。
那男人是啥时候来的,是咋来的,金枪是一点都不晓得。金枪只感到眼前一阵白光乱晃,睁开眼睛时那男人就站在自家面前了。金枪吃惊的是那男人跟自己长得非常像,也是个半驼背,也是披了件褂子。更相同的是那男人也打个手电筒,腰里也别个装了酒的军用水壶。
那男人又用手电筒晃晃金枪,嘶声哈气地说,睡着了?小心冻着嘛。
金枪揉揉眼睛说,你是?
那男人说,我叫三德,邻村的。
金枪说,你也叫三德?我咋不认得你?
那男人说,我可认得你。你不是那年跟我一起在乡里结扎的金枪嘛。
金枪说,开啥玩笑嘛,我啥时在乡里结过扎?我从没结过啥扎。
那男人说,哦?只怕我认错人了?
金枪说,是嘛。
那男人又哦一声,嘶声哈气地说,先架个火烤吧?五更了,冷嘛。
那男人说罢,打着手电筒钻进灌木丛了。不一会儿工夫怀里就抱了一大抱干柴出来。那男人把干柴朝金枪面前地上一扔,火苗就呼地蹿起来了。干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把四下照得如同白昼。那男人拂拂面前的柴屑,重新扯了扯褂子,搬块石头在金枪对面坐了,叉手向火。有了火,金枪这才觉得真是有些凉沁了,也重新坐起,叉手向火。
烤了半天,那男人嘶声哈气地说,不对嘛。
金枪说,啥不对?
那男人说,你还是在乡里结过扎的。那年跟我们一起结的。
金枪说,你瞎说,我从没结啥扎。我现在原封原档的,好好的啥都没坏。
那男人盯了眼金枪,说,不对嘛,只怕我认错人了?
金枪说,肯定是嘛。我从没结过扎的。我现在真的原封原档的,跟一杆金枪样。
那男人唉了声,说,好,没结过就没结过,不说了,不说了。
金枪说,只怕说,你结过扎了?
那男人说,嗯。说罢,他就给金枪讲起了他当年结扎的经过。那男人说,那年,乡里逼他到乡卫生所结扎,他死活不肯。乡里说要是不结,就赶他猪扒他房,他只好同意。临到做手术时,他感到格外疼,就喊着说不对嘛不对嘛。但医生们根本不听他喊,几双大手死死把他胳膊腿按了,一坨棉球把他嘴严严实实堵了,他想喊也喊不出声了。等把棉球拿出后,手术已做完了。可做完后几个月里那物件一直疼得厉害,后来越疼那东西越朝里缩。最后到县上一检查,才晓得医生错把他的动脉血管当输精管扎住了,那物件早不供血了,早坏死了。
男人说到这里,痛苦地摆了摆脑壳,说,唉,全乡一下扎坏了十七个,造孽嘛。
金枪说,只怕说,你从此做不成那事儿了?
那男人说,废话嘛,屙尿都要抠半天才抠出来能做那事儿?
金枪说,哦,哦。我晓得了,你是让你女人好跟别人做那事才找借口晚上打猎的,是不是?
那男人一听,顿时哭了起来,哭得两个肩头一耸一耸的。那男人说,咋不是嘛。我只要晓得我女人相好的要来,就自觉跑到这儿来假装捉催生子,一坐就是一整夜。我有啥办法嘛,我不找借口走开咋行嘛。我总不能老让我女人跟着我苦嘛。她也是人嘛。
金枪一听说他也假装捉催生子,觉得好生奇怪,就问那男人到底是哪村人,到底叫啥名字。
那男人抽泣着对他说,实话对你说嘛,我是石桶村人,我叫金枪。
七
金枪一觉醒来时,天已蒙蒙亮。月亮也早落到西边桶沿上,老大一个支在树梢上。金枪看看脚下桶里,一盏盏灯火重新亮了。自家屋里灯火也亮了。他估摸着小满早起床了,三德也早该走了,就把被露水打湿的头发拢了拢,把被露水打湿的褂子脱下来抖了抖,重新披了。然后,金枪仰起头望着日天峰顶像小女人压低声呼唤野男人那样叫了起来。
哥哟,哥哟。
刚叫罢,一只催生子像张毛毯样打日天峰顶上飞了下来,轻轻落在他肩头。不住地用毛毛茸茸的脖子亲昵金枪。金枪轻轻抚了把催生子毛茸茸肉翅膀,然后一步一顿地往桶下走。
天色越来越亮。月亮落下西边桶沿儿。太阳从东边桶沿升起。空气清新而甜蜜。一路满是树枝嫩芽气味儿。还有兰草花香味儿。时不时还有剌花香味。各种野花香味。晨风吹起,送来桶里上千亩的油菜花香味儿。布谷一声声叫,哥哥,哥,哥。锦鸡一声声叫,扯皮,皮,皮。
金枪回头仰望,日天峰早已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中了。金灿灿的阳光中,日天峰越发像个男人的那物件,正一耸一耸地日着天,日得咬牙切齿,日得怒火万丈,仿佛天犯了啥不可饶恕的过错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