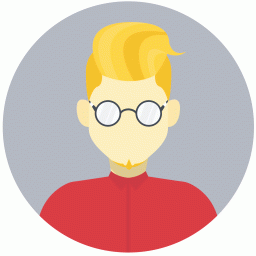于晓丹 独立女人的三重面具
时间:2022-09-28 08:04:37

她是纳博科夫《洛丽塔》、雷蒙德・卡佛《你在圣佛朗西斯科做什么?》在中国的最早译者,而后远走纽约,成为资深内衣设计师,又因一个BBS,重新拿起笔,写起了小说。于晓丹给自己戴上三重面具,却依然不失本真与自然。
于晓丹穿暗格子棉布衫,一头短发,白皮肤,眼睛有光彩。她屈着腿蜷在沙发上,放松,是个平静下来的文艺女青年。平静下来了,便不会有惊愕,只是淡而有趣地,说些文人间的八卦,是非曲直,她有她的评判,但都不尖刻。
最近她出了一本白色封面的书,《内秀》,关于她在纽约做内衣设计师的生活,却不炫目不叫嚣,是下午窝在沙发里看到昏然入睡、醒来再读也不觉得突兀的书。黄佟佟为她写了一篇《白粥生活》,“写得简单比写得好要困难―因为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是你的炫耀欲,你要对付的是你的时刻想要冲出来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读于晓丹的文章有这点好,你看不到一点炫技之向,火气全无,读得非常舒服。”
她确是沉实的,洁净的,温笃像一碗白粥。
《洛丽塔》,珠玉在前
故事的开始,是个早熟、敏感的女孩,六七岁时开始给小男孩写诗,常常暗自祈祷那个他没有保留,“现在拿出来再看的话真令人想死。”她的青春期没有和家人一起度过,日子被亲戚家的环境分成两个极端:一端是深宅大院,有警卫把守,需要按门铃,再穿过长长的走廊;另一端是胡同,上厕所要到马路上的公共卫生间。“好像也挺适应的,很随意的日子。”
这样的女孩,最初并未想到会为他人做嫁衣,从事翻译, 她自然是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抒发自己的生命,“读书时候参加文学社,听见学校大喇叭里头播报我写的东西,很得意。”只不过在文学领域,她的运气始终不怎么好,二十一岁写的《死情》原定发表在《人民文学》,已经编好,却赶上之前那期因马原的《亮出你的舌苔》,《人民文学》停刊,她的小说两年之后才重获发表的机会,但“已经没意思了”。
外语学院毕业之后她被分到社科院,做《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每周上两次班,每次半天,工作轻松。彼时正值思想解放,所有人都张开了触角,渴求新鲜的东西,一有新书,书店外便排起长龙,《外国文学动态》经常介绍国外最新的作家作品,诱惑着人想看到全书,便有出版社编辑整天蹲在外文所,逢人便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想翻译的?”于晓丹答了《洛丽塔》,迅速开工,“我觉得译纳博科夫这么一本‘大’书应该要五年工夫,因为赶工,一年多就译完了。”
虽有父女相恋这种状似大不韪情节,《洛丽塔》并不让她觉得突兀,“纳博科夫都计算好了,铺垫充分,节奏张弛有度。那时中国最热是伤痕文学,每一篇都铆足了劲让你哭,但纳博科夫的小说太冷静,他会让你的情绪跟着他,好像要陷落了、感动了,又把你拉出来。他是文字上的游戏者,与我们的传统文学太不一样了。”
她呆在没有暖气、又朝北的宿舍楼里,翻译完《洛丽塔》,掉了十斤,一个本来圆润的女孩,变成了个瘦削的女人。译者是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书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也不像许多作家那样,每天收到以麻袋计的信,想着拿到稿费就行了,能印证它销量还不错的,是出现了盗版。”而后她翻译了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是卡佛在中国的最早译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她感受到了社会上的变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奔,特别分裂。许多人下海经商,在社科院蹲点的出版社编辑不再热切问要不要翻译某部作品,而是说‘咱们攒一个什么吧’,或者说‘你再翻译一遍《生活中不可承受之轻》吧,反正有人买。’我常常犹豫:是不是也要成为‘攒’的一分子?”
她也攒过,为台湾一家出版社做一套生活方式的书,还把一部影视剧改写成了小说。“我挣了点钱,可觉得太无聊了。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脱落得斑驳的墙皮,感觉已经没有人再珍惜这个地方。世界都乱了套,价值观也要崩溃了,加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我觉得,必须要走,再不走就窒息了。”
本可以在体制内寻求安稳,她不要。1995年底,她去了美国。
内衣的秘密
这样纤弱的女人,竟然到了纽约,进入了工业化高速运转的内衣行业。“我从小对服装有兴趣,带我长大的阿姨靠给人织毛衣为生,常带我去‘取活’,领回毛线,放回织好的毛衣。但从来没敢想以后会做服装。那么多美术功底好的人,都挤不进工艺美院,我就别做梦了。但脱离了环境的禁锢,到美国之后,我就想什么梦都要做一下。”
两次申请,进了纽约时装学院,每周上五天课,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没有基础,各种材料需要不小花费,周六还要去打工,在一家小翻译公司做事,习惯了社科院的悠闲,她脸上立刻暴出两个脓包,还总被老板催促“吃饭能不能快点?”毕业之后,进入内衣公司工作,之所以在众多服装门类中选择内衣,“因为喜欢它的质料轻且柔软,又注重细节。内衣的式样都简单,但如何让每一件都不一样,就在于对细节的关注。”
初期在小公司,拳打脚踢,什么都做,经常拿着展示板去跟客户谈,观看自己的设计被直接地反映。“难伺候极了,尤其是私有品牌,就是百货公司自有的牌子,它不做设计,只从设计公司购买,常提一堆要求,从图案到款式到布料,还总是改来改去。”
但这个过程,对她来说没有痛苦,没有拧巴,用“高兴”更为合适。出国已经使她抛弃了许多东西,再失去点什么,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立刻发现,我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比如在地铁上看到自己设计的图案,商店里看到自己设计的衣服,你必须要和社会打交道,而非继续享受那些独属于私密的东西。”
对于晓丹来说,内衣的含义远大于我们日常关于内衣的定义。“如果跟不同国家的人说‘我是个lingerie设计师’,得到的反应会很不同。中国人会探讨文胸和底裤,因为他们概念中内衣就是这两种;美国人的脑中多数会浮现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的秘密’T台秀,以及波涛汹涌的模特们;英国人想到的,更多是橱窗里那些薄、透、软……充满性诱惑的小东西;法国人最理智,他们往往会接着问一句:‘内衣的哪一个类型?’真正的内衣,除了文胸和底裤,还包括日内衣、睡衣、家居服以及塑身衣。”
她至今不太明白国内出产的内衣,常要用繁复的蕾丝,作出许多褶皱,将罩杯包得凹凸不平,在轻薄的外衣下形成奇怪的膨起。“内衣最重要的该是减法,即使加装饰,也要加在不影响内衣基本功能的地方,譬如加在文胸的两翼。如果要加在罩杯上,一定要用最细腻最平滑的蕾丝,而非粗糙的、颗粒特别大的那种。包括内裤的缝合应该用什么样的针法,商标缝上去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一定不能硌到皮肤;染色对蕾丝效果的影响……内衣的昂贵,就在于投入巨大精力来关注这样的细节。”
一个女人,该拥有多少件内衣呢?于晓丹的答案如下:一是全罩型,搭配带领或者不开领口的外衣;二是半杯型,适合领口较大的外衣;三是平杯型,穿在一字领口下;四是无吊带型,搭配无肩外衣;五是Plunge,特制深V又能挤出的内衣,搭配V字领;六是T恤文胸,搭配贴身T恤,要求既不露身体特征又不露文胸痕迹。
“既然是内衣,自然应该穿在内里,为外衣服务。比如颜色,基本颜色一定是黑色白色与裸色,进到美国任何一家百货公司的内衣区,文胸和内裤的部分,最大比例的一定是这三种颜色,顶多配一款当季流行色,但国内的内衣店往往五颜六色夺人眼球,店员告诉我,最好卖的是金色和红色。”
“国外的内衣将普通尺寸和大尺寸分得很清楚,只有大尺寸内衣才会特别强调功能性,譬如收拢或上提。内地出产的内衣,似乎将功能性强调得太重了,比如塑身,我很惊讶紧身衣在国内有这么大市场。也许还是源于欧美女性骨子里的那种‘不在乎’吧,不那么在乎自己身体是否有男性目光下的吸引力,反而有了种随意自然的气质。”
做了十年内衣设计师,职业病是见人先揣测内衣是否穿得合适。“看明星走红毯,我特别关注她们的内衣会不会露出来,前阵子看大学生电影节,有个女星的内裤露了出来,好想告诉她穿个低腰内裤,还见过女星的衣服褶皱下,清楚显示出胸贴的形状,真想帮她弄一下啊!”
她曾为Maidenform、Elle、Vera Wang Princess、Vanity Fair等内衣或睡衣品牌担任设计师,《穿Prada的女魔头》之后,时装工业的残酷已露出一角,于晓丹也曾经历,比如“刚刚被一家公司挖走,不到一个月就被解聘”,或者被资本家老板骂到狗血淋头。但内衣设计中,依然有她寻找的美好,比如摩挲那些出产于日本、英国的绝美蕾丝,比如为了工作深夜乘火车从巴黎到米兰,经过阿尔卑斯山时,看到窗外神话般的景色,叫人想起济慈和雪莱的诗。
在更成熟的商业社会,人不会有太多负面情绪。“曾经我和一个设计师品位完全不同,老板让我们俩为同一个品牌做设计,我很抵触,就跟朋友抱怨,说那个设计师的爸爸是开卡车的,懂什么设计;这位朋友立即反驳:我父亲也是工人。我突然发现,自己还陷在中国传统思维的漩涡里,依靠出身划分三六九等,这些年来,这种潜意识慢慢消磨了,所以这次回国,我发现很多人依然有这样的观念,他自以为成功,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看演出一定不能坐在五排之后……还好我到了美国,少了许多负担。”
在那样的世界,不会有一个IT富豪问邓文迪,“我们都知道你过得是很富豪的生活,能跟我们讲讲具体是什么样的富豪吗?”也不会有人写了一本书,专门用一章来讲述自己如何买Armani,还得意自己被称为“Armani Girl”。她的名片显示她已经到了Senior那一档,这意味着她在纽约可以过着中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看到喜欢的衣服,不用担心不够钱。“我的好衣服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她说。
《1980的情人》:记忆是有力量的东西
内衣设计师的日子持续到2006年,一个大学同学建了个BBS,她上去看,“好像所有的青春记忆都回来了,那个过去跟我当时忙碌却优越、辛苦却不痛苦的内衣设计师的生活,跟纽约不细腻却活色生香的生活大相径庭。它像一团荆棘,让我感到了久违的心疼。二十年前的人,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那种滋味太迷人了,‘现实’立刻变得无足轻重。”很快,她辞去内衣公司的工作,开始全力写作《1980的情人》。
“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上世纪80年代就想起沸腾的文学、思想的解放,但更日常的生活,譬如如何恋爱,年轻人之间的小伎俩小阴谋,我没有读到过,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也有同学说这不像他的经历,但我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的小院,每个人之间的差异都很大,有人当过兵、插过队,进了学校依然叱咤风云;有的则一路初中、高中读来,还懵懵懂懂,无法进去前者的圈子,好像过得乱七八糟,依然要面临许多青春期的问题。”
“也许真的是十年设计师生活让境遇变了,文学已成了背景,我越来越不能欣赏那些曲折叠沓、似是而非的形式,越来越排斥伪浪漫、伪传统、伪历史的表述方式,而更喜欢朴素直白、迎头而上又内心敦厚的东西。时下很多作品,最让我痛心的,就是好端端的一个故事不能好好地讲,而是被作者用各种各样所谓的‘形式’糟蹋了。我愿意做点我认为对的尝试。”她说,这其中也有纳博科夫的影响,有《洛丽塔》珠玉在前,“让我在文学上有另外一种反省。”
十万字长篇中,从未有作者跳出来抒发感情,只是几个年轻男女的故事,感情克制,细节充沛。“好像是一种还原,小说中人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甚至提到食堂外面经过了一辆车,都是对那个年代的记忆。记忆是特别有力量的东西,我至今提到这部小说,还是觉得有点难过。”然而“我觉得作家还是要痛的,不是你痛就是让别人痛,总要痛一点。世界已经歌舞升平,人们躲进物质或宗教中寻求安慰,文学应该发现一个比上帝更有力量的东西。”
在文字中“痛苦”的于晓丹,却说那段写作的时光,是最舒心的日子,“一边写作一边给一些内衣品牌做兼职,不用早起,不用定闹钟。”现在她有一个教在纽约大学中文的先生,“他是个没有负面情绪的人,特别阳光。”有朋友说他们的结合,是她“终于修成了正果”,而一个阳光的伴侣、一份安稳的感情,也让她有了安全感来继续一边兼职设计一边写作的日子。
这次回到国内,她惊讶于,每个人面具的厚重。“比如不少老朋友会看我的微博,但他不会点击‘关注她’,我在关注他,但他一定要做出‘我不关注你’的姿势。我很奇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个年代有其表演性质,但它是裸的,摆明了‘我要当一个什么’,但如今这种表演更盛,有些我当时就认识的人,读他如今的文字,我常不由自主地笑出来。他一定要用某种身份,譬如古玩专家、古典文学专家,来装饰自己。” 这当然没必要。她说纽约也有这样的风气:进入餐馆,男人一定要按规定的程式脱掉西服外套,把它搭在手臂上,要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将商标看似无意实则用心地显露出来。“我热爱那个城市,就是因为它给我自由,让我也可以不那样生活。”
可以不那样生活的于晓丹,在不惑之年,做了肆意的生活家。这或许是她的第四副面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