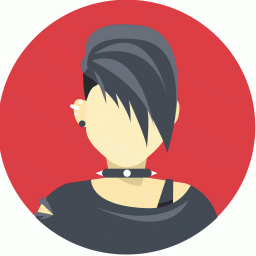与孩子一起到南极
时间:2022-07-13 09:50:13
说出来,很多人不信,我带儿子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是逃学到南极。
千万别因此把我们想象成“虎妈豹子”组合。我们这对母子拍档,虽然搭伴走过欧亚一些地方,在瑞士下湖游过泳,在老挝玩过漂流,但远远没有“凶猛”到骑行川藏、徒步沙漠、足迹纵横七大洲,更何况远赴世界尽头的南极?事实上,去南极前,儿子九岁,我四十;他不到一米四,我刚过一米五;他感冒咳嗽还没好,我正严重贫血,刚刚停了调节内分泌的药。
出发前,周围一片劝阻声。有一天,儿子问我:“妈妈,我是到南极年龄最小的孩子吗?”“肯定不是。你想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吗?”“不是。我只想知道,那些去过的小孩儿,都平安回来了吗?”
儿子肯定不是到南极年龄最小的孩子,但他应该算是第一个为了南极行放弃期末考试的中国孩子。究竟是什么,让我下决心带孩子逃学到南极?
期末考试常有,而南极行不常有,孩子的童年经历一旦错过更不会再有。我想知道:
一个孩子,尚在鲜活纯真的年龄,他的眼睛和心灵还没有被世俗污染,当强大而神秘的南极扑面而来,他会怎样?
我们到南极去上课
南极究竟有多远?
北京飞上海,上海飞多哈,多哈飞布宜诺斯艾里斯,四十多个小时的飞行、转机、经停、再飞行,跨越欧、亚、非、南美4大洲,我们终于到达了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火地岛上的乌斯怀亚。登上开往南极的邮轮,此时,我们距离南极半岛还有一千公里。去南极最严峻也是考验最大的一段旅程正等着考验我们母子――穿越“魔鬼海峡”德雷克。
德雷克海峡,处于臭名昭著的西风带,以狂风巨浪著称。如果运气不好,除了没有电闪雷鸣和暴雨外,德雷克海峡的风浪,就堪比《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Pi一家在船上遭遇暴风雨的场景。
晕船开始了。“开始,晕船实在太难受了,你害怕你会死掉;后来,晕船实在太难受了,你害怕你死不了。”同行人中,有的人晕得四十多个小时下不了床,我也一度晕得躺在床上不敢睁眼,儿子干脆随身拎着呕吐袋,随走随吐。
一年中,只有11月到次年2月,普通人可以到南极旅行,因为这是南极的夏天。 典型的南极日常生活场景是:早晨,就着榨菜、辣酱喝碗船上大厨发明的中西合璧的“粥”后,就要开始登陆前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装备:保暖内衣、冲锋衣、防水裤、脖套、太阳镜、手套,相机、镜头等放进防水背包,按组集合,换上防水靴,趟过颜色可怕的消毒池,上橡皮艇,乘风破浪,我们巡游、登陆。
起初,一切皆新鲜。冰山翻转。座头鲸跃出海面。八头虎鲸出击围猎。阿德利企鹅仿佛永远在跳水。两只年幼的帝企鹅不知为何落单在威德尔海。有些金图企鹅走向偷盗石头的犯罪生活。一只受伤的豹海豹躺在浮冰上愤世嫉俗。有人居然捡到了脱落的海狗皮。贼鸥在空中将掠获的小企鹅一撕两半。蓝眼鸬鹚孵出了雏鸟。岛上风的味道是企鹅的味道。阿根廷科考站常有人参观。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所有人发出那句感慨,直到日落时,船驶入拉美尔水道。
儿子十分善解人意地要求留在船舱里休息:“妈妈你去拍照吧,我自己睡觉。”
几乎所有人,包括船员,都涌上甲板,我也在其间。
拉美尔水道,昵称“Kodak Gap”,1600米宽,11公里长,船行其间,两岸雪山相对出,美不可言。船长细心地计算好时间,赶在日落前驶入,他特意降低了船速,以便我们有充分时间欣赏这条“十里画廊”。
“一切代价都值了……”这时,你会听到所有人的同一句感慨。你会一再想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挪威人阿蒙森形容南极的那句话――“这里就是仙境” 。
从晚上十点一直到凌晨一点半,我一直站在甲板上。当我觉到冷时,寒冷已经浸透。回到船舱,儿子已经呼呼酣睡,床边茶几上赫然放着一个银色托盘,里面是全套红茶茶具,茶壶里的水还滚滚热!我正想感叹船家的管家式服务如此周到,忽然看到了茶托旁的东西:在船上提供的便签纸上,儿子用圆珠笔画了一瓶花。我坐下来,沏了一杯茶,慢慢喝,感觉身体由内而外暖起来。儿子从小不善绘画,画一瓶花,是要费些工夫的。这花告诉我,这茶不是船上的例行服务,那是儿子为妈妈准备的礼物。是谁告诉他,我几小时夜不归宿会需要一杯热茶?是怎样一颗心让他想到看南极日落归来要有花迎接妈妈?
南极行开始时,一到登陆我就急三火四,叮嘱儿子戴帽子、戴头套、戴眼镜,两个人都一身汗;登陆后就总担心,担心相机设置不对以及镜头焦距不够,担心儿子错过看企鹅,看海豹,看各种该看的东西。殊不知,孩子有自己的尺度,他的南极旅行清单中,没有“南极十大不可错过的体验”,也没有举着旗帜摆拍 “到此一游”照片的任务。他爬雪山滑雪道,淌海水舔浮冰,体验了很多“第一次”;在半月岛,他孜孜不倦地拍企鹅,因为他想回去让同学看看“企鹅肚子下面的世界”,这些照片后来成为他参加GESE(三一口语)九级考试时自选话题的重要道具;他在船上向同行的摄影师学习如何拍摄飞行中的海鸟,然后自己一两个小时在甲板上实践,殊不知我们的相机没有那么先进的功能,他拍了一千多张照片,没几张清楚,但那段时间他仰头看了多少飞翔的姿势啊。
因为南极行,儿子错过了期末考试。但是,南极教给他的远远比一张考卷多得多。而南极也给我上了难得的一课――
起初,我以为带儿子到南极是我在带他看世界,后来慢慢才懂得,孩子仿佛是这世界给我们的另一双眼,世界借由他的眼睛袒露在我面前。我们共同去看,才可能把它看全。
南极让我们学会了一个词,试!
带孩子到南极,听上去已经够“疯狂”,但更“疯狂”的事是我去南极前想都没敢想的――下海游泳。
登陆迷幻岛(Deception island)鲸鱼湾前,每个游客都被告知:如果不想错过在南极最刺激的活动,一定要内着泳衣。迷幻岛实际是一处独特的环形火山口,火山口部分倒塌,形成了一条天然航道,通往火山口内部湖区。无论外面风浪滔天,港湾里也是水波不兴。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港湾之一。岛上有一座废弃炼鲸油厂,是当年英国人租赁给挪威人的,专门用来处理捕鲸人利用鲸脂炼油后处理不了的鲸尸。1969年的那次火山喷发,害得当时驻守在这里的5名英国人不得不顶着瓦楞铁板躲避四处迸射的火山岩落荒而逃,幸亏智利站派出飞机营救才得以脱险。
这里的沙滩是黑的,缭绕着淼淼升腾的白色水汽,岸上到处是废弃生锈的炼油桶和破旧厂房。火山使得这里的地热资源丰富,随便在沙滩上挖个坑,里面汩汩而出的水都很烫手。真正下海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虽然岸边海水混合了温泉,水温尚可,可是走进去十几步远,水温骤降,跳进去,那绝对是冰火两重天啊!曾经有人形容那种感觉像是“一万根针扎在皮肤里”。
出发前儿子还在感冒,鼓励他下海,会不会生病发烧?阻止他试,这后悔药谁吃?对于妈妈,试与不试,在南极成了大问题。
在岛上,可以爬山去看火山口,也可以参观那些废弃的木屋,腿脚快的还可以去找找当年捕鲸人的墓地。我们在海边溜达了一个多小时,其间的活动包括:透过鲸骨遗骸窥看远方,向一只帽带企鹅邯郸学步,观察沙滩上一种不知名透明生物的身体结构,挖沙聚水探测水温。做这些时,我心里其实一直在为“试与不试”纠结着。当我独自转悠到废弃油桶那里大拍特拍几只傲慢海鸟时,一回头,儿子已经在沙滩上了,这一回他自己做主了!
接下来是典型的电影快进镜头:冲下海,跑上来,再冲下海,再跑上来。快门声伴着尖叫声,喝彩声混着大笑声,儿子成了船上第一个跳下水的中国人。
没感冒没发烧,没有出现担心的各种“后果”。这次勇敢的试水经历,成为我们南极行津津乐道的谈资,让儿子从此爱上水中探险,而且赢得很多女孩的“友谊”。
这段共赴世界尽头的南极旅程,让我们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和兴趣,让我们的内心有了某种频率相同的共振,我们看待彼此的目光更宽容、深厚了,我们有信心携手去走更长更远的路了。
带孩子到南极,无关炫耀、猎奇、赚人眼球。南极旅行,功效不能急功近利地衡量。也许多年以后,当儿子在他的成长中遇到了难以逾越或抉择的事情时,九岁的南极行,会帮到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