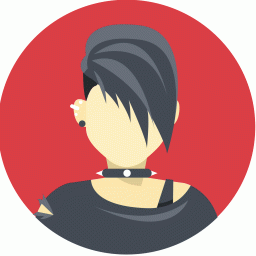浅析“哀而不伤”:儒家中和的审美原则对中国古代文人悼亡诗的影响
时间:2022-06-10 11:30:26

摘 要 “哀而不伤”,忧愁而不悲伤。多用来形容诗歌、音乐等具有中和之美。也比喻处事适中,没有过与不及之处。中国古代文学,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必然是巨大而深刻的,而其中儒家的“哀而不伤”的中和观对诗歌的审美尺度的影响更是尤为突出的。这一点广泛的反映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上,特别是在悼亡这一特殊题材的创作上更是明显。
关键词 哀而不伤;中和;悼亡诗;影响
一、“哀而不伤”:儒家的中和观
孔子曾经评价《诗经》中的《关雎》篇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P30。“哀而不伤”,忧愁而不悲伤。多用来形容诗歌、音乐等具有中和之美。也比喻处事适中,没有过与不及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儒家倡导“中庸”,反对片面化和极端化,这些在文学中则表现为主张有节制地宣泄情感。孔子所说“哀而不伤”就是这个意思。在孔子看来,喜怒哀乐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而艺术正是人们用来表现这种情感的手段。适度的情感表现,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而过滥的情感宣泄,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害的。所以孔子主张适度的、有节制的情感表现,反对过滥、无节制的情感宣泄。而《关雎》对哀伤和欢乐之情的表现,即无过分之处,又无不及之处,合乎中庸之道,堪称典范,所以备受孔子的赞许。
中庸是儒家哲学、美学思想的基础和灵魂。孔子极其推崇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1]P63,同时,儒家还把中庸原则应用到了艺术审美领域之中。“中庸”即中和庸常之道也就是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 [2]186孔子在赞美《关雎》时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显然是“中和”原则在文艺美学方面的运用。这也是被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者称为“温柔敦厚”的诗教。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对于情感的节制的行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对情感的合理的节制,有利于诗人们从根本上自觉的把握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即使作品能够起到表达和宣泄情感的作用,又使得作者不会被情感所驱使,自觉的避免出现一些过度、过激的情感和表达方式。
在《诗经》以后,虽然中国文学史上陆续出现了不少激情昂扬、充满浪漫主义的文人及其作品,如屈原、李白等,虽然他们在感情表达的深度和烈度方面相比《诗经》而言有了突破,但他们对情感的宣泄仍是有限度的,是以理节情的。他们仍然严守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德规范,谏诤明志,心系主上,从不跨雷池一步。其激愤之情最终还是归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与下层民众揭竿而起走向反叛之路的行为大不相同。而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悼亡诗而言,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
二、对中古代文人悼亡诗的影响
悼,悲伤、怀念之意。悼亡,就字面意义而言,指的是生者对已逝之人的哀悼思念。“悼亡”一词,依王立先生的见解最早见于《南史・卷十一》:“宋文帝时, 袁皇后崩, 上令颜延之为哀策, 上自益‘抚存悼亡, 感今怀昔’八字, 此‘悼亡’之名所始也。” [3]P320悼亡诗,指的是“夫妻间丧偶后生者哀悼亡者的诗篇。” [4]P2悼亡诗,是关于爱与死的篇章。这里既有痛失所爱的悲伤,也有对生命终结必然与不可挽留、不可反复性的深沉思索。可以说这是人世间最令人悲伤、痛苦的两件事之一了。
文人悼亡中,即有对夫妻之间天人永隔的悲痛惋惜,也有丈夫对亡妻的不悔深情,更有由痛失爱妻的悲苦心境引发而来的对悼亡者自身未来前景的预见性的悲伤。但是,就算内心多么痛苦不堪,使人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的在诗篇中有所节制,也并没有在不可排除的死亡焦虑的压力下悲愤的抗议、呼号。不得不说,这是受儒家“哀而不伤”的中和的审美观的影响。
(一)中国式的死亡焦虑
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人在活着的时候是无法亲身体验死亡的。而一旦亲历,便再无能力言说。正如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所说:“向不在此在过度恰恰使此在不可能去经验这种过度,不可能把它当做经验过的过度来加以领会。”虽然自身的死亡不可在个体生命还存在之时有所体验,但是,他者的死亡却是可以经验与把握的。虽然“我们并不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我们最多也不过是‘在侧’”,但我们能且只能以并非真正死亡的他者的身份来对其加以体验。悼亡诗的作者们,正是在亲身经历了身边最亲爱之人的死亡才深深意识到了死亡这一终结的真实存在,以及对自身生命的威胁。“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4]P74越是亲近的人的亡故,对于生者的打击与震撼也越大,使他们对生命及死亡的感触就更加强烈,思考也愈加深沉。
死亡,即生命的消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更是无法逆转,已成既定事实,就回天乏术。这是无论每个人愿意与否,都必将面对的最终结果。“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5]P266加之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大多并不相信所谓的彼岸世界,而佛教对文人的影响只限于提供了一个精神上得以休憩的净土罢了。但是,任何个体生命,从其生命的本然意识出发,却始终都存在着将生命永恒的延续下去的冲动和渴望。这样的矛盾,造就了不可消除的死亡焦虑。这样的焦虑极易使人陷入一种猝然而生的痛楚、悲伤、绝望之中不可自拔。
然而,受讲求以礼节情的中庸之道的儒家“哀而不伤”的影响,更多的是内心形成一种较为缓和的悲伤与哀愁,即哀死的心理。在哀死的过程中,始终对死亡的自然性和不可逆转性有着相当的理智和冷静,而不是绝望的呼号和悲愤的抗议。表现于诗歌中,就会流露出一丝丝令人感伤、叹息不已的哀愁情调。受到“哀而不伤”的中和的思想的影响,哀死“是对死亡造成的世俗生存欢乐消失的哀伤,流露出来的恰恰是极其强烈的对现实生活的眷恋、执着。它仍然肯定人生,甚至是由哀伤而更加深沉的肯定、热爱热爱人生。”因此,文人们虽然对死亡深怀焦虑,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人生、灰心失望,在他们的诗句中,也不会消极的否定人生,更不会将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而是在世俗的生活中慢慢的消解对死亡的哀愁。这是属于中国式的死亡焦虑。
(二)温柔的感伤
人总是要在失去了重要的东西之后才会愈加发觉它的珍贵。生命短暂,美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再恩爱不移的夫妻,再好的爱情也终有分离,走到尽头的一天。不能再和人生中举足轻重的爱人聚于此刻,分享喜乐哀伤,相伴共同走完人生多彩的路程,怎不令人扼腕怅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的离去,对诗人而言受打击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面对亲爱之人的死亡,似乎有太多要说的话还没来得及言说,太多的情感也未及表达。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盛行的社会中囿于封建礼教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很少会,也不会想到要在日常的社会及家庭生活中轻易的写诗来对结发妻子一吐深情。“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 [6]P99 “男尊女卑的长期伦理价值取向造成了中国文学某种缺憾,这缺憾只得不可避免地由痛发失却爱妻的遗恨中部分地得到补偿……许多文人,也只有在悼亡哀祭之作中才得抒吐对女性的依依款曲。”[7]P326特别是当往日的欢乐、幸福、温暖同今天痛失爱妻的孤单、凄清、冷清相对比时,内心的哀伤更是难以抑制,凄凉、心酸。
但孔子说:“丧致乎哀而止。” [1]P200人失去亲人,不免产生哀痛之情,这是人性使然,但这种哀思之情要适可而止,不要沉溺于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还要“哀而不伤”,要适度的、有节制的表现情感。所以,即使是如此悲伤难抑的事情,还是要有所节制。你看:
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
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
譬令愚者寿,何不假其年。
忍此连城宝,沈埋向九泉。
――梅尧臣《悼亡》其三 [8]P63
这是梅尧臣的一首悼亡诗。首联一句“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可以看得到,作者深知死亡的自然性,生命本来就有长短,没什么理由去质问苍天。“岂敢”二字道出了诗人对死亡的无奈、无助的悲伤心境,无力回天,只能痛心。第二句道出了诗人对妻子的一片深情的思念,并从侧面体现了亡妇的可贵之处:看尽了人世间的美妇,却再也没有人能比你更加美丽、贤惠的了,这叫我如何不想念你。而“譬令愚者寿,何不假其年。”一句则道出了诗人内心的不舍,以及对爱妻亡故的事实的难以接受:愚钝丑陋的人可以活得长久,却为何不给我那“美且贤”的妻子多些时日的寿辰呢?这也只算得心中的一点感慨而已,并无抗议与不肯承认的想法。而最后,还是不得不对现实低头,要“忍此连城宝,沈埋向九泉。”虽然诗人心中不舍,却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沈埋”。
这就是儒家“哀而不伤”的中和思想影响下的悼亡诗,没有激烈的言语,没有强烈到不可抑制的情感。有的只是字里行间那挥之不去的淡淡哀伤、落寞。而在寄托思念表达哀伤,对死者及其所带来的与生者共有的美好往昔、真挚情意的不舍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亡妻地位的无可替代性及生者对现实生命的深深眷恋之情。即使再悲伤的悼亡诗作,也不会走向极端。这是属于中国式的温柔的感伤。
三、小结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其中儒家的“哀而不伤”的中和思想对诗歌的的影响更是尤为突出,这一点广泛的反应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上,特别是在悼亡这一特殊题材的创作上。受儒家“哀而不伤”的中和的审美观的影响。文人悼亡中,即有对夫妻之间天人永隔的悲痛惋惜,也有丈夫对亡妻的不悔深情,更有由痛失爱妻的悲苦心境引发而来的对悼亡者自身未来前景的预见性的悲伤。但是,就算内心多么痛苦不堪,使人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的在诗篇中有所节制,也并没有在不可排除的死亡焦虑的压力下悲愤的抗议、呼号。让我们看到的是属于中国式的死亡焦虑,属于中国式的温柔的感伤。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011.07重印)
[2]崔高维(校点).礼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000.03重印)
[3](唐)李延寿.南史・卷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尚永亮,高晖.十年生死两茫茫――古代悼亡诗百首译析[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5]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等.吕氏春秋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7]王立.永恒的眷恋――悼祭文学的主题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8]朱东润.梅尧臣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