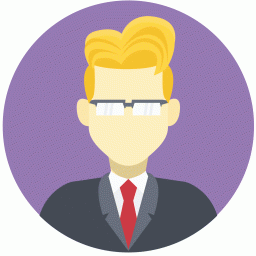话说“孝道”
时间:2022-05-17 03:03:03
“孝”,如果仅指晚辈对先人的那份感情与牵挂,那是美妙的尤物,但是中国古代奴才文人借“孝”说事而炮制出的那个“孝道”,却是贻误中国文明进程的孽障。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必须予它以足够的批判,不使它妨碍今人、贻害后代。
以孝治国,贻误千古
年少时乱读书,读到“君子以孝治天下”时,很是不解。这“孝”明明是一家人当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和应尽的赡养义务,一种简单的初等社会行为和朴素感情,怎么就能够把这种谦恭和温顺作为工具来处理复杂纷乱的国家大事呢?虽曾讨教过几位长者和先学,却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几十年来就一直困惑着我。
而今我知道了,我所疑惑的这个问题,正是产生各种各样“中国特色”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人从一个人人所能感知的简单常理――对至亲的爱――起手,经过一种未经论证的“非逻辑”的推论,而演变成一套存在致命缺陷的理论,这套“说法”,就是所谓“孝道”,它内在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和谐,乃至人伦的畸形。
孝,是许多种“爱”中的一种,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没有特别地对它予以高度关注,只是中国古人特地把它提纯出来,借此胡乱地比喻、推演,把它无限地拔高,几乎与宇宙存在的法则相提并论,成为“天道”的化身,这就大谬了。这暴露了中国文化视野的局限甚至浅薄,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自然生长和发展。中国人在“孝道”被盲目尊崇的这两千多年中的遭遇,就一直被它的荒谬所纠缠,至今未得脱身,因此很有必要就此多说一些话。
“孝文化”是家族或家庭的产物,只有婚姻成为社会普遍的文化氛围,才有可能产生关于“孝”的道德规范。在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民族有过如中国人这样丰富、繁杂、畸形的关于“孝”的文化观念体系,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讲,这是生活方式决定的。
“孝文化”在商代以前是没有特殊地位的,到商代为止,王位继承制度还基本上是兄终弟及,可见那时的纵向血亲的力度还不够强劲,或者那时人的寿命还不足以支撑后代人顺利长到接班年龄。
学者曾昭旭说,在“孝道”观的建立过程中“孔子居于关键性的地位的”《孝道观的发展》)。他认为这是孔子所宣扬的恢复“周礼”的总行动纲领的一个部分。据说孔子曾经为曾子开过一个“小灶”,专门给他一个人单独讲述了自己关于人伦秩序的见解,这就是《孝经》起源的一个说法。许多学者质疑这个说法,说《孝经》成书于战国时代,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作。我更倾向于它产生于汉代以后,而且是假托孔子而作。我这是反那些“孝道”的尊崇者而动,他们想给这套理论找一个伟大的始作俑者当招牌,而我却不愿意让这样糟糕的东西与孔子发生直接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孝”的语录,但不管怎样,在孔子时代关于“孝”说法还仅仅停留在学术和教育的层面上。不应当被人指摘。言论在当时没有禁锢,这是文化生长发展的背景,条件是任何一种学说不能妨害别的学说的存在,更不用说压制了。学者说了什么都没有关系,关键是王者宦者不能随便作为。正如希特勒是恶魔,而尼采是有永恒人类价值的。
到了汉代,就有了关于“孝道”的明文法律。《后汉书》中就有关于“王杖”作为执行“孝道”的法律,只是内容没有流传下来。80年代在甘肃武威发现的“王杖诏书令”,就有关于“孝道”的详细的记载。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年满70岁的老人由朝廷赐予他“王杖”,这是一种顶端雕刻有斑鸠形象的特制手杖。持有“王杖”者,在全社会享有优待和照顾。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当于俸禄六百石的官吏。如果有人侮辱持有“王杖”的老人,将以蔑视皇上的罪行被处以死刑。持有“王杖”老人做生意的,可以免税。那个时代的人能活到70岁是很罕见的,所以才能有这么一部法律。这是“孝道”与政权最早发生联系的一个例证。“孝道”进入政治生活,也就开始了危害民族身心的历史。
“孝道”成为法律以后,成为不允许由别人胡乱解释的王法,逐渐由于绝对化的刻板遵从,它把原来处于原始状态的那种孝义变化成一种“愚孝”,并开始禁锢人们的大脑和奴化人们的心灵。
我认为,中国文化之停滞、倒退乃至畸形化,始于汉朝。你看,思想与学术垄断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垄断对历史的记录权和解说权是从司马谈、司马迁开始的,剥夺民生权、垄断流通与盐铁业等经济命脉是从桑弘羊开始的。而此时所说的“孝文化”的变味,也是从汉朝开始的。从此“孝道”就成了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思想奴化教育的一个工具。
“孝道”影响宏观社会的作用,开始时更为直接的体现是在皇家内部。一代帝王在进行更迭时,谁能抢先一步握到权柄,就能对历史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胜利者因为得到了绝对的话语权,也将流芳百世。这样露脸的事一定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所有手段包括文化习俗都会在此时悉数用上,“孝道”当然也不会被露掉。
后宫干政在汉代是十分频繁发生的事件,几乎代代都有。这个现象就是“孝道”这个文化习俗引发的后果。杨联升先生在《国史上的女主》中就提到过孝道在治国方面的负面效应。他说,“在以儒教为本的传统中国,因为鼓励孝的行为,母亲的地位通常较高,这是有些太后临朝称制的前提。”自吕后专权被镇压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后宫仍旧依仗外戚势力,实施专权。这样的事例一直持续到汉代灭亡。到了曹魏,曹操的卞夫人还是如此,她当了太后和太皇太后之后,频频干预朝政,把曹氏的政权折腾得愈加虚弱,不久就被司马氏所乘,江山随即易手。一直到隋文帝创建了科举制度,并依此组织文官政府,接受皇帝的委托管理国家大事,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后宫的干政。但是时不时地还发生过未经“专业训练”的女人直接操持权柄的事例,如武则天的上台称制等,连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朝的逊位也发生在女人当政的时候。
我不同意把国家的动乱和衰败嫁祸于女人的说法。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些从小在深宅大院里长大的女人,在“孝道”等等压制人性的文化氛围里长大,难有接触大千世界的机会,与那些饱读经书、社会阅历较为丰富的文官们相比,眼界与胸怀必然相差甚远。她们占据了本来应当是政治家的位置,极不可能做出成绩。所以,不是女人应当对“乱国”负责,而是让那些有野心的女人乘机取得顶级权力的文化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道”)才是祸水的源头。
“孝道”只讲资格,不讲是非,说话者与聆听者被摆在不平等的地位上,没有办法把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引入进来,不容对既定的陈旧制度进行改革。那些中国历史最上的黑暗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些本无资质成为领袖的人物依仗传统习俗所赋予的特权,获得了最高的统治权。一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缺陷,而造成这样的事实的最直接病根,就是“孝道”。与上面所说的“君子以孝治天下”正相反,我想说的话是“孝道”根本不是治国之本,而是祸国之道。
“孝”的生物学意义
“孝”是不能凭空就变成文化的一部分的,它必然有更深远的生物学法则渊源。我在研读和思考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的时候,有了如下的颖悟:“孝”的根源是动物界的血缘关系的纽带。
东非的狒狒种群很大,动物学家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老年狒狒种群的地位在所有哺乳动物群体中最受尊崇,它们不会被自己种群所抛弃。而狼群、狮群等就不行了,头领一旦稍有体力不逮,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被淘汰之后,它们也决不可能留在种群内部挨活度日。但是,当上头领的老狒狒在以武力捍卫自己的地位时,能得到群内其他的狒狒,无论是雄的还是雌的的帮助,也就是说狒狒的“族长”能得到“后人”有力的支持,动物学家也没有发现有老年狒狒惨死荒郊的事例。这看似简单,但相比其他的动物种群,就不是这样了,其他种群需要挑选“族长”的原则只看谁更有力量。
这样,狒狒头领的执政年限也就大大长于其他有头领任职的动物兽王了。于是在狒狒的这个种群里,由于头领的执政年限较长,也就更有可能在种群内部留下长寿基因,而不仅仅是体质优秀的基因了。久之,这样的长寿基因就必然在整个种群内弥散开来。种群的“领导”执政年限加长,一个可能的效果是出现大“家族”,造成“三代同堂”以至“N代同堂”的存续,一个直接的好处是增加种群中的个体数量。所有成员都与头领存在血缘和姻缘关系,这对种群的凝聚力和它的兴旺发达很有正面意义。假设曾经有别的狒狒群有别样的“习俗”,不那么尊重“族长”,久而久之,小的狒狒种群必然为大的狒狒种群所征服或消灭,它们的领地也会被并入“大家族”狒狒群的天下。
人类有远比其他哺乳动物更长的寿命,我推想,这就是原始的“孝道”使得人类远祖能够有更大族群,从而开始了征服整个地球的伟业。
在炎黄时代,中国人内部的兼并和征战,也可以依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当年在中原的逐鹿地区,炎帝与黄帝两个部落联合打败蚩尤部落,后来黄帝又打败炎帝部落,其道理、其过程我设想都是这个逻辑的合理推演。
以中原汉族人为主要后代的黄帝部落,确实比以苗族、瑶族为主要后代的蚩尤部落更讲究“孝义”,而以西北人为主要后代的炎帝部落则处于上述二者之间。其他人种和种族的民族,只要历经残酷争斗淘汰而存留下来,想必也是如此,只是不能做更为详细的论证了。
“人类的寿命为何远长于其他同体形的哺乳动物”原本就是许多不同领域理论的注目点。不少宗教的理论就以此为“人类最为神灵所钟爱”的依据。我认为这是始祖人类的组织原则造成的。“孝”这个尊重(或者“盲从”)“族长”的习俗或机制,是人类在恐龙灭绝以后能迅速崛起、进而征服其他强悍动物,成为新一轮地球霸主的根本原因。人类的寿命那么明显地长于其他哺乳动物。所有体型小于人类和与人类相仿的动物的个体,其生命周期都远小于人类,而体型远大于人类的象和鲸的寿命也仅仅稍微长于人类一点点。可见,大自然并不是以身体强悍为唯一原则来选择动物王国的王者的。人类是因为有了“孝文化”,后来才以此取得种群数量的优势,最终战胜狮虎豺狼而成为现在的地球之王的。
再举蜂群社会和蚂蚁社会这个例子。
蜂和蚁,它们的社会形态,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几亿甚至十几亿年的时间,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它们的面前连小弟弟都难以比拟。它们的社会结构比人类的更加稳定、更加恒久。个体的数量也更为惊人。我认为它们的“成功”,也是缘于亲体之间的血缘链条(或称为“血缘键”)的强健有力。它们种群中的个体,与“族长”――蜂王和蚁后的血缘关系比人类更为直接,因而它们对她的“忠诚度”,也远非人类可比。
由此,我可以据此对外宣称一个“定律”,内容是:“生物种群的规模(以个体数量的大小计),取决于这个种群社会里的纵向血缘键的强度,血缘键强有力的,种群中个体的数量就大,反之就小或无”。
在人类文明史中也能找到上面这个“定律”的根据。那些“纵向血缘键的强度”大的民族,人数就多,“纵向血缘键的强度”弱的民族,人口数量就少。我们中国人的“纵向血缘键的强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中国人最讲”孝道”)人口数量当然也就最多。不同意我这个观点的读者尽可以对此一笑置之,也希望那些严肃的批评家不要太过认真,这是我为了阐释我关于“孝道”的理论而临时打造的一块基石。
人们比较多地注意蜂群和蚂群内部的团结,却常常忽视它们群体内的残杀。
也正因为他们都是以血亲为原则组织社会的,因此一旦出离了这个血缘圈子,就没有了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我曾经听过一位养蜂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蜂群之间“战争”。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发生,养蜂世家都各有自己的“秘诀”,这些“秘诀”有专业技术成分,也有迷信的色彩,传子不传婿。其手法就是用巧妙的手段迷惑它们,敉平它们因血缘不同而产生的鸿沟。不同蚂蚁家族之间的战争就更是广为人知了。蜜蜂和蚂蚁这些同种不同族之间的战争,俗称“窝里斗”,中国人一向精通此道,可以将其认定为“国技”。究其缘由,还是来自血亲链条造
就的家族政治。
“孝”的社会学意义
子曰:君子务本。孝弟也者,人生之本也。我从中感知的是:如此发扬下去,一旦过分,就会造成“人只知有家族,而不知道有社会”。后来的儒家学者把它又修正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多多少少修补了孔子的漏洞,但我还是感到这话说得很别扭。
第一,怎么说着说着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什么硬要把与家族血缘毫无关系的君主拉扯进来了呢?这真像是期间申请结婚的一对新人也要先三呼万岁以后才有资格取得结婚证件一样,显然是有一股外力在压迫着谈论者或当事人的灵魂,让说话者言不由衷。
第二,如果用逻辑的思维来解释这句话,又是一个不通:事亲是家庭伦理,立身是个人修养,而“事不事君”,“事这位君主”还是“事那位君主”,是政见问题或社会价值观差异的问题,这又进入了政治学的领域。在讲述“孝”的时候,显然是把处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内容混为一谈了,这违反了做学问的常规。也可以这样判断:此学说极不严谨。
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永远也长不大的原因之一。逻辑是学术的生命力,没有逻辑的学术不会存续多长时间的,它会在其他有生命力的理论碰撞或冲击中不堪一击。原因就是它由许多孤立的松散的结论组成的,而它们则仅仅是说话者为了取得眼前利益而仓促组合起来的,不会建立起宏大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很快就会淹没在更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发展浪潮之中的。但是,儒家理论就这么久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存续了20多个世纪,这个现象似乎违反了上面哪个结论。这里面有太多的话要说,此时只能放下不提。
以“孝道”为根基的皇权世袭制度在中国之所以能长久地存续,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中国人惧怕竞争,为了简单生活而绕着社会问题走的生活哲学――这又可见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
你想,别的民族为了社会的存续,有的要建立玄虚的神乎其神的宗教思想体系,――如回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天主教诸民族,有的要建立复杂的社会法律系统,――如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中国人也曾经试图建立复杂社会法律系统,有过这样的实践或经历,时间发生在战国后期和秦代。但是由于那部法律(即“密如凝脂”的《秦律》)是战争年代的产物,由于秦始皇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和平时代来施用,让老百姓感到生活的紧张和压抑,很快就被大众所厌恶,不久就被来自民间的造反者所否决。其实,《秦律》之“恶”,是由于它没有与时俱进,如果能有富有远见眼光的能臣看到这一点,帮助秦始皇及时对《秦法》进行修订,与时俱进,因时制宜,想必中国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那时实施法制的形式很具有现代性,很能为时人所遵从(只是内容不很好),不若后来的中国人那样轻视甚至鄙视法治,只仰首盲从于活着的强人的喜好和权柄了。
为了压低统治成本,简化管理社会的制度,中国人从此就“以家比国”,以父子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一说“国”就想到“家”,“国法”对“家规”,“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紧接着就是“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这样,就把人们对自己父母的依附与感情,嫁接到对那个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君王身上了。巧则巧矣,却丝毫没有道理。中国人现在还仍然是这样,“国”的组织原则与“家”的组织原则在思想上依然是千丝万缕、难以厘清。人们普遍认可“上智下愚”,服从和人身依附的情况根深蒂固。究其根底,都是“孝道”所致。
国家的管理方式固然是变得简单多了,但是许多存在于国家治理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却因为在“家”的范畴内的缺无(例如我们中国人一向避讳的竞选方式的运用),就使得中国特色的国家管理方式因此就规定性地缺乏了人性关怀――义务与责任的不对称。如果说家长可以打孩子的屁股,那皇帝也就有权当庭脱下大臣的裤子打他的板子。这虽只是一个比喻,历史上那无数种胡乱“比照”的愚蠢做法(例如所谓“国孝”等恶俗)实在有失中国文化的脸面,降低中国文化的品位和档次。
“国法”与“家规”往往是一起拿来“说山”,相互比拟。殊不知,这在长久地生活在法治环境中的外人看来,就像是古代的祭司在导演着现代社会的生活。人家说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氛围“很神秘”,很“不可理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只是人家不能直接把“荒唐”这个词说出口来,而我们往往却浑然不觉知。
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在最近30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被越来越普遍的企业化的组织冲击着人们以往的那种人身依附的观念。企业化组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契约精神”,它体现的是缔约双方的平等,以及双方对信息的充分了解,没有欺瞒或欺诈。要摆脱这种从“孝道”演化而来的人身依附的传统社会生活准则,还将遭遇很大的阻力。除了上述思想上的顽固势力的作用以外,已经是畸形化了的人口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社会安定、平稳转型,我们还有时不得不屈从于与孝道相类似的一些原则,如多一些服从,少一点责难。
“孝道”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集中体现是服从,而且是无条件的服从。要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地服从,做一个驯服工具,有思想的人想要先理解都不行,要“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这比孔子当年所说的“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矣”还厉害,根本不给你可以着手修改君父旧有的清规戒律的期限,也就是说,永远不能改革旧制度,只能“按既定方针办”。――祖宗之法不可更替。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原则下守了两千多年的旧。
在西方,人们把所有的荣光和赞美都归功于上帝,而在中国,人们最大的成就是实现光宗耀祖。西方人上千年的赞誉使得上帝在他们的心目中获得了无上的地位,而中国人只知道各自光耀自己的门楣,就造就了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家族。家族事务是门前雪,社会公利是瓦上霜。家族意识就这样冲淡了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社会被人家称为“家族社会”也就毫不奇怪了。一位中国学者说过这样一句激愤的话:中国人(他在前面说的都声明主要是指汉族人)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有有信仰的民族都被择开以后,剩下的那些只看重自己血亲的那一群人。别的意义不说,我认为这句话把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在“孝道”的熏陶下所造成的民族狭隘性揭露得淋漓尽致。这大概可以解释我们曾经的外号“一盘散沙”的来历。许多辛酸的民族往事都与这个“一盘散沙”密切相关。“孝道”就是这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它的巨大影响力的。“孝道”和它的宣扬者之罪孽不可不查,不可不究。
评论几则“孝”的事例
说了这么多虚的道理,顺便讲则有关“孝”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是汉朝时的故事。郭巨,河南林县人,父亲早亡,侍奉母亲至孝。有一年旱灾极其严重,已经接近断炊,为了能让母亲有口饭吃,决定把儿子活埋。在他们夫妇二人掘土时,挖出一锅黄金来。
――现代人一听就知道这很像是一个荒诞无稽的神话,要是在今天,他们夫妻犯的就是杀人未遂之罪。
第二个是晋朝的故事。王祥,山东临沂人,母亲早丧,继母不慈。但是王祥却是个极孝顺的孩子。继母想吃鸟,他就上山捉鸟,继母想吃鱼,他就下河捕鱼。一天,正值天寒地冻,继母的馋病犯了,要吃活鱼。王祥就到结冰的河面上脱下衣服用体温融化了冰面,得到了两条鲤鱼,抱回家去孝敬那个不仁义的女人去了。
――显然这是件不合乎自然法则的事情,一个人那里有那么大的“热度”能融化冰河呢?人们也能从中体味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那种人格的不平等,反而这样的事实却成为一个楷模性质的典故。
以上是取自《孝经》的故事。我们严肃的道貌岸然的教育家们就是用这样的教材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后生们的。再说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现在时”的故事。
在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电视节目中,有个教育家说,一位父亲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不理想,就责骂孩子没有出息,说“白白养活这么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孩子听了,马上回了一句:“谁让你们养活我的?你们生我前征求我的意见了吗?”问得父亲哑口无言,只能改文斗为武斗,把孩子打一顿出出气。
这个敢说话的孩子很让我感到钦佩,因为这是我幼年挨我父亲打时,想说而不敢说出口的话。用传统“孝道”的观点看,这个论题的基点已经超出了“范围”,进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盲区了,孔子来了也会没有词儿的。一个孩子能揭开长于“教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短,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领域(实际上只是一种狭隘的伦理说教)一点也不深刻,更谈不到广博。其实,这个孩子提到的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教育思想体系里,根本就不成其问题。因为在那里,没有“孝道”,没有强迫,没有谁必须服从谁的问题。
易卜生在《群鬼》这部戏剧中,也曾经借助于一个患上先天疾患的孩子的口吻如此这般地责备他的母亲的。这样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获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的高度评价。而今,我们的孩子仍然这样发问,说明那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也说明“孝道”还应当继续受到严厉的批判。
在我看来,为中国人所常说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一个荒谬之词。依照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传统中国人养育孩子这个行为不外有三个理由:第一是防老、第二是承嗣,第三是为发泄而承担后果。这三个理由都不是多么磊落,对社会却造就了人口过剩的恶果。我的上述思想是受明末思想家李贽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位思想家最后因此而遭难,在打给皇帝的检举报告里,据说有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儿女有什么理由孝顺父祖?他们不过是父亲的一泡尿。”在被押解进京的路上,他自知难以说说清楚,愤而自杀。
确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哭闹着来到这个他们本不情愿来的这个世界的。每一个造成这样事实的那个成年人或那对成年人或那群成年人,在本质上都是“绑架者”。而中国的“孝道”又在事后告诉那个被绑架者,“你的地位低于绑架你的人,你必须做他们的孝子贤孙”,这是一件很不讲道理的事情。而用现代社会的伦理则可以较为人性化地处理好这个“悖论”,――只是此处就不能再多说了。
最后说一句话。我对我的父母充满了感激和怀念。如果他们还在世,我是不想让他们读到这些文字的,以免引起他们的自责。如果有人因此而判定我也受到了“孝道”的毒害,我也不予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