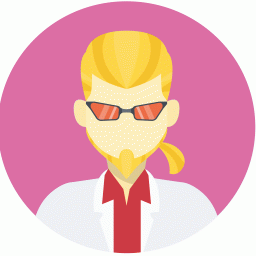火烧云 第2期
时间:2022-03-12 01:31:14
出事的前一天傍晚,天气突然热得要命。这是很奇怪的。谷雨才过呢,对于习惯于按二十四节气过日子的乡下人,他们觉得天也热得太早了一点,大伙儿都还没作好热起来的准备。许多人心中涌起一阵极大的不安。
海运爷照例拎着铜锣挨家挨户打了一遍,吆喝着让大家小心火烛,烧完饭煮完猪食后记得用冷水把灶膛里的火烬泼灭。海运爷是村里惟一的孤老,这是村支书海宝安排给他的活儿。海运爷掐指算了一下,明天就是火曜日哩,难怪天气这么热。
没人注意海运爷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汉子们都在自家门口一桶桶往地上泼水,阳光晒了整整一天了,哪怕起一丝微风,尘土就开始飞扬。连那些看家护院的狗,一闻到这股味道就开始咳嗽。用水压一压就好了。待到汉子们把屋坪浇透了,各家的女人和孩子,又纷纷把饭桌和竹榻从屋里搬出来。都提前开始过夏天的生活了,生活很有味道,随处可以闻到烧鱼、烤山芋和柴火蒸饭的香气。狗鼻子们贪婪个不够,绕着桌腿儿嗅来嗅去。
这时才有人注意到海运爷已经回来了。海运爷住在村里的牛栏里。牛栏用土砖砌了两层,顶上盖的茅草顶。那还是大集体时的遗物,散伙时也没有谁拆这东西,几块干打垒的土砖,一堆破茅草,拆它干嘛。都多少年没人管了,四下都破着。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孤老海运爷搬进来了。自从他搬进来之后,这幢空了许久的牛栏反而多了一种鬼魅气息。老汉每天像幽灵一样从这牛栏里钻出来,夜里又返回里面去。听见那木梯嘎吱嘎吱好一阵响,一点儿火光就弄亮了,像一点鬼火。村里好多年前就点上电灯了,可谁往这牛栏里拉电呢。
这会儿老汉还没掌灯。可能是天气太热了,海运爷把脑袋伸在栏外吹风。他的脸被别人家的电灯照着,脸上满是干了的血迹。许多人心中于是涌起更大的一阵不安,觉得会出啥事。果然就出事了,不一会儿人们就听见一个女人在牛栏底下大声叫骂。是海宝家的。海宝家的很会骂人。跟骂着玩儿似的,她非常快乐地一直骂到牛栏外面伸着的那颗脑袋像乌龟一样缩进去了。可这女人并没有饶过老汉,她大声喊,老畜牲,你下来!
算起来海运爷还是海宝他叔,海运爷搬进这牛栏里来住,也就等于把自己屈降为畜牲了,海宝家的自然就可以不认他这个叔,连人都不是了,那还是啥叔?所以海宝家的就可以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老畜牲,你下来!老畜牲,你下来!!但老畜牲不但没有下来,反而爬到牛栏顶上去了。他抱着膝盖,坐在牛栏顶上的茅草里,摆出一副像骡子一样倔强的面孔,一动不动。渐渐的,他这样子就给人造成了这么一个印象,他不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背后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在操纵他,在暗暗地给他力量。要不,他一个孤老,怎么敢和海宝家的对抗?怎么敢和这么强大的一家人对抗?海运爷原来的样子大家都还记得,无论海宝,还是海宝家的说什么,老汉就会使劲地点头,点得脖子都发出了响声。那会儿海运爷可真听话,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像个乖孙子。搬进牛栏之前的海运爷和搬进牛栏之后的海运爷好像是两个人,反差实在太大了,让人接受不了,也难怪海宝家的一口一声地骂他老畜牲。
老畜牲往那茅草顶上一爬,海宝家的就更加开心了。她反复地给自己制造舆论,好让大伙儿都知道那真的是一个老畜牲。她又用她的骂,宣布自己准备采取更大的一个行动。老畜牲,你再不下来,老娘就一把火把这牛棚烧了!
老畜牲条件反射般地在屋脊上站了起来。老汉是个高个子,凭空往那屋脊上一站,脑袋就像顶着天了。这感觉,或许是大伙儿都站得太低了,一个老畜牲看上去才显得那么高。女人站得也低,可女人觉得是她的庄严宣告在老畜牲身上起了反应,女人就更加恬不知耻地露出胜利者的神气。
下来!她开始下命令了。
可老畜牲又坐下了,居然还叼上了一颗烟,划根火柴点亮后,然后吹灭了那点儿火苗。大伙儿于是又松了一口气,老汉没把那茅棚顶点燃,这老畜牲,实际上还有不顾一切地要活下去的念头啊。随之而来的平静又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了。海宝家的不见了,好像是去找火柴去了。牛栏下边的人都喊,海运爷,你下来啊,快下来啊!
老汉却无动于衷,好像这一切都同他毫不相干似的。如果那个妇人真的一把火把这个牛棚烧着,他可能也不会管。老汉慢吞吞地抽着烟,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他这样子,更加显出了一个孤老特有的孤独。
一阵风似的,那女人又来了,但手里并没拿着火柴,却捧来了满把的牛粪。老畜牲显然对这个结果有些猝不及防。他连躲闪一下也来不及,好大一片稀牛屎就飞溅而来,老汉伸手挡了一下,牛粪还是穿过手指溅了个满脸。大伙儿也就没点儿心理准备地一下子全乐了。一个壮烈的悲剧没有上演,就演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闹剧了。老汉再怎么板起脸装神圣,这满脸牛屎的,也装不出来了。老汉开始哭。老汉垮了,不再像个老汉了,像个受了委屈的娃儿了。
这哭声把始终深藏不露的海宝招来了。
海宝朝那在牛棚顶上干嚎的老汉叫了一声叔,叔,你怎么了?老汉于是哭得更加汹涌,哭声中散发出阵阵牛粪味。海宝似乎有点明白了,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堂客,你把咱叔怎么了?你打咱叔了?女人不敢吭声,变得谨慎起来。海宝看了她手上的牛屎,笑了笑。女人也笑了笑。海宝咣地就掴了女人一耳光。女人哭了。女人一哭,海运叔就不哭了,拿眼瞅着牛栏下边。牛栏下边已经闹成一团了,大伙儿都在作死的笑,那女人要往牛栏里冲,海宝又把她拉了回来,那女人就伸长了两只手,像桨一样划来划去,老畜牲啊,老畜牲啊,你死了谁来埋你啊?
海宝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胳膊一夹,就夹着那嚎着的女人走了。
火曜日那天早上,海运叔茫然地坐在牛栏门口,一把镢头横在屁股底下。猛然看去,觉得老汉一夜之间真是老多了。
海宝又来了,吭哧吭哧的扛来一袋白面。叔,热啊!海宝把那袋白面一卸下,浑身就像穿了孔似的到处漏水,汗流浃背。老汉像是没有听见,一双老眼仍就茫然地看着一个方向,那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麦地上空,一朵朵小白云在刚出来的太阳映照下闪闪发亮。
海宝一屁股坐在那袋白面上说,叔,你要想吃五保你就吃,你要不想吃我养着你,我给你老生养死葬,我只求你一件事,别住在这牛栏里了,你侄儿大小也是个村支书哩,你这是打我的脸哩。
老汉的目光可能望得太远了,一时还没有收回来。但老汉说出来的那句话却一股闷气地把海宝呛得脸色发白。
老汉说,我不吃五保,也不要你养。我有地,这地养我呢。
看着海宝忍气吞声地走了,海运爷也拄着镢头朝麦地里走去。他也不是存心要跟海宝作对,海宝虽不是他嫡嫡亲亲的侄儿,隔了多少代了,可也算他本家房下的后代,一笔难写两个海字呢。他一个孤老头子,也就这个亲人了。海宝待他也不薄,老汉原本有幢老房子,和海宝家壁挨壁,海宝拆老房建新房时,捎带把他的老房也扒了,把他的宅基地也占了,但不是白占,在那新建的房里也给了老汉一间,这就更像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却不在一张桌上吃饭,老汉还是单独开火,不单独开火不行,海宝家的人都年轻,牙口好,煮的饭就硬。老汉吃不了那么硬的东西,老汉每次看见那一家七八口围着一张桌子热热辣辣的吃着喝着,自己一个人坐在灶门口端着一碗饭,就觉得自己真的变成无依无靠的孤老了。
老汉名下还有块地,和海宝成了一家人之后,这一块地也成了一家的地了。这地夹在海宝的两个种草莓的大棚中间,海宝早就规划好了,要把这两个隔开的大棚弄成一个连成一片的大棚,地更大了,成本反倒节省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老汉没说什么。开春后,老汉像往年一样把那块地翻了翻。海宝家的警觉地问老汉想干什么,老汉说不想干什么,春天里,一边翻地一边晒太阳很舒服。老汉只管贪图着这份舒服,不知不觉又在地里胡乱撒了些麦籽。麦苗开始长得稀稀拉拉的,没谁把它们当回事,就像没谁把这个孤老当回事。等到一场春雨落过,麦苗都出齐了,绿油油地长成一片了,就没人不把这块地当回事了。
无论是块地,还是个人,被人当回事了,那感觉还真好。那长势喜人的麦子,是很容易激起一个老农的热情的,海运叔又变得浑身都是劲了。但海宝吃不住这劲了,叫他叔,问他想干什么。老汉是个不会撒谎的人,就说,我还想一个人过呢。海宝嘴里叼着纸烟,盯着老汉看了一阵,说,那你就吃五保,你这样老了,该吃五保了。海宝话里藏着的意思,老汉明白,只要他吃了五保,这地就要收回村里了,海宝当着村支书,把这块地划拉一下还不成了自己的,只认交税就是。可老汉突然变得固执了,老汉说,我既不吃五保也不要你养我,有地,这地养我呢。
海宝说,就算这地养得活你,你死了,总还得有个人来埋吧?
老汉果然就说不出话了,他的下唇在微微颤抖。海宝仍就死死地盯着他,那目光实在叫好汉难以忍受,好像他已经死了。
看见老汉发愣的神情,海宝又笑了笑,说,你可能都吃不上这茬麦子了啊!
海宝语重心长,拍拍屁股走了。
要说老汉也不像马上就要死的样子。老汉虽是七十岁的人了,不过身子还是很硬朗,往麦地里一站,硬朗得就像一把镢头。老汉住在海宝家的大瓦房里,总觉得四肢乏力。老汉搬进牛栏里后,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像是跟谁较上劲儿,也不是跟海宝,好像是跟死神较上劲了。
老汉寻思着该给麦子间间苗了,可他往麦地里一蹲,一棵也舍不得间掉,此时麦子还长得像茂草一样,青勃勃的,每一片叶子都在他鼻子底下呼吸,闻起来也是青勃勃的。老汉猛地把手里的镢头攥紧了,猛地刨了一镢头,眼泪就流下来了。但那把镢头却义无反顾,每刨一下,就有一种声音在麦地深处回响。被连根刨起来的麦苗,从镢头簌簌地掉下来,那断了的根茎上渗出一滴滴绿色的液体,那是麦子的眼泪啊,那是麦子的血啊。老汉突然有点害怕了,脑子里响起一片混乱而绝望的呼喊声,救命啊,救命啊。
老汉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犯罪感觉紧紧抓住了。他用土堆了个坟一样的小墩儿,本来想把那些刨掉的麦苗给埋了,可那么多,多得埋不下。老汉自个儿躺下了,把那小土墩儿当了枕头。他使劲地嗅着这从地底下刚翻出来的新鲜泥土味儿。他知道这是他不久就要闻到的味儿。
只在此时,老汉才真的感到自己离死不远了。
这天中午,一辆驴车从镇上拉来了一口大棺材,在海宝家高大的瓦楼前停下了。
海宝家的从屋里走出来一看,就傻眼了,你这个老畜牲,你这个老畜牲到底想要干啥?海运爷站在棺材旁边,把头上那顶晒得已经开裂的破草帽摘下来扇着风。
海运爷说,你叫我侄子出来,帮我把这棺材搬进去,我回来了,我是这家里人呢。
海宝出来了,忙不迭地给赶驴的、看热闹的递烟。海宝又绕着那棺材看了看,不是白材,黑漆漆的已经刷过了,这个孤老,他可是给自己办来了全村子最大的一口棺材。海宝说,好!好棺材。海宝又说,好!好兆头,棺材棺材,升官发材啊,叔,你可真是处处为你侄子作想。劳驾了,各位乡党,帮我把这棺材抬进屋吧。
大伙儿正要动手,海运爷说,慢,让我先躺进去试一试。
这倒是件挺好玩的事。众人便把那棺材盖揭开了。海运爷爬进去,躺好了,还用手把那几根稀疏的山羊胡子理了理,白花花的胡子荡来荡去,扫在他的两腮上。这使他看上去有那么一股玩皮劲儿。他笑了。
海宝!海运爷叫。
海宝唉地答应了。海运爷说,我的房被你扒了,宅基地给你占了,那块地里的麦子我自己也给刨了,那地也给你吧。你想要的我都给你。现在当着全村的老少爷们我要问问你,我这断子绝孙的老畜牲,死了谁埋?
海宝也突然有点儿害怕了。海宝忽然也觉得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犯罪感觉紧紧抓住了。海宝颤声说,叔,我,我埋。
海运叔摇了摇头,说,我那侄媳妇呢?她干啥?
海宝说,她给你老下跪,给你披麻戴孝。
海运爷摇了摇头,表示他不相信。
海宝说,我让她现在就给你跪下!
海宝转过身对堂客说,你跪下!
女人是骄横惯了的,让她当着这一村的老少爷们给一个孤老下跪,她可放不下架子。海宝便摁住女人的脑袋,使劲踢她的膝弯。女人跪下了。大伙儿看了那跪下的女人都吓了一跳,女人一声不吭地跪在那里,像一块石头。谁也没见过女人这副样子,大家都觉得老汉有些过分了。可老汉还不肯饶过女人,老汉说,让她哭,她是我侄媳妇呢,我死了她怎么不哭?
海宝又踢了女人一脚,喊,叔让你哭呢,你哭啊!
这一下可能踢得很疼,女人哇地一声哭了,她是真的在哭,有眼泪顺着她蓬乱的鬓角流下来,在她满脸灶灰的脸上流出两道清晰的痕迹。女人刚才还在做饭呢,女人跪在这里那锅灶就没人管了,一锅的饭菜开始散发出焦糊的臭味,大伙儿都闻到了。
老少爷们把棺材抬进海宝家里,又抬进了海运爷原来住的那间房里,就散去了。事情发展到这个样子,大伙儿都感到有点扫兴。海运爷也有些沮丧,坐在自己的房门坎上,看着海宝,海宝正用斧头劈老汉睡过的床。海宝把床劈成了柴拌,抱进灶房里,捎带着又端来了一碗饭,黑乎乎的像一碗堆得冒尖的牛屎。
海宝说,叔,你吃饭。
老汉的手抖得拿筷子都拿不稳了。
海宝说,叔,我喂把你吃。
老汉把嘴紧紧地闭着,他看清了,那碗里真的是装的牛屎。海宝用筷子去捅他的嘴,老汉就用牙齿更紧地咬着嘴唇。海宝把一条腿跪下了,海宝说,一村的老少爷们刚才都看在眼里呢,你侄子可是最孝顺你老人家了,吃吧,吃吧。
整整一个下午没看见老汉出来。老汉出来时眼里已开始闪烁黄昏将尽时的光亮。那个牛栏已经拆了,夕阳映红了牛栏里边从来没被太阳照过的一小块土地,老汉走来时,那堆烂茅草里一群觅食的麻雀一哄飞走了。老汉在草里拨了拨,拨出了那面铜锣,还有一只鼓棰。老汉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像平日里一样拎着铜锣挨家挨户的打过去。他看上去走得很慢,其实很快,不一会就穿过了村里那条狭长的街筒子,又看得见那片麦地了。他伸着头向那块麦地瞅了瞅,就走过去了。
那些被刨掉的麦苗经了一天烈日的曝晒,晒得焦黄干枯了,干枯地闪烁着某种生命干枯后的色泽。老汉慢慢地看,慢慢地笑,然后坐下了,一阵风吹来,差点吹掉了他头上的草帽,老汉伸手捂住了。他点上一颗烟,抽了一口,左右看了看,左右就是海宝家的那两个大棚,被落日的余晖映得一派红光。西天边上燃起一片好大的火烧云。火曜日呵!老汉在心里莫名地叹息一声,用一只手撑着地爬起来。他要回家了,回海宝家。除了海宝家,他连个牛栏都没得住了。
老汉无意扔下的那个烟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冒火了,那些干枯的麦苗都烧了起来,迅速地向两边的大棚烧去。老汉感到背上热腾腾的,但他没有回头,他以为是那片火烧云照在自己的背上,才会这么热。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哪!海运爷一锣棰击下去,走得更快了。
老汉感到没使一点劲儿,是两只脚自己在走。
上一篇:爱牙日,请跟你的牙齿谈一谈吧 下一篇:Protective effect of exogenous IGF—I on 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