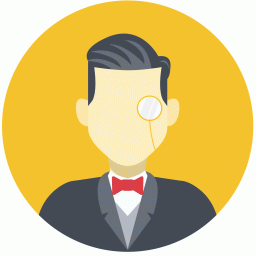论规范权力运行的法治杠杆
时间:2022-10-25 10:08:23

摘要:法治在规范权力运行中具有撬动社会格局、平衡利益关系的杠杆作用,杠杆的支点是民治理念和民治能力,杠杆的力矩是国家与社会治域调整的现实空间。在将权力这一重器纳入良性运行轨道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发挥的程度取决于从治民到民治、从国家到社会两大治理模式重构的发展情况。民治理念的树立,民治能力的提升,国家与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为通过法治建设撬动表层利益格局的同时撬动深层传统理念,从而为平衡权力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法治杠杆;权力运行;规则意识;社会组织;社会稳定;过程控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4-0032-05
一、绪论:法治建设的杠杆作用
“考察古今权力现象和权力界说,权力实际是一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资源。”[1]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是要规范权力的运行,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既要搭建笼子,也要调整不稳定的社会结构,遏制改革扭曲机制的形成,同时撬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培育新生的社会力量。法治建设正是整合权力、权利、道德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2],完成这一使命的历史性杠杆。
目前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矛盾冲突是发展中的利益矛盾冲突。“好的制度是能够容忍矛盾、容忍冲突的制度。”[3]而共识的形成、利益的调处需要法治建设这一杠杆总效用的发挥。
培育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空间是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在现有格局下,只有通过法治对权力的约束,才能使其不致膨胀而占有全部资源,戕害稚嫩的社会组织生长,挤压其宝贵的成长空间;只有通过法治建设和法治意识的培养,才能区分国家与社会,在价值层面回归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人的联合体”①。若使社会由不稳定的洋葱型转向稳定的橄榄型,必须疏通社会的阶层流动渠道,唯有通过法治方式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弱势群体。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方式,目前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大障碍是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未来必须在增加供给方面有所突破。
法治建设是建立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恢复社会秩序理性平衡的有效方式。
矛盾既是事物发展的必要动力,也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根本。[4]调处矛盾,促进公平正义是司法的追求,而社会矛盾调控体系和矛盾排解渠道的构筑需要实现公平、效率统一,风险责任合理分配;根据社会冲突理论,“法律所能化解的社会冲突是有限的,同时,一定限度内社会冲突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法律化解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法律疏导机制与法治国家的建立。”[5]
社会学学者孙立平认为,需要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再建立一个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包括“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机制。”[6]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国家这一杠杆若要发挥作用,还需要坚强的支点、合理的力臂以及动力和阻力的平衡。
二、规范权力运行的支点:从治民到民治
法律化解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法律疏导机制与法治国家的建立,从力学角度讲,杠杆若要发挥作用,首先要选好支点,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
(一)民治的能力建设:意识培养与组织培育
“美国19世纪法典化运动的倡导者菲尔德曾经认为,只要有十分通俗和简明、能够被人民阅读和理解的法典,人们对法律就可能认同甚至信仰。但是,美国其他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7]法律的认同或信仰需要经年累月的教育与实践,法治意识只有融入生活,才能融入大脑。
规则意识是与法治这种生活方式相伴而生的,是可以通过教育后天培养的,更是且只能通过不断的实践和传承固定下来的。因此,当代中国转型期的实践往往使各种信仰走向多元,许多行为开始失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造成了不尊法、不信法、不守法的恶性循环。同时决策者以及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等法律共同体的法律意识不足、率先违法,特权盛行、潜规则大行其道,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从城市中的交通状况就可见一斑。然而,辩证地看待规则意识的缺失,正如看待历史转型时期的“礼崩乐坏”,其意识的缺失正意味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根据张伟仁先生的研究,我国历史上并非涉及个人权利的民事法律制度缺失,而是通过礼的形式广泛而精确地调整着社会的运行,就此观之,中国社会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恢复规则意识。同时通过经济生活不断实践现代法治理念,通过法学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寄希望于未来。“与单纯的法制教育不同,法治教育不是教育民众盲目、被动地服从法律,也非使其知晓法律内容,而是教育其如何尊重法的权威,运用法律捍卫自身权利,主动参与法律监督,抵制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8]
同时,作为民治基础的社会组织正悄然发展。尽管当前社会组织与团体基本依附政府和权力而存在,但随着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政府的简政放权和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成为必须。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经登记的社会团体25.3万多个。2012年1月1日起,广州市各种行业协会、异地商会以及公益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类、文化类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这一举措到2012年7月1日起将扩大到广东全省。这一过程同中国的法治发展一样,将是长期的,但是不可逆的[9]。在汶川抗震救灾等各种突发事件中社会组织已发挥积极作用。
(二)民治的现实基础:法律运行的法治化
除了自律,改变权力拥有者自我分配权力的条块治理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抑制其政绩冲动,对部委而言抑制部门权力扩张,对个人而言避免公权私用,暂时都未有有效的制衡模式,在现有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唤醒宪法施行、引入民众参与,中立监督和立法、司法权力制衡都是未来的可能路径。
法律运行的法治化核心是通过法律实现控权,现实中如何才能做到,通过笔者实证研究发现可以从公开、程序和公众参与三种方法入手。
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实施以来,开启了通过依法公开方式约束权力运行的方式。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主动公开“三公”经费、财政预算,为落实条例、实现政务公开迈出了重要一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
施行立法决策、行政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是法治理念中程序正义的体现。不少地方除地方性法规采用严格程序和事先审查外,在重大行政决策方面也公布了规定:例如2005年至今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积极探索,制定了为数可观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范性文件。据统计,截至2011年9月,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立法规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共有9个,占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29%。市级市主要有:丹东市、西安市、杭州市、苏州市、东莞市、滁州市、濮阳市、徐州市、广州市等。县级市主要有:四川省长宁县、北京市延庆县、浙江省宁海县、吉林省抚松县、江西省兴国县等。可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建设已越来越多地得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重视,相关的立法与规范性文件还在陆续出台,与之配套的具体执行措施也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之中。整体看来,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已经初具规模,涵盖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绝大部分环节。
扩大公众参与,公权力部门开始采用法律法规公开征求意见,采取听证会、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多种形式。近年来,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推进下,公众参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进步。2013年11月底,国务院法制办首次公告面向社会征集立法项目建议②。
然而,以上三种方式带有明显的权力自律性质,不足以实现长期的有效控制,在现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现实背景下,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笔者认为若要真正平衡权力,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公权力的分权让利机制;二是民众的有效监督机制;三是社会的觉醒。
公权力的分权让利,是建立在改革者准确的制度设计和民间组织力量壮大,国家与社会充分博弈基础上的。民众的有效监督机制包括现有制度架构下的委托监督,即通过各级人大和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各自在自身权限范围内依法监督,也包括建构通过网络媒体和舆论直接有序的监督机制。社会的觉醒是社会成长的有效动力,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代中国社会已现萌芽。
以上所有机制,需要将法律内化为信仰,从外部硬约束提升为内部软约束。法的秩序、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只有内化为信仰才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不因权力的膨胀而变化,不因少数人的好恶而转变。而信仰的内核要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完成根本上的重构:将驾驭民众的王权人治文化、官本位权力信仰转化为为民所驾驭的现代法治文化、人本位的权利义务信仰。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英籍德裔学者达伦多夫曾说:“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六个月,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六年,而民众心灵和思想的革命则需要六十年”。[10]内化的过程不但是长期的,而且必须同自身的道德追求和民族文化找到契合点。现实中各行各业近年来出现的诚信缺失,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定位出现了问题,也是道德底线崩溃和信仰缺失的结果。这就需要利用更长的时间重塑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真正现代化。如何在利用法治国家建设撬动表层利益格局的同时撬动深层传统理念更为关键。也只有这一目标实现后,在中华文化土壤中才能生长出法治的文化支点,衍生出道德支点,再外化为支点,民治的支点才是长久的、有生命的。
(三)规范权力运行的理论和现实分析:以“维稳”为例
规范权力运行,有助于决策者和全体民众客观地看待社会问题与矛盾,政府依法行政。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是可以统一并应当统一起来的。心态的焦虑往往带来思维的僵化,而权力的失范会助长僵化思维带来的危害。因此,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新思维。“强调危机的威胁有积极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决某些问题;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导致政府‘过分反应’——不必要的控制,同时用‘维持稳定’挤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11]
规范权力运行,避免“泛政治化”。周旺生教授曾指出,现代法治的发展需要实现党政法三者的分离,三者分离可以清晰地实现政治和社会治域的分野。[12]应把矛盾冲突还原为失业、下岗、拆迁等与百姓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不应意识形态化。权力被依赖,解决了短期问题,难以化解形成长效机制,同时给权力膨胀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形成恶性循环。
规范权力运行,提供政府自律依据。“有效约束政府权力,促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加强政府与民众基于共同法律基础之上的沟通与互信,是有效防止、化解各类发生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13]
权力规范运行,有助于创新能力的迸发。规范权力,必然要打破其对市场的扭曲,冲破垄断,释放创新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改变有创新需求者无创新能力,有创新能力者又无创新需求的尴尬现状。权力规范后,垄断逐渐打破,创新需求得到满足,产业升级、就业问题这一影响国家安定的民生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才是形成良性循环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方式。
综上,社会稳定的前提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核心是民众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目前维稳成本的攀升正是权力膨胀和民众制约权力机制不完善的表现。
三、规范权力运行的力臂:从国家到社会③
有了权力规范运行的支点还需要选好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杠杆撬动社会建设表层利益格局和深层文化格局的力臂,在阻力大于动力的阶段,要保证放大动力,显然需要调整支点的位置,保证动力臂大于阻力臂。从撬动权力的角度观察,动力臂是社会,阻力臂是国家。
(一)国家权力治理模式的重构
国家权力治理模式的重构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宏观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微观层面的治理技术调整。邓小平同志曾言:“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4]
宏观层面的改革面临的更多是思想观念和决心勇气的障碍。认为权力重构是一种国家自毁根基的做法,是狭隘的。前苏联“恰恰是由于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旧政治体制,长期窒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到发现了病根时已病入膏肓,再搞政治体制改革为时已晚,何况其政治体制改革方向不对头,导致灾难,而不是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5]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家治理的技术层面由全能计划逐步转化为宏观调控,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将社会治理模式由国家刚性调节逐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和社会的有机组合,使运行机制由简单脆弱而柔韧坚强。继续推进治理方式调整,应着重以下两点。
首先,变末端治理为程序治理,适处罚,重预防。末端治理是环境工程学上的概念,是指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针对产生的污染物开发并实施有效的治理技术。本文中笔者借指现实中国家对社会问题出现后采取的在最终阶段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具有成本高、投入大,且治标不治本的弊端;应当借鉴过程控制这一治理模式,将危机处置关口前移,以预防为主。这就要求权力运行科学化、常态化,在各个程序阶段有程序可循,依法治理,防患于未然。将各种法律责任的惩治与处罚方式科学匹配,即综合考虑处罚程度和可追溯概率,严格避免选择性执法,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
其次,变严防死守为依规运行,轻管制,重法治。当下社会治理模式中注重管理甚至控制,一方面由于过去计划经济和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习惯,另一方面由于管制过程中的利益获得机制,不习惯也不愿意采用新的治理模式。但经济的发展、国内外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昭示:依规运行、重视法治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全体国民长远福祉所在。现代技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等科学方式,完全可以做到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最佳治理效果。
(二)社会力量的成长:个人与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常常把“市民社会”称为“经济国家”,就是由于它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领域或“需要的体系”。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范畴,是“公民社会”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或者说经济国家与政治国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16]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认识到,随着社会的二元对立,“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约束自己”[17]“所以,需要尽快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多元治理结构”[18],社会力量的成长和权力的规范相辅相成。
社会力量的成长,源于其构成要素即人的成长和转型,以人为本,人的转型,包括传统人向现代人,计划人向市场人,单位人向社会人,市民向公民,民族人向世界人的转变。人结合在各自的生产圈和生活圈中,各个圈结合成社会。现实中各行各业近年来出现的诚信缺失,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定位出现了问题。计划人向市场人的过渡中,忘记了自身的社会人身份,缺失了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形成社会在成熟前一定程度的溃败。
(三)国家权力陷缩与社会权力的扩张:从包揽到共治
国家和社会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更多的是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的并行共治关系。
当下,我国的社会权力非常弱小,国家权力异常强大,但随着社会组织的成长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一力量对比势必发生变化。
社会权力主体,广义而言,包括全民——社会权力的最高主体;政党——社会权力的强势主体;政协——具有宪法权威地位的社会权力主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权力的潜在支柱;媒体——社会权力的“无冕之王”;非政府组织——社会权力的核心主体;宗教团体——精神权力的主宰;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社会势力和其他社会权力主体。[19]这些主体将逐渐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分离出来,部分从市民社会成长起来,通过道德、宗教、法律运作机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同国家权力形成共治。
(四)从国家到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尽管经历了朝代更替、自然灾害、战争、革命等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华文明,这一源远流长的古文明依然在社会层面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呼吸着;无论好坏,当代中国社会都无法割断自身的历史血脉。庙会、祠堂、乡绅分别代表着中国社会祭天、敬祖和现实权威文化,也是三重社会权威的来源,是自然经济生发而成的社会体制,直至今天依然是民族潜意识和中国社会的基因。
中国社会具有相当强的弹性,弹性一方面来源于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另一方面源于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
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民间交流日益广泛深入。中国社会由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参与。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生活消费和理念创造。相应带来两个转变:学会从国际社会成员的视角观察与思考,视野更宽广,例如印尼海啸、日本地震等国际援助中民间机构和组织的自发动员;学会利用全球资源,履行国际义务。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失业率攀高;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在经济社会关系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社会,无论是外贸企业还是旅游者都身在其中,参与全球治理是实实在在的要求。
四、结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理性的选择,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选择是撬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畅通阶层流动④和建立公正有效的矛盾调处机制,从而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杠杆。
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支点,以理顺治理关系为力臂,发挥由社会觉醒和对外开放的正向压力转化而来的动力,克服既得利益集团和历史文化中人治因素的阻力;以利益关系调整撬动利益格局变动,用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平正义,是解决发展后问题,消除成长中烦恼,巩固发展成果、推动科学发展、实现改革目标的基本思路和有效方法。同时,这一杠杆机制若要发挥作用,必然要打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完成历史文化的扬弃与重构,同时需要社会力量的孕育与壮大,国内外环境的支持与包容。
注释:
①“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http:///article/xwzx/tpxw/201311/20131100393833.shtml,最后登录时间2013年11月30日。
③周旺生教授多次讲座中提出从国家到社会这一未来法治的发展方向的内容。
④2013年3月17日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注意完善社会阶层纵向流动机制。
参考文献:
[1]周旺生.论作为支配性力量的权力资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87.
[2]后向东.权力制约机制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11.
[3][6][11]孙立平.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J].学习月刊,2011,(4上).
[4]赵鑫.论社会转型中的法治[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5]吕明.法律如何维稳——基于社会冲突理论的考察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1,(6).
[7]周光权.公众认同、诱导观念与确立忠诚[J].法学研究,1998,(3).
[8]刘军宁.共和 民主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9]朱力宇.论当代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可逆转性[A].转型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C].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71.
[10]Vojtech Cept,The Transformation of Hearts and Minds in Eastern Europe,Cato Journal,1997,(2):229-230.
[12]周旺生.中国立法五十年[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5):1-23.
[13]封丽霞.法治视角下的社会稳定[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4).
[14]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EB/OL].http:///mzh/jng/dxp/zzxz/,2012-05-26.
[15]郭道晖.建立法治国家必须推进政制与法制改革[J].法商研究,1999,(2).
[16]吕世伦,郑国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从身份到契约”公式引发的思考[A].刘海年,李步云,李林.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10.
[1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4.
[18]孙立平.“收入倍增”莫成“支出倍增”[J].社会科学报,2011,(1下).
[19]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M].中国香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