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乐的时光(外三首)
时间:2022-10-23 11:5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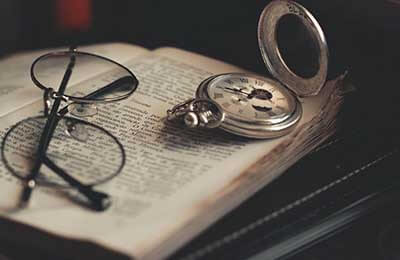
常有人问我,你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面对如此简单直白的话题,我竟傻愣无语,恍惚茫然得不知所以。
我问自己:你快乐过吗?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时光吗?那所谓的快乐时光在岁月流程中能一直被你铭心刻骨地珍记着吗?答案永远都那么不确定,因为对于我这个此一刻总要为下一刻担心的人来说,是没法留住并享用那最快乐的时光的。
近读一篇散文,很惊叹这位我并不熟悉的作家的颖悟力,她说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时刻,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可她在当时就知道,那是自己最好的时光。当时就知道,这真太了得,这说明她对她自己有着清醒和认识和把握,这些文字是如此地打动着我,如此让我认真回检过往时光中的记忆……
被许多人怀念的美好童年,对我却是模糊的。贫穷偏远的大深山里没有书读,没有风筝,更没有音乐,在我能够记起的几件事中,全都和快乐的时光不沾边儿。仿佛我对一些事物还没有多少意识,它们就过去了。想来,第一次吃糖,过年时穿上母亲给做的新鞋,在春天的原野里看到第一朵花开,听见第一声鸟鸣,金秋品尝第一只苹果,双手托起冬日洁白纷扬的飞雪,把自编的承载着自己太多梦幻的小小草叶船放上河面……那应该都是非常快乐的,可惜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而没有任何印象的想像中的快乐是不属于我的。
及至慢慢能够清晰地回望自己的每一段时光,我这才很惊异地发现,快乐于我从来都是擦肩而过,稍纵即逝,或者根本就没有真正停留过,而更多的时候我却是沉陷在对快乐到来的焦盼等待和因快乐转瞬不再的失落、无着和忧伤。
看来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我明白,不是没有快乐,而是我不敢正视它,不敢享受它,我给它涂上了一层悲观主义色彩,我忽视了快乐本身,而只注视着快乐之后的悲伤。
明明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可我却无论是和朋友、熟人、老乡在一起,还是外出开会与大家相聚,从未能做到尽情享受那即时即刻的快乐时光,而心里老为之担忧的则是这种幸福和快乐正在分分秒秒残酷无情地流逝,任谁也挽留不住,要不了多会儿就得散场,热闹重新回归清冷,大家又得各奔东西,回到既定的生活中去。心里汪着这浓重的叹息、空落与哀伤,怎么会能够快乐呢?
平日看戏、看电影、电视抑或看书,因内心里老想着每一个场景、每一幅画面以及掀过去的每一书页,都意味着离剧终又近了一步,那心思便被很快就要来临的结局纠缠得一点好情绪也没有,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快乐可言!有些时候,我会放弃正看了个开头的电视剧,会搁置起已读了差不多一半的书,甚至会故意不去打开一幅收到很长时间的画儿,我无疑是在和自己较劲儿,但这种人为的强制性的拒绝结果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往往因自欺反倒令自己在焦躁不安中有一种怒火攻心的恼恨,那是近乎本能的悲伤和丧气。
终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出并发表了,这原本是我渴盼已久的事情,更是我多年的心愿,现在它实现了,还被同道们认可,这对于把文学爱到骨髓的我来说,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让人高兴和快乐的呢?可是,也仅仅只是刹那间很短暂的欢快而已,接踵而至的却是无边的迷茫和恐惧,下一部作品应如何写、写什么,怎样写才可以不比这部差得太多?那种空茫和迷失,一如一个好容易攀上一座小山头的人,目的地的到达同时也是失却,极目四望,独立虚空,忽然不知往下的路该怎样去走。
一趟精心设计的旅游,从起程之日开始,满心里涌动的不是旅途中所见所闻给自己带来的新鲜、兴奋与快乐,不是置身在其中的陶然忘情,而是时时被强烈的、总也放不下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消失感痛苦地折磨着。风光虽旖旎,景色惹人醉,然而却是在无情地逼向本次旅程的终点,这是没有谁能够改变得了的。怀着这样痛失的心情,只能暗叹好景不长,似乎那迅速流失的一天天是被自己的叹惋给数点掉的。陷入惊恐不安中的一颗心,怎么可能会真正愉悦得起来呢?
哪怕是刚刚买来的自己喜欢的一套衣服,一件与众不同的工艺品,一盆盛开得正热闹的花,满天燃烧的霞光……我都不能做到很好地享受当下,让自己幸福地去充分领略最快乐的时光,而是永远为它们那即将的破旧、破碎、破败担心,叹息美好的一去不复返,在这样诚惶诚恐的忧虑中,一颗灰郁的心也就绝不可能会感受到来自生命内部的种种快乐。
同事多次劝我:这种心态得调整、改变,要强化自己的快乐意识,最起码也要想方设法放大、延长那些最快乐的时光。收回你的担心,因为那种这一刻为下一刻的担心、害怕、惊恐除了徒增烦恼外,别的统统没有用,无论是对什么样的人,所有那些无比珍贵的最快乐的时光都只可纪念而不能留住,既如此,还做那种傻事干吗?何不这刻不管下刻事,得欢乐处且欢乐呢?
这话我还真就听进去了,是啊,自己这是何苦呢,倘若一直为彼时担忧而过不好此时,不但与事无补,改变不了客观存在,还自伤自毁不可救药!为什么要像那位愚人一样,面对一框桃子每回都要留下好的而吃那个不好的呢?聪明人却恰恰相反,每次都拣最好的那个吃,他自然就一直处在快乐满足中了。同样一件事情,所想不同,做法各异,当然也就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境啊!
然而,真正做起来,我果然能如同事所希望的那样吗?能吗?我听不清那自信满满的声音,也明白习惯是多么可怕,因为对我来说,那凝固着宿命和悲情的日子毕竟太深太久了,我一下子根本不可能走出来,这需要一点点去做艰苦的努力,我要让自己坚定地相信,正因为欢乐和痛苦都是要去的,才要顺乎自然,在最快乐的时光享受快乐,使快乐最大化。
那么,还是给自己以时间,力争尽快从永无了时的忧思、担心、惊惧中走出来吧,抓住快乐本身,享受它,待它消失之后再追求另一个快乐。即如已经逝去的快乐也仍可给你回忆中的甘美,即使它的消失本身,它给你带来的淡淡的忧伤和哀愁也应该是快乐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完成这种心态的转变。
其实她从未放弃
县里一位和她相熟的朋友告诉我,半年前,她已留职停薪离开家乡那所中学到西南一高校读研了。好像专业是古典文学,但具体是哪个方面的却不大清楚。还说,她这次走的动静比较大,是全家开拔!那个家在外地和她大学同窗的他,为了她毅然在婚前就放弃一份不错的工作,应聘到她所在的那个学校执教,这次,他又为了她,为了他们的爱,再到能与她朝夕相伴的远方去应聘。自然,他们那八岁的女儿也一起同行,重择新校入读了。可以说,她丈夫,他们这个家完全是围着她在转呢。
我听了,既惊喜,又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早年她拿给我看的第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我是一条天河里的鱼……听听,够厉害的吧?那是怎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孤绝和高贵啊!我那时就想,这条鱼不仅会在水里依其心性不停地畅游,还会笑得水草弯腰,碰见或碰不见另一条鱼,都将决然上岸,说一些和岁月有关的话语。以致当我默念着“让我们到月亮里开花吧”的诗句时,就会倏然想起她,想她做为一条鱼上岸后就是为了要到月亮里去开花这件事情。
与她相识在一次她所在那个县举办的文学笔会上。当有关人员把她介绍给我时,我竟被她那两道炯硬的目光照得心里一凛一凛的!那是我在女性中从未见到过的探照灯般的目光,那目光把事物看得很狠,很毒,让人有一种被洞穿被挖空的恐惧。我不喜欢这样的目光,这样的目光不应属于女性,就是男性也最好不要!因而,我对她的印象并不怎么样,内心里充满着天然的排斥和戒备。
乡村的夜墨黑墨黑的,虽是初秋,却已寒凉。那晚我们住在乡下的农家,会务主任安排她和我同屋。细雨冷风的夜,我们睡不着,便围坐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昏黄的灯光下,她的目光仍不肯软散下来,就那样直直地穿越我,我时时需低了头,避开她的目光,或眼睛尽量望着别处和她说话,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我便有些得意地暗下偷乐,白天在一条小河边,她提出与我合影,我虽然答应了,却在快门按下的刹那转了一个侧面,想想倒是挺开心的,谁让是她呢?
闲扯中,让我记得最清的是,她说有一回,她周末骑车子行走在回家的小路上,迎面遇到一位也骑自行车的女性,路很窄,那女子不肯让路,她见此更是坚决不让,结果她加快速度不顾一切向前骑,那女子连人带车被她给逼掉到路边几丈高的麦田里。看她说起来眉飞色舞得意洋洋的样子,我心里极不舒服,尽管她再三强调人和车子都没伤损,但何必如此恶作剧呢?一个堂堂的为人师表的女教师怎么可以这样?再就是她说她认真考虑过了,自己一定得不惜一切牢牢抓住那个现在的她的先生,不然,在这么个山城小镇中学,她的终身大事就会成为永远的难题,她可耽误不起!她已把他“挖”过来了,目下,正在办理有关手续,不日,他就也到她工作的那个学校上班了。能耐还真不小呢!我说不清自己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情。
外面风声雨声,室内温暖宁静,这样的时候本该把茶吟诗很有情调,可和她在一起我却倍觉乏味,什么话也不想说,了无情趣。想看书,屋里光线太暗,正百无聊赖着,忽然从墙角的一个旧竹筐子里跳出一只老鼠,我和她旋即起身,呼叫着用木棍来回追捕,好一阵闹腾,最终还是她把那只老鼠打死了。
你真行,手疾眼快打得准,我都快给吓死了。望着那一团血中微微抽动的死鼠,我真心称赞她。
还不都是为了你我才这么做的,其实,我胆子很小,平日见一只小青虫都害怕得不行呢。这话有点虚,我听来显然有些过,我不相信真就是这样,能射出如此两道目光的她,难道还畏惧一只老鼠不成?
后来,会议结束那天,等她将自己那两本抄写得十分干净整齐的文稿交我带回来“指教”时,我不觉大为惊异,没想到她的诗和小说都写得那么不俗,那么有想法,这真的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默然盯着她看了许久,许久之后才问:这么够水平的稿子,为什么不寄给报刊发表呢?
发表很重要吗?在我看来,不断思考经常写着才更有意义!她说,以前,她也曾狂热地追求过一阵子发稿率,但随着一些作品被刊发,她却慢慢安静下来了,相对于文坛的喧嚷热闹,她更愿意在教书之余,坐下来静静地思索,静静地写作。对于她,文学从来都不是手段,而是真正的心灵家园。她执信,世间有那么一部分人就是为文学而生的,但她却不是,她既不想为文学而活着,每天都不与外界接触,生活在诗和小说里,专心、孤绝、闭关式地写作;也从不边缘、弱化文学,把文学骂得一钱不值,讥嘲文学在当下的尴尬、无奈和微弱。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却也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只要有人类存在,文学就绝不会死亡、消逝,因为人们的心灵永远需要抚慰!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读到过她的任何作品,但我坚信她依然在写着,肯定不会停下笔来,她选择了一种很好的爱的方式,爱便持久!
上帝生气了/后果很严重/让我们安静下来吧/听一听/一朵花在绽放时/是如何/喊出它自己的名字……果然,朋友从邮箱里传过来她的一首诗,依然有那种卓异的意味,我相当喜欢。
这次,她能够被学校定为享受全额助学金的优秀学子,完全是她那些未发表过的作品起了大作用。听说,她把它们刻在光盘上,特意送给那所高校的校长,校长是中文博士,看了那些作品自然就特事特批,把最优厚的待遇给了她。
没能时常读到她的作品,也许我会有些失望,却也会不断希望。我知道,其实她从未放弃过文学,她笔下的那些文字,自然恬淡,和谁都不争,只悄然让一朵朵静美的花开满春天,开满时间。
一生的交付
这是五月的一个夜晚,这个原本与以往没有任何不同的夜晚,却因了来自台湾的八十七岁著名摄影师吴绍同先生的一场精彩摄影专题讲座而充满着永远的意义。
鹤发童颜,清俊文雅,平易温和,他的讲解那么纯粹,干净,言简意赅,引人深思。无数双渴望的眼睛如沐甘霖,有一种东西在欢快地涌动,泛滥,生长,令人感觉温暖而深入。
他从事摄影创作七十四年,曾两度夺得电影最佳纪录片金马奖。六十五岁退休后,他最初打算以五十六个民族为主题进行拍摄,但因很难拍到原汁原味的习俗而不得不放弃;后又改拍和我国相邻的那些国家的边地风情,不料实地拍摄起来更为困难,几乎无法进行;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东北他经人带领见到了一群野生鹤,竟一见钟情,爱不能禁,此后十七年,他背负十五公斤重的摄影器材,走遍五大洲,持之以恒,倾力投入摄鹤。至今,真正把世界上十四个国家所有的十五种鹤的全部鹤种在原生地拍遍的摄影家,仅有瑞典摄影家托朗尼文、德国摄影家阿布雷、中国台湾摄影家吴绍同三人。这位中国摄鹤第一人的吴先生,由于在漫长艰辛的孤旅中,他的身体几次摔伤,眼睛出血,视力骤降至不到0.1,无奈,他只得中止摄鹤,拍了六年骆驼,接下来不得不再改换主题,只有找比骆驼更大、又能追得上的恐龙了。
望着屏幕上吴先生展示的一幅幅鹤类作品,我深知每一幅作品都凝结着他非同寻常的心血和汗水,他艰苦卓绝的持久努力!中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印度、加拿大、南非、北极圈内荒无人迹的西伯利亚……不同国度原生地的不同种类的鹤,都被他一一定格在某个瞬间的时间的节点上,成为永恒的艺术品!许多时候我很恍惚,分不清那画面中的生命究竟是他还是鹤,我自己是在时间之中还是在时间之外,连他自己也笑言:人们都说我鹤头鹤脑,整个的样子也有些像鹤呢!
他已忘我,已深入到鹤的内部,是真正的鹤魂!他说他从不喜欢给照片起名字,希望能留下一些空间,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把“大将军”这个名字给了那只站在树林旁威武远眺、高达1.65米的印度红颈鹤,因为鹤们对树林都有点害怕,独这只鹤胸藏丘壑、气势磅礴、无所畏惧的样子让他特别喜欢。
他尊重鹤的生活习性,始终以平等关爱体量之心与鹤亲密相处。常年的观察中,他知道鹤都非常喜欢清幽,洁净,一天最少要有两三次来整理自己的羽毛。这种时候,无论内心多么急切,他都会安静地等待,等待它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拍摄。为拍一张小雏鹤出蛋壳的照片,他独行荒原,住伪装帐篷,花费三万美金。有次,为拍一张自己想要的仙鹤图片,他在沼泽地里蹲守了二十多天。那苦那累那艰辛让人难以想像!由此,他对鹤也有了更为深度的了解,鹤每一窝都是两个蛋,而且也一定每次要孵两个蛋,若有一个被人拿走或不慎损坏,它就会再生下一个,什么时候都是两个一起孵。
他摄鹤始终都有自己明确的想法和追求,无论是构图、光线、技巧、画面意境、语言,还是内在的承载和蕴含,无一不透射出他独特的思考和领悟,甚至在数量上也可看出他的用心:往往单独一只鹤时,大多表现心情;两只鹤则主要表现爱情;三只以上的鹤一般来说就是表现友情了。这些作品告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并不重要,属于传统还是现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做到极至,成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他,做到了!
我在为一只只的鹤赞叹的同时,分明感到那扑面而来的画面是有温度的――他的体温。他是把自己的一生全都交付给了艺术,因而他的人生也是不可复制的。在物质最大化、艺术边缘化的当今,他对艺术的这份痴迷和深爱便愈显得古典而神话。他竭尽心力毕生只做一件事,他的眼晴、耳朵、嗅觉、心灵在随时准备接纳他需要的东西的同时,又坚执地抗拒和坚守着另外一些东西,他很喜欢诗人里尔克那“你要爱你的寂寞”的话语,几十年来,他以超常的毅力,向自己的体能与意志进行极限挑战,在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上孤旅独行,在寂寞中思索,在孤独中劳作,经受着灵肉的双重考量,任何时候都不曾动摇过,直至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令一颗颗心无不向他深致敬意。
当我在这个夜晚与他相识相握的那刻,久居在内心里的恶痛忽然消散,清风徐来,花影浮动,芳香四溢……
这是我身上带的最后一张名片,送给你了。没想到他边说边离开座位走到我旁边很优雅地将自己的名片递我。
这,这,谢谢啊,太谢谢您了!我手执名片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恨汉语怎么不再造出一个比谢字更能表达一腔感佩之情的字呢?我很清楚这只剩下最后一张的名片对他对我都意味着什么,我真的有些担当不起他的这份信任和期待,我非常害怕不争气的自己今生今世辜负了他。平日里,我每每不厌其烦地向人喋喋自己如何执爱艺术,如何为文学而失去许多,如何心在文中甘守孤寂,如何……然而,今日面对他我惭愧无比,深感自己是多么无知可笑,那爱也多么苍白无力,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把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坚贞执著始终视为一种生命应取的常态。他说,我真的没有什么,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只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而已。何况,很多次的拍摄都犹如天助……
是上天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了吗?
早已声名远扬的吴大师,完全可以息影休歇,安享天伦之乐,享受人生万事不关心的闲散,最起码由于高龄和眼疾的原因绝不可以再天涯孤旅地跋涉了,他已超常地完成了自己,完全没必要像西绪福斯那样一刻不停地再去推那块巨石。可是不行,他不可能放下摄影,因为他是将自己的一生彻底交付给艺术的人。一生!这当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那所谓的“看开”、“通脱”、“透彻”、“了悟”等等,他虽然全都懂,却依然执著,他惦记自己一手操办并捐献了大量摄影类藏书的内蒙古“赤峰摄影图书馆”,他计划三年内完成对世界上十七个国家的六十多个恐龙博物馆的拍摄,他打算出版自己的第五部摄影集……
他是做到了把一生都交付,这也许说起来容易,可真正做到难上加难!我向他默然行注目礼,哗哗的泪水中,心头倏然走过:鸟儿虽小,可它飞的却是整个天空……
弦歌台
天热得一点儿也不像是春日的天气。
我懵懵懂懂地随一群作家乘坐一辆专为参观而开的大巴,心一直沉郁着:每次参加这样颇具规格的创作会,差不多都是激奋而来,沮丧而归,自己的那些文字在名家高手如此林立的气场下,早已稀薄苍白得不是东西,只剩下对别人羡煞的份儿,怎能不气馁不自信心丧失殆尽呢?
何况,这次遭遇的事情颇有些怪异,我暗忖怕是会有些不妙。那个我认真记录下每位作家座谈发言的小本子,竟莫名其妙不翼而飞了。我在会议室、住室、餐厅、服务台等处反复寻找查问,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无数次奔走,多么希望它能在某个角落突然出现,但终究却毫无所获,它杳无踪影得那么神秘,那么不可思议。
你还说大家的这些高见卓识你全都记下来了,回去后要好好品味和领悟呢,这下倒好,竟给丢了,丢得不留任何痕迹。一位知情的女作家怅然叹惋。
是啊,丢得这般干净彻底该不会是在预示着什么吧?难道……我不敢往下想。
这天早饭后集体合影,我原是听从安排一直老老实实呆在房间里等候通知的,可偏偏那个喊我的服务员火急拉肚子,待她完事来叫我,大家刚好已照毕散开。我好生丧气,不免又将丢失的本子联在一起,心就更加灰暗得厉害,莫不是莫不是莫不是……我拼命打住,让脑海一片空白。
因为文学,我一直在现实生活中大撒把地退守和放弃在许多人眼里是必定要拼死相争的东西,可当我越来越失望自己的创作,倍感在圈子里没有能使自己硬气的作品时,这种失败带给我的痛楚和懊恼常常令我痛不欲生。我是将一腔真爱连同生命全都给了文学的,可文学所给予我的爱却太过浅淡,太过表层,太过可有可无……
车子跳了一下,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著名先锋小说家拿出一个青灰色、枣核状、体面上有两排小孔的器物给我看,他让我猜猜这是什么。
是埙啊。我接过来,轻轻抚摸着这种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忍不住轻轻吹了一下,又一下。
喜欢就送给你了。先锋小说家很大方很情愿忍痛割爱。
真的?那太谢谢你了!我确然是很喜欢的呢。我说着,再不肯放下,就那样一直用手小心托着。闭上眼睛,内心奔涌着对这位如今无论是文名还是政声都俱佳雷人的先锋小说家的一腔感激,他送埙给我,可否是因了当年的那点小小的情意?当年,作为一家地方小刊物的编辑,我编发过他的稿子。但那是不值得记住的,应该记住的是我,我十分感谢他那高品质的作品对刊物的支持!当然,很可能什么都不是,生活中那么多的事他难道都一一记清楚吗?眼下是,我手里托着他赠的埙就已足够,我沉醉在心满意足里。
有人递一瓶矿泉水给我,不知怎么回事,这时候我的脑海忽然跳出一个念头,埙这种乐器可否吉祥?听声音呜呜的,要是……真该死,我把丢失本子、错过照相又和手中的埙联系在一起,心顿时冷得发抖,浑身直冒慌汗。
我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我拼却全力想转移自己的思绪,那只埙被我用纸巾裹了,装进袋子里,放在货架上,还叮嘱前后左右的同道们一定要替我记好,返回住地下车时,千万别忘在上面啊。
去弦歌台呀!先锋小说家笑答。他的老家就在此地。
什么弦歌台?我一脸茫然。
见我一无所知的样子,他很讶然地小声问:你没读过《论语》吗?然后便告诉我,这儿就是古时的陈国,是有名的孔子陈蔡绝粮地。当年,孔子带领他的弟子们曾三次来此地讲学,他讲的那些道理是让统治者如何治国,如何管理百姓的,最后一次陈国的老百姓不满意了,就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围困在湖中的一个小岛上,不给他们吃喝,一连七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靠吃蒲根生活下来,这之间,孔子忍受着饥饿与困苦,每日仍诵经讲学不止……
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弦歌台已在眼前。
徜徉在四面环水的弦歌台前,仰望高高矗立的孔子塑像,想着当年孔子在此绝粮的困苦与艰辛,目光便陡然模糊起来,时光的利刃划过心头,疼痛的血汩汩流淌。“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高山”,殿前两侧抱柱上的这副楹联,自然引发前来此地的人们对孔子寂寞求索的共鸣。我的心在说,这是成功者的苦难,这苦难足可以被认为是莫大的财富是又一次地成就了圣人孔子,曾巩不是就称孔子的陈蔡绝粮是“圣人齐日月之时,不能违日月之道”吗?想一想吧,倘若孔子寂寂无名,没有成为令人推崇备至的一代儒师、教育家,那他所遭受的苦难和颠沛流离的困厄还能被人记起来吗?还会有眼前这气势不凡的弦歌台吗?时光的流程中,还会有一代代的人来此凭吊吗?普通人的苦难哪怕再不堪再空前绝后地遭劫,除了了无声息地领受,永远也不可能像成功者那样使经受的苦难成为令人赞叹的伟绩和荣耀。
普通人只能永远普通平凡着。
知道吧?先前有过几十年时间这弦歌台成了关押犯人的监狱,我自己就曾被关押在这儿三天半呢。先锋小说家的话让我大感惊异,想不到他还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像不认识似的盯着他看了又看。
这时,一位大牌作家非常郑重地道:这个经历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珍惜,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没有过那可是大不一样的!只是,你才被关了三天半,要是七天半多好啊,那不是就超过孔子了吗?
后边的玩笑话,引得大家十分开怀。
有同行就说,生活对作家而言太重要了,那些写出非同凡俗经典精品的作家,人生道路大都坎坷多舛,当然,贵族作家也有写得好的,比如普鲁斯特,但《追忆逝水年华》也就只能是那样的题材了。
我承认,他说的也许对,但我却不希望自己去经受那所谓生活赐予作家的超常苦难,哪怕苦难是一种意义我也绝不情愿,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一个平庸凡俗的人,永远缺失化蛹为蝶的能力。
本想在弦歌台留影的,可惜同事未带相机,一位不很熟悉的作家倒是主动用他的相机给我拍了两次,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类照片向来石沉大海,了无音信。
重又坐到车上,我突然为自己未能在弦歌台留下影子而庆幸,这很可能也是一种注定呢,我那颗不想经受苦难的心兴许早已被圣人看穿?
也正是在这时候我做出决定,先锋小说家送的这只埙,我绝对不能拿到家里,只可将其安放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