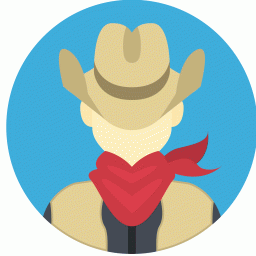母亲, 你在哪儿!
时间:2022-10-23 11:50:52
【前言】母亲, 你在哪儿!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以往每年的这个时候,鳏夫嘉玛尔的歌唱总是跟爱情有关,那让人陶醉的歌声就飘扬在特克勒尔村的上空: 我唱歌,我唱歌, 黑眉毛的姑娘歌最多; 双眸传情送秋波, 吻一吻你的红唇多快活。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鳏夫的歌声被一种凄凉哀惋的调子替代了,再听到他...

母亲是在郭兴上小学六年级的那年走失的。那年郭兴十五岁。
头天夜里,郭兴照例在梦中听见了早已听惯不怪的那些响声了。那是皮带梢儿撕裂空气时才有的响声,跟沙漠蛇遇到危险时,蛇信抖动时发出的嘶鸣一样。天亮后,母亲穿上她那件只在参加村里婚宴时才舍得上身的府绸衬衫,对刚撒了尿从屋后转过来的郭兴说,上午娘要去趟巴扎,你好好在家呆着。此刻郭兴正放暑假在家,总跟同学下河坝抓狗球鱼也没太大意思,就缠着母亲,非要跟她一起去巴扎。母亲有点着恼,说好好好,你去吧,你要是去的话,我就不去了。长这么大了一点也不听大人话。停了一会儿母亲又说,在家好好复习功课,将来才有出息。母亲伸手揉揉郭兴毛茬茬的脑袋,看书看累了,就到咱家瓜地里摘个瓜吃吃,我上巴扎给你买酸薄皮包子带回来。
郭兴“嗯”了一声,眼泪巴扎地目送着母亲走出低矮的篱笆院子,跨过前边的木板桥,消失在了一片葵花丛和玉米丛掩映的村路上。
郭兴家所在的村子叫特克勒尔村,离县城有三公里,中间隔一条车尔臣河。村里那个放羊的老汉嘉玛尔吹牛说,这条河发源于全村人都看得见的那个南天尽头,名字叫穆孜塔格峰的雪山上,河水起初非常清澈,比县里那些干部喝的瓶装水还要清澈甘甜。只是在流经了斜度很大的戈壁大漠后,才变成了即便是澄清后仍有些苦涩的泥浆子。从县城到特克勒尔村,河上架了一座全部由粗壮的胡杨木搭建的桥,桥很宽,也很结实,别说过毛驴勒勒车,就是跑小卧车,大货车都没嘛达(问题)。特克勒尔村濒临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多亏了这条脾性敦厚稳健的车尔臣河,和它伸出去的那条臂膀。那是一条车尔臣河在村南边生发出去的支岔,支岔像一个人叉着的胳膊,紧紧地将特克勒尔村护在怀里,这样以来,再暴虐疯狂的沙尘和沙丘,也始终不能跨越雷池半步,以至这片绿洲里树木葱茏,牛哞羊咩,鸡鸣狗吠,五谷丰登。
村子里大部分住的是维吾尔村民,在经过村子东边的国防公路边,则住着十几户的汉族村民,他们只种少量作为口粮的麦子跟玉米,大部分的土地上种的是长绒棉,油葵及瓜菜等经济作物。眼下正是西瓜和“老汉瓜”上市的旺季,天空中不时可以嗅到它们飘忽的香甜。
以往每年的这个时候,鳏夫嘉玛尔的歌唱总是跟爱情有关,那让人陶醉的歌声就飘扬在特克勒尔村的上空:
我唱歌,我唱歌,
黑眉毛的姑娘歌最多;
双眸传情送秋波,
吻一吻你的红唇多快活。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鳏夫的歌声被一种凄凉哀惋的调子替代了,再听到他的歌声后,叫你心头不由隐隐升起莫明的哀伤。
郭兴家既没有跟汉族村民那样,临国防公路修盖房子,也没有居住在村里头,而是将家建在了特克勒尔村北面的一片荒滩上。郭兴家与村子之间有一条宽宽的排碱渠,渠里终年汩汩流淌着一股碱水,荒滩上长着一丛一丛的野苇子,刺芽子,羊奶疙瘩和各种杂草,一个一个硕大而突兀的褐色土丘上,长着茂盛的沙枣树,临渠则是一些阔叶的弯腰柳,柳叶在风中闪烁着银白的光亮,发出“啪啪”的脆响。
郭兴的父亲郭大古虎背熊腰,两臂过膝,远看活脱脱就是人类的远亲大猩猩。尤其是他的五官,红肉外翻的环眼,又厚又糙的嘴唇,两道浓重的卧蚕眉,胆小的孩子乍一看见他,十有八九被吓得哇哇大哭。从打记事儿起,父亲郭大古跟郭兴说过的话没有一箩筐,无论郭兴干什么,他统统不管不问,在他眼里,这个长得除身材高挑一些,其余外貌都酷似母亲的孩子跟他一点感情也没有。郭大古冬天卖菜,春夏秋都在地里干活。他总是吃过早饭后,又兜上一份中午饭,不到太阳下到车尔臣河西边的镇子后边不回家。母亲的身子似乎停在一个十岁女孩的高度上,再没有往开里长过,有时擀面条还得在脚下垫两块砖。母亲迟钝而倔强,每当夜里父母的房间里发出空气被撕裂的尖哨声,以及郭大古那狗熊一样的喘息声,只有母亲永远是沉默的,似乎那些夜里发生的事情跟自己毫无关系。
母亲答应郭兴说从巴扎上给他买薄皮包子,酸,不知是母亲把对儿子的承诺忘记了,还是连同儿子跟她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一同忘记了,总之是,那个热得太阳能把人晒得秃噜一层皮的夏天的上午,说是要去赶巴扎的母亲竟悄然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自己的老婆没有了,郭兴的父亲郭大古跟个没事的人一样,照样每天一大早下地,太阳落地回家,吃完饭后就躺到床上睡觉,呼噜打得跟往常一样,像头酣睡的猪。
可怜的是儿子郭兴。郭兴一下子没了母亲,生活彻底变了样儿,他除了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寻母征程。
村子里很快有了关于郭兴母亲失踪的传闻。有人说,郭兴的母亲被人贩子骗到和田,卖到更加遥远的地方去了,但更多的人撇着嘴说,唏,就她那个模样,那个岁数……还有人说,郭兴母亲肯定自杀了,说不定是投进了车尔臣河里,被大水冲到罗布庄子去了,整天介活受罪,搁在谁身上都会受不了的,这一点郭兴死活不信,母亲多次搂着他说,为了儿子,她也一定得坚持活下去。也有另一种说法,说郭兴母亲跟牧羊老汉嘉玛尔关系好,有人曾经看见过俩人在一起,郭兴的母亲伏在老鳏夫的臂弯里哭泣,所以他们猜测,会不会是老东西把郭兴母亲给藏匿起来了……一时间,各种说法都出来了。
郭兴在特克勒尔和四周的村子里寻找母亲的下落,连他的同学也都帮郭兴打听,暑假很快就结束了,母亲就跟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看见她究竟去了哪里。开学后,郭兴来到县城上中学,每个星期天,郭兴都要在巴扎上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地转悠,巴望出现奇迹,让郭兴看见母亲的踪迹。从秋天转到春天,从初一转到初三,除了那个身上挂满小孩遗弃的破烂玩具的乞丐总是与郭兴不期而遇外,郭兴每每是怀着希望而来,满腹惆怅而归。躺在寝室的床上,郭兴总是叹息着想,如果母亲跟大街上的那个邵子(傻瓜)乞丐一样,是个啥也不知的傻子多好啊,那样的话,郭兴就可以挽着母亲,把她扯回自己的家,母亲是不分聪明和呆傻的,是自己的母亲就行。想到这里,郭兴就在心底长长地呼喊:母亲啊,你到底在哪里呀!
郭兴初中毕业那年冬天,县上开始了冬季征兵。郭兴虽然个头儿体重都十分勉强,但下乡进行家访的人武部和接兵干部在了解了郭兴的情况后,十分同情郭兴的遭遇,破例批准郭兴入伍,带领着郭兴和入伍的新兵来到中俄交界的塔城边防部队,郭兴在连部当了一名通讯员。
战士在部队都有一次探亲假,假期批下来后,别人都是带着当地土特产,直接回到入伍地探望父母,而郭兴不是,郭兴什么都没带,穿着一身军装来到了母亲的原籍。在部队期间郭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觉得母亲会不会是回到老家去了,母亲可是一别故乡几十年了呀。郭兴曾多次听母亲说起过,自己在老家还有一个小姨,小姨家的住址母亲只说过一遍,就跟用刀子刻在郭兴的脑子里一样,从此郭兴再没有忘掉过。
郭兴先是坐汽车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坐火车来到母亲的老家,根据记忆中的地名,郭兴没有费太大的劲儿就把小姨的家找到了。小姨听了郭兴的叙述,顿时大哭起来。小姨对郭兴说,回家?回啥家呀,你妈是个倔眼子驴,从这里走出去了,她就没有打算再回到这里来。小姨讲了一个母亲过去的一件事,当年,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村里一个寡汉条子趁郭兴母亲一个人在家时,破门而入,欺侮了郭兴的母亲,家里人都劝郭兴母亲忍一忍,哑谜下来算了,因为那寡汉条子是支书的哥哥。可郭兴母亲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到公社告状说理,要求公社法办那个赖种,被派出所的干警连推带搡地轰了出来。郭兴母亲一气之下,连夜就出走了,还是在生郭兴那年,才跟家里打了个信儿,一家人才放下心来。不过,郭兴母亲是绝不会踏上老家半步的,否则她也就不是郭兴的母亲了。
郭兴的希望再次破灭后,年底,郭兴退伍回到了特克勒尔村。令郭兴想不到的是,这一次,连郭兴自己都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了。
原来,在郭兴当兵走的那年冬天,郭兴的父亲郭大古到县棉麻公司交售棉花,在巴扎一个饭馆里吃饭时,遇到一个有几分姿色的中年妇女。这个女人原籍是浙江温州人,她的丈夫在那次震动全国的严打中被判重罪,送到塔里木劳改支队服刑。由于是重型犯,他几乎没有了走出监狱的那一天,就组织其他犯人越狱,结果在一次越狱当中被执勤的武装警察击毙。她远在万里之外的浙江,自然对丈夫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久后的一天,她在公公婆婆和亲人的催逼下,来到劳改支队看望丈夫。到了新疆才得知丈夫已死,她也无颜再面对家乡父老的白眼,就在劳改支队附近租间房子住了下来。开始的时候,她靠着一名北京自由犯的接济,那自由犯种着支队的十几亩菜地,隔长不断地给她送米送面,还有顺手从地里采撷来的蔬菜。不过,北京自由犯在原籍有老婆有孩子,不可能带着她一起回北京,更不可能当一辈子的自由犯。一年后,那名北京自由犯刑满释放,她万般无奈下只好操起了皮肉生意。这天,他跟一个嫖客在县城一家旅馆里完事儿后也到饭馆吃饭,跟郭大古对上了眼,俩人一来一往后不久,干脆合铺一处,过起了日子。
面对形同陌人的父亲郭大古和冷眉冷眼的外地女人,郭兴更加想念自己的母亲,有时候实在想得太苦了,郭兴就走出家门,来到村子北边的沙梁上,极目北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连绵起伏的沙丘。郭兴知道,沙漠的对面,就是石油重镇库尔勒,再往北,翻越天山就是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郭兴的很多战友在沙漠外边的城市里打工挣钱,有的成了老板。郭兴的连长在一次车祸中压断了大腿,退伍后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生意很是红火,在他手下干活的大都是老连队的退伍兵,他曾多次联系郭兴,要郭兴到他的厂里干,月薪肯定是所有工人里最高的。郭兴对老连长的好心表示感谢,但他说自己还不能答应他的召唤,因为他还没有自己母亲的确切消息,在没找到母亲的下落之前,他不会答应任何人的任何事儿。老连长对郭兴说的还是那句话,你先到这里干着,一边干一边找,大伙儿一块儿帮你找,登报纸发启示,办法多的是,总比你一个人在小小的特克勒尔村寻找要好得多。郭兴觉得老连长说得有道理,说自己还想在这里努努力,郭兴最后哭着对连长说,他认为前些年自己的努力都是白费,他现在突然感到,母亲其实根本就没有走远,很可能还在特克勒尔村,至于在哪儿,他不清楚,他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弄清这个问题。
冬天是沙尘暴频仍的季节,那天郭兴坐在沙梁上,正遇上漫天的风沙,狂风搅动着沙砾打在郭兴的脸上,一开始时郭兴还架起两臂遮挡,后来连冻带打,郭兴的脸已经麻木了,就听凭刺骨的风沙对自己施暴。渐渐地,风沙打着尖细的呼哨远去,寒冷和孤寂再次统治了沙漠。经过刚才的周天沙暴,郭兴几乎成了一尊出土的陶俑,稍微一动,瀑布一样的细沙哗哗地从头顶上的棉军帽,耳廓上,脖领上,肩头上往下淌。好在郭兴的听力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隐约听到一个浑浊苍凉的声音,经过仔细辨别,声音来自不远处的车尔臣河畔。现在,随着一群绵羊漫上河岸,那个歌声也清晰起来,是嘉玛尔老汉。老人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鞭子,一边唱道:
牧鞭驱赶着羊群,
胡达(上帝)掌管着命运。
但愿我受过的痛苦,
不要再施加于他人。
羊群一边啃着岸边的干草根,一边发出颤微微的咩咩声,似乎在对老汉的忧伤表示着理解和同情。
一个月后,随着元旦的临近,天气也愈加寒冷了。村子的上空开满了雪白的羊耐疙瘩,柳絮一样的种子在寒风里打着亦梦亦幻的小伞四处飘扬。麻雀从田野回到村子里的一棵棵馒头柳和枝叶稠密的榆树上,唧唧喳喳地讨论着应付三九严寒的大事儿。一位跟郭兴一个村子,又一同入伍,复员后跟着老连长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同年兵,被老连长派回来,专程拉郭兴去乌鲁木齐。临行前老连长发了话,说就是用绳子捆,也要把郭兴这个犟种给我捆到乌鲁木齐来。
俩人在村头一家小饭馆里要了半锅手把肉,两瓶伊犁特,开始的时候,郭兴还能绷着劲儿,后来就抢起酒来。同年兵跟郭兴当兵前是好同学,当兵后又都在一个连里。郭兴当了通讯员,没有执勤站岗的任务,但他总是在同年兵夜里站岗的时候起床陪着他。北疆的冬天漫长且寒冷,从八月份开始下大雪,几乎每个礼拜都下一场鹅毛大雪,直到来年的五月过后。从连队到执勤点还有一段山路,虽然每天打扫,但路上的石头被冻得又滑又硬,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滚下山去摔个粉身碎骨。有郭兴拿着手电陪着,平时孤清寂寞的两个小时就快多了。他们身穿皮大衣,不时将眼睛贴在高倍望远镜上看看四周情况,然后继续在燃着煤火的岗楼里畅谈人生,设计今后的生活道路,甚至即将到来的爱情生活。当然,大多的时候都是同年兵在说,郭兴只是兑着耳朵在听,偶尔插上一句,也是离不开寻找母亲这个话题。同年兵没有更好的话来劝慰郭兴,只好拿别的话题来叉开。
同年兵转达了老连长的意思,郭兴说我还没有找到母亲,说着咕咚一声咽了一大口伊犁特。
同年兵说,你都找了这么多年了,也尽了心了,先工作,再慢慢找。
郭兴说,不,我必须先到母亲,否则我生不如死。
同年兵跟郭兴一个村子出去的,对郭兴的情况自然十分了解,他跟村子里所有的人一样,知道郭兴不可能再找到自己的母亲,但他不忍心道破,只好端起一碗酒跟郭兴碰了一下说,郭兴,作为同学加同年兵,我只能对你说,咱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地活着,首先对得起自己。
郭兴碰过酒碗并没有喝,而是一家伙朝着同年兵泼了过去,大喊一声说,我就要母亲。同年兵迅疾地一歪脑袋,一碗酒扑剌一声钻入他背后的土里。
同年兵这才知道郭兴喝醉了,两斤伊犁特郭兴喝了一斤半,却连一块肉都没吃。他在搀扶着郭兴往家走的时候,那个牧羊的老汉哼着一支奇怪的曲子,跟他们擦肩而过。
睡到半下午的时候,一阵隆隆的响声把郭兴从床上叫醒。郭兴踉跄着走出家门,来到平时坐着的沙梁子上。这时沙尘暴已呈四合之势,一座座沙丘被一种神奇的手如同削剥水果一般,越剥越小越削越矮,陆续被大风刮到远处,再按照沙丘被削剥时的相反程序,坐落在远处。这种无聊的游戏在这里上演了千年万年,似乎成了大自然唯一的乐趣,所以才乐此不疲,恐怕这种游戏还会一直玩儿下去的。
在大风搅得周天浊黄,指头大小的砾石呼啸着朝郭兴袭来的时候,郭兴来到河岸一个岩石洞穴下面躲避。无论沙漠的风多大,沙尘多么狂野,移来多少沙子,都注定被车尔臣河阻挡,再一股脑儿地被河水送到下游,送到罗布庄子去。岩洞是郭兴小时候就常常用来躲避沙尘暴的栖身之所,上学时放暑假,郭兴还跟同学在岩洞里架锅煮过狗球鱼汤呢。狗球鱼刺很少,肉瓷实,用澄清的车尔臣河水来炖,喝之前撒点香菜在里边,鲜得郭兴跟伙伴们一碗一碗地喝,一边喝一边说,。等肚子灌得溜圆,又一泡接一泡地往河里撒尿,笑声顺着河面被河水带去很远很远。
似乎是“咣”地一声响,一切忽然就安静了下来。沙漠上的风来得突然,去得也快,等郭兴走出岩洞的时候,大漠上一派宁静,似乎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郭兴拍打拍打自己身上的沙尘,心情凝重地往回走,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在郭兴经过自己刚才还坐过的沙梁子的时候,发现有人在他坐过的地方插了一溜红柳枝子,红柳枝子隔四五米一根,似乎在为什么人指引方向似的,顺着河岸若即若离地一直朝下游走去。郭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要不就是自己中午喝过了酒,视觉出了偏差。郭兴揉了揉眼睛,弯下腰触摸一下那些棍棍,果然是红柳枝子。郭兴觉得蹊跷,就顺着红柳指示的方向一直走了下去。大概走了一千多米的时候,红柳枝子在一个长满蒿草的低矮沙丘面前消失了,在这个沙丘上,有人用红柳枝子编了一个花圈摆放在那里,红柳枝子是新砍下来的,隐隐可以嗅见一股清苦味儿,枝头干枯的叶子苍绿苍绿,细碎的红柳花好象西天的落辉,紫红紫红。
这时,那个浑浊苍凉的歌声再次响起,并随着岸底羊群一声接一声的叫喊声,渐渐飘向下游:
朋友啊,请别把琴弦拨响,
它会勾起我无尽的忧伤;
我心里已经够苦恼了,
我爱上了一个喀什噶尔姑娘。
…………
歌声还在河的上空飘荡,沙漠深处刮过一阵黑风,黑风过后,大漠上一片宁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连刚才还在那里徜徉的那个小伙子,此刻也不知去向,不知所踪。
后来,不知哪个特克勒尔村的村民说,有人偶尔看见老牧人嘉玛尔的羊群发达了,他身边还多了一个帮手,那是个年轻人,他们住在离村子很远的河边,由于相隔太远,没有看清那个年轻人的模样,不过,看上去他们的日子过得娴静而祥和。
村民们不免猜测:那个年轻人会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