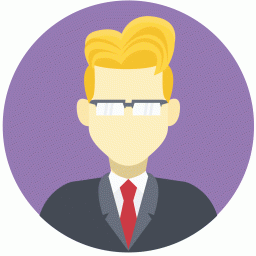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困境转境与进境
时间:2022-10-23 04:39:38

彭玉平,江苏溧阳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中国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华诗教学会理事、副秘书长。曾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120余篇,有《诗文评的体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中国各体文学学史·词学卷》等著作多部,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乐语研究》和《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
黄春黎:彭教授您好!在近年的词学研究中,您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尤其《人间词话疏证》《诗文评的体性》《中国词学史》等力著接连出版,的确令人惊讶!您能谈谈这些著作的撰写过程吗?
彭玉平:谢谢关注!这几年我的成果确实多一些,这其实也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只是出版时间相近而已。像《诗文评的体性》《中国词学史》二书,如果从最早成篇的时间算起,已经是20多年前了。这样来说,我的出书要算慢的。事实上,我的书都是在一个一个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汇合而成,所以特别费时费心。
黄春黎:我注意到您这几年有关王国维词学及其学缘的文章特别多,实际上,王国维的研究虽然一直是热门,但整体的研究进程一直还是很缓慢的,我感到好奇的是,您是如何在王国维及其词学的研究困境中找到自己的进境的呢?
彭玉平:近十年来,我确实通过自己发现的若干新文献以及长期被冷落的一些旧文献,重新调整研究思路,在王国维词学、词学学术史、学术因缘等方面作了一些研究,深化了一些领域,也开拓了一些新领域,相关成果发表、出版了不少。但我的研究在整个王国维词学及其学术史上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我想这应该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检验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我研究王国维,起初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就发现的问题、感兴趣的问题一个一个展开研究,积若干年后,成果的数量才渐渐可观。而且,因为我对王国维的论著读得多,也读得细,所以往往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另一篇文章就在头脑中慢慢构思了,有时会同时写着三篇有关王国维的论文,这样一环套着一环,一篇连着一篇,就有点“一发而不可收”的感觉,学术影响大概也是这样慢慢形成的。所以,如果说我在王国维及其词学研究方面有所贡献的话,那也是从“无心插柳”开始的,当然后来就有意识地规划研究格局了。但我坚守的原则是:尽量拓展他人未曾关注的领域,或者他人虽有研究但我有新的发现,这样的文章我才会写,我不会刻意追求研究格局的宏大。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新材料或新观点,我也是不会去写的。低层次的重复,不仅浪费自己的生命,也浪费读者的生命。
黄春黎:您对王国维的论著读得细致,这从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可见,有许多观点或者对材料的理解,如果没有非常精细的阅读和新锐的理解,大概是很难得出的。我注意到刚才您说对王国维的论著读得比较广泛,那么,您对王国维论著的精读也就不止是文学,更不限于词学了?
彭玉平:是的。王国维的论著,词学、文学方面当然是必读的,但我对他早年的《静安文集》也曾花费了不少工夫去阅读、揣摩,那里面的文章基本是哲学、美学方面的。另外,王国维早年的教育学、心理学甚至他翻译的一些著作,我基本上也通读过。正因为王国维早期的文学研究有着这样丰富的学术背景,所以也注定了后来人的研究同样要拓展研究的视野,才有可能走近他。此外,王国维的大量的经史、地理以及古文字、古器物研究论著,我也尽量阅读,有的因为专业隔膜读得比较辛苦,但经过反复把玩之后,大体还是可以把握的。这种跨学科阅读,对我而言,不仅不是浪费时间,还直接启迪了我对诸多问题的思考,甚至有的文章也是在这种“无意”阅读中触发、形成的,这与王国维提倡的“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的读书法,倒是有点类似。像写《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虽然我是甲骨文的外行,但因为关于王国维的论著读得比较多,所以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产生的情形也与此相似。
黄春黎:我注意到,您对王国维的研究大体上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其一是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其二是王国维词学的学术史研究;其三是王国维的学缘研究。能具体说说,您是怎样产生这种研究格局考虑的吗?
彭玉平:好。这三个维度你说得很对,从我的研究进程上来说,它们大体也是前后相承的。我第一篇关于王国维的研究是考量“三种境界”说的原始语境及其王国维引申后的意义指向。因为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时曾有学生问到这一问题,我这才想起这个问题看似明白实则不甚透明。后来我又注意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有手稿本、《国粹学报》本、《盛京时报》本的不同,三本对勘,能发现许多问题。譬如,手稿中前30则基本上是在此前诗话、词话的基础上进行引申、点评,真正谈到“境界说”是从第31则开始的,则“境界说”并非在王国维写作之前就考虑成熟,而是在边写作、边思考中慢慢形成的。再如,王国维从手稿中选择若干则准备发表前,也很是踌躇,在第一次选择条目时,“境界说”仍未从其理论体系中突显出来,只是到第3次圈定条目时,“境界说”才从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并置于词话的前面。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而王国维1915年在《盛京时报》发表31则本《人间词话》时,不仅缩减了论词条目,而且调整了理论指向。譬如,在《国粹学报》本中带有西学话语的条目,基本上被删除。再譬如说虽然压缩到31则,但论曲的条目不减反增,这说明王国维更注重诗词曲的文体流变,也带着一种明显的“去西方化”倾向。我知道我的后一点说法比较冒险,因为《人间词话》一向被视为是中西美学思想结合的产物,我抽掉了——起码是减弱了西学的影响力,一定会遭受质疑。但我考察《人间词话》的版本变化,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我在中华书局版《人间词话疏证》中曾撰有长篇绪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手稿的所有理论出处(包括明引与暗用)全部整理出来,其结论是确凿的:中国古典诗学才是其词学的主要源头,西学只是以话语的方式点缀而已。王国维1903年才开始接触康德哲学,而此前两年都沉潜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之中。当王国维在中西哲学美学中盘桓了数年之后,他已然发现中西之间主要是言说方式的不同,至其根本底蕴原本可以相通,而他觉得西学中凡是“窒碍”难解的地方,也大都是有问题的,所以王国维其实是停留在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处、契合处,而会通的基石则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之中。在这方面,王国维自己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1914年,王国维在日本京都致信沈曾植就说:“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所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我觉得王国维的这封信可以说明不少问题,应该引起学界重视。
黄春黎:相信一定会!我读过您好多篇论王国维词学范畴的文章,像发表在《文学评论》的论“隔与不隔”一文,发表在《文史哲》的论“境界”一文,以及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文章,我发现您十分注重“语境”。有的在论文题目上直接出现“语境”,有的虽然没在题目上出现,但文章中的考量都是围绕着“语境”进行的。我可以理解为您研究王国维的词学范畴是将“语境”放在首位的吗?
彭玉平:我觉得“语境”是研究一个范畴首先必须考虑的,因为一个范畴的出现本身就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依托语境才有意义。中国古代的范畴在使用上往往有比较随意的特点。譬如,孟子讲气,曹丕也讲气;刘勰讲气,苏辙也讲气。但细细斟酌之下,各家言气,内涵竟各有不同。这是古代文论让人畏惧的地方,但在我看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地方。只有语境才可以让范畴从这种理解的困境中突围。譬如,关于“境界”二字,此前有不少文章探讨其语源,有追溯到《诗经》的,也有追溯到佛教的。但王国维自身使用语境的情况却一直没有人注意到。我在通读《王国维全集》中的早年著作时发现,无论是在翻译著作,还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王国维都有不少使用“境界”的地方,而且其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地理学概念到知识范畴再到美学范畴的变化,这种直接的语源和语境才是最贴近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的语境本身比较微妙,如果不细加勘察,很可能会对其形成简单化的理解,但其实王国维同时还提出过一个“稍隔”的概念,这个概念就基本被忽略在学术视野之外了。在《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又从结构的角度来考察隔与不隔的合理搭配问题,可见“隔”未必被王国维完全排斥,其价值是视具体结构语境而定的,王国维其实是悬“隔”与“不隔”的两极而论,而其理论中心是落在两极之间的,这也是由王国维特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黄春黎:关于《人间词话》学术史,我也读到了您的一个系列,好像有7篇。那么,您是怎样从对王国维词学本体的研究转移到对其词学学术史的研究的呢?
彭玉平:除非是新发现、新开垦的学术领域,一般的学术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不了解学术史,就无法开展新的研究。因为只有知道前人关注过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遗漏下什么问题,才能知道自己所拟探讨的问题是否有价值;否则,很可能就是坐井观天,流于低层次的重复了。我所收集的王国维的研究资料相当可观,中国内地的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相关论著基本上都过目过;此外,像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资料,也请了不少朋友代为复印或购买。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进行。因为我研究的是王国维,他的知名度太高,研究成果太多,这就意味着对我的挑战也更大。此前,我经常看到类似于说“《人间词话》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的话,但我考察了相关学术史后,发现这其实是一句没有根据的随性之语。真实的情况是:从1908年《人间词话》的发表一直到1926年,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其实无人关注并研究这部词话,这其中当然不包括吴昌绶等王国维身边朋友私下的赞赏。只是在俞平伯标点本出版之后,接着是王国维的非正常死亡,才引发了学人的广泛关注,并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第一个研究热潮。但学术史的具体发展轨迹、重点关注的问题、基本观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实学术界的关注是严重不足的,有些问题甚至从未进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如俞平伯标点本与《人间词话》走向经典有着怎样的关系?靳德峻、蒲菁、许文雨、梁启勋等人的文本注释、讲疏或者引述,体现了怎样的学术观念?王国维去世之后,其《人间词话》文本经历了怎样的不断增补的过程?如何看待这种过于膨胀的增补?等等。这些问题十分重要,我个人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希望更多的学人参与到这一学术史的研究中来。因为王国维的词学学术史虽然只是20世纪学术史中的一个个案,但因为王国维的特殊地位和《人间词话》的特殊魅力,因而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意义。
黄春黎:但是,我不能不说,最近也常听到有学者质疑《人间词话》的经典地位,您又如何看待这种质疑呢?
彭玉平:在近年的几次学术会议上,我确实“听到”了一些质疑《人间词话》经典地位的声音,这里的“听到”要加引号,是因为质疑者并非以论文的方式来争鸣,而是发言时附带提及。因为没有成文的文字,以至我也无法准确理解质疑的背景和学理,所以就更不好回应了。其实,质疑《人间词话》的经典地位不是现在才有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人中,质疑的声音已经所在多有,如朱光潜、唐圭璋等都有专文批评王国维,而且朱、唐二人的批评甚至带着釜底抽薪的意味。但既往学术史的事实是,《人间词话》越来越受关注,在至今为止的所有词话中,还没有一部在学术和社会影响上超过《人间词话》的。这说明《人间词话》的经典地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难以撼动的。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也许是:何以这本薄薄的小书会长盛不衰成为经典?这种走向经典的历程反映了怎样的思想观念?如果因为张尔田说王国维晚年对《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吐弃不屑道”以及龙榆生转述的“悔其少作”等,由此来否定《人间词话》的经典地位,乃是依人脚跟了。王国维晚年醉心于经史研究,其对文学研究的热情下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也是人生常态。何况验诸王国维晚年对《人间词话》的心态,张尔田之说并不符合实际;更何况早在1917年之时,王国维虽然认为张尔田的学问才气在况周颐、孙益庵之上,但对张尔田为人的“心事殊不可知”已然感受甚深,这对于自称“简单人”又天性简默的王国维来说,难免心存畏惧,甚至敬而远之。这样来看,王国维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张尔田倾心相谈,坦露心迹,我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张尔田的话很可能是自设语境,他只是在给黄节的信中说:“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其学之大本本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仔细斟酌这段话的语境,张尔田其实是对世人“专喜”推许《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而忽略了王国维晚年学术的“大本本原”——经史研究心存不满,所以出语不免仓促而抑扬过实了。从心态上来说,张尔田其实与“世之崇拜静庵者”一样,只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而已,其所谓“吐弃不屑道”云云更只是张尔田自己的感觉而已,与静安自身何涉?而龙榆生的话大概是来自朱祖谋。1916年之后,王国维在上海与朱祖谋时相过从,而发表在上海《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很可能是朱祖谋曾经寓目过。虽然当年的词学名流几乎集体冷落了这部词话,但原因绝非体制内与体制外这么简单。我个人认为,词话中对以朱祖谋为代表的晚清词人有堪称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朱祖谋等奉为楷式的梦窗词的彻底否定,更是讥其为肤浅,甚至称梦窗为“龌龊小生”,等等,这不免有“逆流”的嫌疑。试图以一人抗对一世,固然可见王国维的勇气,但平心而论,王国维毕竟是有不少出语峻急的地方了。而在《人间词话》发表后,面对曾经被自己大力批评的朱祖谋等人,他也流露出一点“悔其少作”的意思,但这也许只是一种人生策略。在1925年之时,王国维愿意在点校数字后由俞平伯序并交付朴社梓行,就足以说明王国维的真实心态。若真的“悔”真的“吐弃”这部词话,王国维起码在自己身前有足够的理由和能力让其尘封在历史之中。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人间词话》中的不少概念包括“境界”说等已为他人先行提出,有的在表述方式甚至语言上也十分相似,所以将相关理论归于王国维名下,不免有掠美他人的嫌疑。我觉得这就是学理问题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承传乃是常态,但同一话语,何以在他人口中寂寂无闻,而在王国维笔下却熠熠生辉?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理论的价值是在体系当中彰显出来的,王国维将他人曾经使用过的若干概念,结合自己的理解,予以新的界定,其实是以新内涵重新激活了旧概念、旧范畴的生命了,其贡献完全不在新创一名词、一概念之下的。何况王国维以“境界”为核心建构了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并持之以衡诂词史,其理论体系和批评实践中所包涵的现代观念和学科意识,是应该得到学术史的充分尊重的。当然,我认为《人间词话》无愧于经典之名,绝非认为其理论十分周全,无懈可击;相反,我认为其中不仅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特别是手稿,而且偏锋之论所在多有,譬如不能充分认识长调的结构特征,以小令作法移论长调,不能客观对待词史发展与词体变化,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慎重言说的。但因此否定《人间词话》的经典地位也属无谓。这就好像刘勰以一部《文心雕龙》成就一门“龙学”,也曾有学者撰《〈文心雕龙〉能代表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的长篇论文,从10个方面揭出《文心雕龙》的种种不足,而对其杰出成就则漠然视之。一边故意放大着不足,一边故意遮蔽着成就,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客观的研究态度。这种惊人之论的背后往往是学理的严重缺失。《人间词话》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心雕龙》一样,虽然是经典,但也一定存在着学术的不足或者盲区。但有缺失的经典也是经典,或者说,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经典,缺失也是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经典则是由“缺失”之外的因素造就的。我在《人间词话疏证序》中曾经直面此事,至今我的观点也无变化,所以我愿意把这节文字引在这里:“窃思静安论词非徒逞一家之言,乃因时而起,岸然救弊者也。故其不避偏锋,恣意而发。若贬抑长调,鄙薄南宋,甚者以小令作法衡诸慢词,皆为人深相诟责,良有以也。以余观之,静安词学本得失参之。若依词史而论,则未免自限门庭而堂庑未张;若就济世而言,则宛然导引时流而厥功甚伟。”王国维词学的这两面,都是需要我们冷静面对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其实对于全面深刻地分析总结王国维词学缺失的鸿文充满着期待,因为经典本来就不只是用来膜拜的。但就好像盲目的崇拜固然没有意义,随性而发、浅尝辄止的否定又何尝有意义呢!
黄春黎:确实如您所言!经典的意义也只是从主流、主体意义上说的。您研究词学20多年,堪称是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近年的王国维研究又成果斐然,那么其中一定有一些治学的独到体会,能为我们谈一谈吗?
彭玉平:谢谢你!“领军人物”真的谈不上,我只是较早涉猎这一领域的一个勤奋的耕耘者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我相信年青一代学者的学术底蕴和学术锐气是值得信任和期待的。我的词学研究在敬畏之心、庄重之意、勤勉之态上,可以说曾无愧色,因为我很清楚学术在我心中的分量和在我生命中的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词学研究在方法、观念上不算新潮,甚至可以用“保守”来形容。我觉得对于一个将学术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的人来说,以下几点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一、前人言学,有如熊十力所说“根柢无易其固”的,也有如陈寅恪所说“同情之了解”的。前辈学者的核心意思是对原著、原文或某一具体观点要有忠实而深度的了解,就是不脱离基本语境,不用现代观点去扭曲或遮蔽古人,如果不能对古人的观点做到最大程度的理解,则所谓学术判断很可能就成为空中楼阁。二、学术研究不是以还原历史为目的,而是以其彰显客观规律、丰富当今的文化学术为宗旨,这就意味着熊十力所说的“裁断必出于己”,才是体现学者深度和高度的准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精准的判断力,而且这种感受力和判断力越强,其所呈现的学术境界便也越宽阔高远。三、重视文献的基础意义。也许要源源不断地发现新文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文献虽然已经公诸学界,但长期被冷落。像王国维的《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被发现,但数十年间,居然没有一篇研究的文章,真是咄咄怪事。再譬如王国维的《词录》在湮没80多年后重现于世,而学界也显然冷待了这部著作。这些学界的“旧”文献,在新的学术视野审视下,完全可以成为研究者的“新”文献。当然能够有新的文献发现是最好的,我在国家图书馆访书时就曾意外发现过7通王国维致沈曾植的书札,都是散佚在《王国维全集》之外的。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手稿虽然影印问世了,但附在手稿后面的《静庵藏书目》却被刊落,我在国图将其抄录下来,后来专门写了一篇《〈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的文章,发表在《复旦学报》上,以这一材料从这种角度来分析藏书与王国维早期诗学的关系,此前我还没有见到,文献的意义于此可见。四、努力培养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感情。这里所说的感情并非出于一己爱憎之偏,而是深度融入到研究对象的世界之中。譬如,我曾经专程踏访过王国维的海宁故居,踩着王国维当年的足迹,听着曾经震撼过王国维心灵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海宁潮声,我对王国维的诗词突然有了更切近的理解。我去国家图书馆访读王国维的手稿,其实并非完全求得文献的真实——部分手稿已影印,真实性是显在的,而是为了求得一种捧读手迹、如晤对古人的感觉。学术之敬畏、庄重,除了其本身内容之外,也包括这些外在的东西。五、沉潜含玩的研读工夫。我认为现代的学术研究,功利性大大增强,但如果失却了沉潜含玩的工夫,其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也很难经受住学术史的检验。古人讲“十年磨一剑”,又说“板凳要坐十年冷”,等等,无非是把对学术的沉潜含玩作为优秀学者的一种基本品格。现在过于频繁、流于形式的考核等,对于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示出来;但盯着现在,还是放眼未来,这就要看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定位了。我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反复把玩王国维的《词录》,一直也未能找到研究的角度。后来我找到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这是给王国维编纂《词录》以启迪的一本书;又根据《词录》体例多仿照朱彝尊的《经义考》;再加上《词录》编纂于《人间词话》撰述之前,其间的理论承传自然不能疏忽;而罗振常的补证也同样值得关注。这些要素慢慢汇集起来,我也就找到了研究的路径了。后来这篇两万字的长文发表在《文学遗产》上。六、“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的读书法,这是王国维告诫他人的读书法。我觉得在当下略显逼仄的学术环境中,要“不悬目的”可能有点脱离现实,但王国维的“自生目的”才是“不悬目的”的目的所在。换句话来说,虽然是目标读书,但读书的范围不能过于狭窄;太过狭窄的读书会束缚思维发散的空间,也影响到学术判断的宏阔与大气。“目的”是自在的,而过程却可以“不悬目的”。我本人在研究王国维的过程中,虽然侧重于文学、词学,但其关于甲骨文、音韵训诂、古史地、古器物、民族关系等的论著,也是广泛浏览的,而且与王国维同时的罗振玉、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的论著,眼力所及,也不放过。这些论著的作用也许不会在当下的研究中立时显现出来,但作为一种知识储备,也许会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七、由微观以达宏观,做足微观,适度中观,谨慎宏观。我虽然是学理论出身,但我一直谨守师训,不敢随便作汗漫而无边际的所谓宏观之文。以前章学诚曾说天下学术不出“沉潜考索”、“高明独断”二途,其实高明独断也往往是从沉潜考索中来。熊十力提出研读佛书有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四要”。但这“四要”之中,踏实、分析是基础,凌空、综会是提高,其中所包含的学术“程序”其实甚明。循序渐进,才能臻于高明独断之境。有鉴于前贤垂诫和本师教诲,所以无论是在晚清民国词学研究,还是在王国维研究中,我都是以大量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先做好细致踏实的考索分析之功,然后再综会、凌空,以谋更高远的论说。即使像我刊发在《武汉大学学报》的《王国维的哲学、宗教观念与“人生”诗学》这样的文章,也是在我经过了六七年的研究发表了20多篇相关文章之后才写出的,而这也不过算是“中观”的文章而已。我一直认为在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中,没有众多个案研究作为基础的宏观研究很可能是脆弱的。上面的这些想法是我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总结出来的,也许并不具备多少普适意义,但此在我却是甘苦之言,希望与学界的朋友们多多交流。
黄春黎:谢谢您!如此细致而翔实的研究总结一定会对年轻学人有所帮助!您能根据您的研究成果,对中学语文教师简单指点一下诗词教育的思路和方法吗?
彭玉平:词学是从填词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学问,回过来对于诗词分析当然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觉得诗词教育,要把诗词文体的特征放在首位,也就是诗词它应该是怎样的?有哪些文体规范?要达成怎样的审美效果?这些因素明白之后,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分析讲解。从教师的角度来说,还应该对这一文体的发展源流、风格流派有所了解。在这些基础上再来对具体的作品进行分析,看看它的特殊性在哪里,是否属于变体,变体的价值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是作为讲解分析的背景而存在的。而具体在分析作品时,名句当然要重点分析,但篇章结构、意思承接的脉络也需要梳理清楚。对于一些字眼之类,多一点分析,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诗心。如王国维为什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句,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原因就在于这个“闹”带着声响、带着场景,能够将春景的热烈一下子渲染在读者面前。如果是“红杏枝头春意在”,作为句子,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字作为一种静态描写,太普通了,也很难把读者带进“现场”。诗词的妙处大多在这些精微之处,有时感受比分析要更有魅力。
黄春黎:可以说,中学古典诗词教学对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或充分体现,这恐怕也与我们对古典诗词的认识局限有很大关系。您能为我们谈谈,中国古典诗词教学对青少年的人格形成和心理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吗?
彭玉平: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其实也是当下很严峻的问题。我们平时都宣称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但无论是在学校教育还是在社会教育的环节,我觉得对诗词的重视程度都严重不足。最突出的例子是:高考作文竟然将诗词创作拒之门外。无论是全国卷或省卷,往往在作文的要求一栏特别注明:“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且不说这是一个在意义上存在矛盾的病句,何以可以接纳诗歌之外的所有文体,惟独将诗歌摒弃在外?这在其他国家,也许无可非议,但中国是“诗”的国度啊!诗的国度拒绝诗歌,不说荒谬,也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我曾经写过一篇《不要轻易对诗歌说“不”》的文章,发表在《当代诗词》杂志上,就是主要针对高考排斥诗歌而论的。现在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中学生处于心智发展的重要阶段,青少年的人格形成和心理发展中如果缺少了诗词教育,很可能会使他们的心灵被世俗的东西所蒙蔽所污染。诗歌的纯洁、高雅,无形中会让人生变得从容而优雅起来。让学生们在传统诗歌的瑰丽景象中感受并接受熏陶,强固自己的心灵,在纷繁复杂的尘俗中获得判断美和丑的能力,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养成对于人的一生才是最为重要的根基。我觉得不仅中学要强化诗词教育,小学阶段就应该重视了。文化是在传承中创造的,传统诗词在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便退居到主流文化的边缘,现在到了重新审视并重新激活诗词力量的时候了。
黄春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兼职编辑。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