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词汇习得实证研究成果综述
时间:2022-10-10 08:4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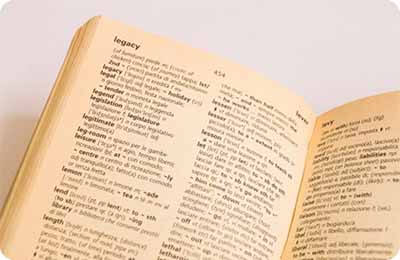
【摘 要】词汇习得是语言习得的核心。本文综述国外词汇习得实证研究成果,以期加深我们对词汇习得的机制、影响词汇习得的因素以及一语和二语词库的词汇表征异同及相互影响等方面的认识。
【关键词】词汇习得 词库 实证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8-0047-03
【Abstract】Lexical acquisition is the cor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indings of foreign empirical research on lexical acquisition in the aim to enhance our knowledge of such aspects as the mechanisms of and the constraints on lexical acquisi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1&L2 lexicons.
【Key words】Lexical acquisition Lexicon Empirical research
一、引 言
词汇习得隶属于语言习得,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国外在词汇习得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对这些成果进行综述,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词汇的习得以及心理词库构建机制的认识。词汇习得牵涉到母语词汇习得和二语词汇习得。本文不区分母语和一语、二语和外语及习得和学习这三对概念。
二、母语词汇习得研究
1.词汇习得中的语境因素
一般研究认为,儿童词汇习得的成功应归功于外界可容易被儿童感知的物体和特征,即把语音与感性经验的显性方面联系起来。但直接经验以外的语义技巧被发展科学家忽视。Corrigan(2008)认为语言环境中的语义输入模式为儿童构建有深度和广度的心理词库提供了线索。比如一个儿童从未见过一种叫orca 的东西,但他可能知道那是鲸鱼的一种,是哺乳动物。这是因为那位儿童可以通过这些词汇与其他词汇的共现(co-occurrence),即语境,发展对词汇的微妙认识。对人类语言而言,环境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语言环境并不贫乏而是很丰富的。有许多语言输入模式为儿童提供意义线索,特别是词汇微妙意义方面的线索。一般认为一语学习者得到的语言输入在形态句法方面都较简单,但是作者认为一定的形态音系复杂度可能有助于儿童的词汇习得,学习者可利用语境来理解输入中有难度的词汇。而输入刺激越简单则儿童得到的语义信息越少,语言输入中如果没有丰富的语义信息,语言习得者就不能构建意义丰富,语义详细和有内在关联的词库,也不能有效处理和应用这些知识。D’Odorico & Jacob(2006)(转引自Corrigan(2008))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但输入本身并不足以促进儿童词汇理解的进步,除了语言输入外儿童至少还需要两种认知技巧:意图理解技巧(intention reading skills),它要求儿童理解不能直接感知的复杂的语言模式;模式发现技巧(pattern finding skills),即范畴化。作者在文章中引入了三种模式,即隐含式动词因果性(implicit verb causality)模式;隐含式情感意义(underlying affective meaning)模式及生僻形容词(rare adjective)模式。作者还发现语言输入会改变一些语义范畴的结构从而使词汇习得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容易。传统的心理词库理论认为词义被学习后储存起来,甚至是不依赖语境的。这种观念是有缺陷的,比如不能回答学习者如何区分词汇的核心意义和边缘意义。新观点认为词汇的意义不是被存储(stored)而是以输入单词的共现或语境为基础被建构(constructed)的。共现在构建词汇意义方面不可或缺,共现分为直接和间接共现两种。在语言习得的早期直接共现占主体,随时间的推移间接共现逐渐占据主体地位。
2.接受性词汇和表达性词汇的习得
儿童习得的词汇可分为接受性词汇(receptive lexicon)和表达性词汇(expressive lexicon)两种。Stolt等人(2008)通过对35名芬兰儿童词汇发展的纵向研究发现接受性词汇比表达性词汇的习得要早、速度要快、个体差异要大。在表达性词汇习得中有性别差异,而在接受性词汇中则没有。两类词汇的语义词汇范畴发展相似,统计发现两类词汇均经历了从社会名称(social terms)到指称(reference),从述谓(predication)到语法的转变,这在跨语言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这也说明词汇语义范畴的习得与目标语的结构无关。但在接受性词汇习得中动词习得较快,根据Goldfield(2000)(转引自Stolt(2008))假设这可能与语用有关,因为母亲总是让孩子做什么而不是说某个动词,所以母亲促进了儿童的名词输出而很少有动词输出,所以在理解性词汇中动词产出优先于其它词汇。女孩的两类词汇习得均早于男孩,且两类词汇量均比男孩大,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会影响成年后的语言能力。接受性词汇发展较早说明儿童产出第一个单词时他们的语言发展以先于此开始了。但是Bates等人(1995)(转引自Stolt (2008))发现拥有大量接受性词汇的儿童表达性词汇规模个体差异较大,说明拥有很大的理解性词汇并不能保证儿童用相似的方式进行表达性词汇的习得,这种早期的差异可能是因为理解和输出技巧反映的是语言的不同方面,是通过不同的神经系统调节的。大多数儿童的表达性词汇增长速度是由慢到快,有些儿童则出现高原现象(plateau),即两种类型的词汇习得速度在一段时间的增长后突然慢了下来。Goldfield & Keznick(1990)(转引自Stolt(2008))发现接受性词汇也有相似的现象,只是因为儿童在词汇习得早期已经具备了大量的接受性词汇,所以其增长速度不像表达性词汇那么显著。整体上儿童词汇爆炸(vocabulary spurt)与其词汇规模有关,即儿童的词汇规模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才会发生词汇发展的增速。
3.短语节律效应
Christophe(2008)还发现了儿童母语习得早期的短语节律(phrasal prosody)和功能词的互动。婴儿在大约一岁时接触到节律短语并用他们来限制词汇切分(segmentation),成人同样用它们来约束在线句法分析。两岁婴儿能用功能词推知其不认识的实词的句法范畴。这说明节律界限可助于划分句法成分的界限,而功能词则帮助标明这些句法成分。
三、二语词汇习得
1.新奇音位对立体的习得
二语学习者经常面临的问题便是二语中新奇音位对立体(novel phoneme contrasts)的感知和学习。尽管一般认为这些困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二语的接触加以克服,但是这种方式对二语词库的音系结构影响如何?Hayes-Harb & Masuda (2008)考察了英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对日语长短辅音对比的习得,发现学习者在初始阶段没有对日语的长短辅音对比在词汇表征中进行系统连贯的编码,但在学习一年后他们日语词库的音系结构与日语本族语人士相近,说明二语词库在二语学习的第一年就能发生重大改变。成人二语学习者的典型困难就是在一语和二语音素构成及音系结构不同时感知和产出二语音素,这种困难就是二语听说中“外国腔”的根源。学者认为一语对二语音位对立的影响取决于一语和二语因素的对比,即二语听者如何将二语音素映射到相应的一语因素上去。证据显示二语学习者即使是在多年的学习后仍可能将二语有的音位对立中和(neutralize),但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区别能力会逐渐提高。作者通过实验发现有经验的学习者同本组语者在听力任务上能力相差不大,但在产出性任务中远不及本族语者。Werber & Cutler(2004)及Cutler(2006)(转引自Hayes-Harb & Masuda(2008))研究也证明学习者的经验能够调节母语对二语词汇音系结构的影响。为什么二语学习者能够将日语的单音(singleton)和双音(geminate)的区别性词汇表征存储在词库中却不能准确的输出呢?原因可能是学习者开始时只是将二语新奇音素作为与其最相近的母语音素的异体进行编码,当该新奇音素在听力中出现时,他们只需要知道该音素与其母语因素不同就可以将新奇语音素区别开来,所以二语学习者在听力中表现较好。但在产出性任务中,二语学习者需要提取相关的词汇表征,如果二语音系对比没有被准确的编码,他们就会遭遇产出。所以帮助二语学习者分析二语新奇音位对立有助于他们建立对比性词汇表征,提高感知和产出二语的能力。
Hayes-Harb(2007)研究发现成人通过接触二语提高对新奇音位的感知能力,具体是借助于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s)和数据信息(statistical information),即输入语言的声学特征来实现。数据显示成人可以仅凭数据信息进行学习,但是最小对立体使他们对新奇音位的感知更精确。
2.混合代码及母语耗损现象
二语习得的一个显著现象便是习得的混合代码(codemixing)现象。Treffers-Daller(2005)分析了含有法语和荷兰语的复合词如legume+winkel以及荷法双语者经常插入到荷兰语中的法语名词短语如carte d’ identite。作者发现这种混合代码既不同于传统的借用(borrowing)也不同于传统的代码混合,作者将其称为插入性混合代码(insertional codemixing),是借用和代码转换的中间状态。这种插入到荷兰语中的多词单位既非独立的单词亦非完整的成分,其在心理词库中的地位暗示了句法和词库间存在接口。作者认为代码混合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耗损(attrition)或者因需要特殊词汇而引起的词汇空缺等。Liceras等人(2005)研究了双语儿童产出限定词短语(determiner phrase)时的功能-词汇混合模式并运用语法特征拼读假设(grammatical feature spell-out hypothesis)进行分析。该假设认为在两种语法特征得到激活时,儿童依赖两个词库对包含最大不可解读特征的功能范畴优先进行代码混合。如对于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儿童,混合话语el book将优先于the libro。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儿童对显性的形态音系刺激特别注意导致抽象形式特征的激活。作者认为早期的功能-词汇混合证明儿童在自然发生语法中单个目的语抽象句法特征的激活。具体而言,功能-形态产出模式是句法性激活的。由于拼读时具有大量抽象特征的形素优先,所以对于任何语言,统治语(dominant language),即在限定词―名词序列中经常性提供功能性自由词素―限定词的,将是其限定词包含更多不可解读特征的语言。如果两种语言的限定词包含的不可解读特征相近,则二者机会均等。
Bar-shalom & Zaretsky(2008)研究了母语为俄语的俄-英双语儿童的母语耗损,即在形态句法和词汇方面的失落,结果显示双语儿童存在少许体误(aspectual errors),在形态手段方面没有发生错误,但形态句法和词汇错误很多,所以母语耗损存在一定的选择性。耗损母语产出性错误主要发生在从习得初始阶段遗留下来的母语语法上。产出性错误和母语未终断的时长正相关。所以二语环境下经常性的母语使用有助于延缓母语耗损。双语儿童在习得早期经历一个双语混合阶段后,大概两岁六个月时突然中止双语混合。对此学者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成人双语混合受语法规则制约,即混合语受第三种语法约束。但是儿童和成人的语法结构不同,那么制约语码转换的语法要素在儿童早期语码转换中不存在,所以双语儿童早期的语码转换不受任何语法制约。还有人认为成人语码转换不受外在语法制约,只受双语自身限制因素的制约。作者认为第二种观点也适用于儿童语码转换,即儿童与成人的语法组织一样。作者还发现双语转换与儿童的双语流利度相关。
3.二语心理词库的特征及二语概念习得
那么,二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的心理词库组织有何不同?Zareva(2007)运用词汇联想(word association)测试发现二语者和本族语者词汇组织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成人二语学习者像本族语者一样偏爱用聚合式的(paradigmatic)词汇联想,作者推测可能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认知技巧和词汇熟悉度。
Elstor-Guttler(2008)研究了母语词汇化模式对句子环境下二语词汇处理的影响。作者具体研究了一语中的多义词是如何在二语中用独立的单词实现的。如母语为英语的高级德语学习者将德语中的blasé实现为英语中的bubble和blister。研究发现一语词汇化模式影响二语语义处理,即使在强二语环境下也是如此。学习者读到特定语境下的二语词汇时激活的词汇概念与本族语者不同,所以要习得类似本族语者的词汇概念,习得的时间越早越好,但是对词汇间联系的习得则是年龄越大越容易习得。而平行双语者(parallel bilinguals)似乎将cup和bowl的概念界限置于单语者界限的中间。Abel(2003)研究了二语者和本族语者在英语习语方面的差别,发现二语者没有本族语者那样多的习语词条,因为二语者接触习语的机会要小的多,所以二语者在习语处理中多依赖习语内部成份的词条和相应的概念表征。
四、结 语
词汇习得作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国外学界已有诸多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实证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弱项,所以介绍外国的实证理论将是我们对词汇习得的相关问题和理论有更好的认识。词汇习得研究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 Abel, B.(2008).English idioms i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lexicon: a du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9(4): 329~358
2 Bar-shalom, E. G. & Zaretsky, E.(2005).Selective attrition in Russian-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preservation of grammatical asp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2(4): 281~302
3 Cantone, K.F. &Muller, N.(2005).Code switching at the interface of language-specific lexicons and the comput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9(2): 205~225
4 Christophe, A.(2008).Bootstrapping lexical and syntactic acquisition. Language&speech, 51(1&2): 61~75
5 Corrigan, R.(2008). Beyond the obvious: constructing meaning from subtle patterns in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quaterly, 29(2): 109~124
6 Elstor-Guttler, K.E.(2008). First language polysemy affects second languag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evidence for activation of first language concepts during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4(2): 107~187
7 Hayes-Harb, R.(2007). Lexical & statistical eviden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phoneme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3(1): 65~94
8 Hayes-Harb, R.(2008). Development of the ability to lexically encode novel second language phonemic contrast.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4(1): 5~33
9 Liceras, J.M. et al.(2005). Bilingual early functional-lexical mixing &the activation of formal fea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9(2): 227~252
10 Stolt, S. et al.(2008). Early lexical development of Finnish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 First language, 28(3): 259~279
11 Treffers-Daller, J.(2005). Evidence for insertional codeminxing: mixed compounds and French nominal groups in Brussels Dut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9(3&4): 477~508
12 Zareva, A.(2008). Structur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mental lexicon: how does it compare to native speakers’ lexical organizatio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3(2): 123~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