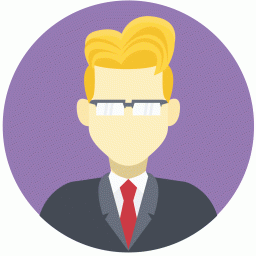西夏占卜考
时间:2022-08-27 07:28:43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对羌党项西夏占卜文化资料的梳理、分析与论述,对西夏时期的占卜文化进行初步探索,说明占卜在西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认为在占卜文化中易学被发展运用,并将西夏占卜文化推向新的阶段。
关键词:西夏;占卜;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西夏王朝是羌族的一支党项族建立的王朝,主要以党项族为主体,羌族文化是我国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西夏文化深受汉族河陇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西夏不断的吸收汉族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和典章制度,发展儒学,弘扬佛学,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党项文化为特色的西夏文化。西夏文化容丰富,除了神秘的西夏文字外、传统党项的卜筮文化、西夏的易文化也闪烁着迷人的光辉。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来了解和论述西夏占卜文化的发展轮廓,对西夏的占卜进行探索研究并试着全面的认识。
一、西夏占卜文化由来已久
占卜意指用龟壳,铜钱,竹签,纸牌或星象等手段和征兆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的迷信手法。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西夏有一些占卜之术,可以预卜吉凶。占卜预测是西夏进行各种活动的首要依据和先决条件,有了占卜预测的结果,西夏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对症进行活动。宋兆麟在《巫与巫术》中提出:“占卜是巫师的重要活动之一。所谓占卜,是指占卜者用自然的、机械的或者人为的工具盒方法,向神询问过去或将来人事和其他事物的结果,并根据占卜工具上所显示的兆纹、信号等,判断吉凶祸福,认为上述信号就是鬼神的意志,人们根据这样得来的信息,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
(一)、党项羌人崇拜鬼神
历史记载党项:“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对于天的崇拜是党项人最早的信仰,随着党项人的内迁信仰内容增加,并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归之与鬼神,并且崇尚巫术,盛行占卜。
查阅史籍可知,其占卜文化源远流长。汉代司马迁《史记》记载:“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今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占伐攻击,退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由此可见,早在汉朝时期,在羌人中就存在占卜和崇拜鬼神的事实。宋朝著名科学家,曾参与领导对夏作战的大臣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就明确记载:“盖西戎(指党项人)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又见《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党项人“笃信机鬼,尚诅祝。”《辽史・西夏外纪》记载:“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西夏文译本《类林》将汉文原本的“巫”译成“卜算”,说明党项人认为“卜”和“巫”是一样的。西夏的传世碑有两个,其一西夏黑水桥碑的诏告记载:“敕镇夷郡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之神等,咸听朕命…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可见党项人正如其他尚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在西夏人的原始信仰中敬奉鬼神十分普遍,这种鬼神主要应是指自己的祖先和灵魂以及党项人最敬畏的一些鬼神。
(二)、党项羌人传统卜筮
西夏党项羌人是羌人的一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生。”羌是牧羊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与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古以来对羊就有一种神秘的依赖,在其占卜文化中亦不少用羊来进行占卜。在《西夏纪事本末》中记载:“西夏旧俗,凡出兵先卜,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髀骨卜师,谓之厮乱,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座位者王位也;近傍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间以奉神鬼,不敢居,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位胜负。二擗竹。擗竹于地以求数。三羊。先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视其五脏,羊肠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谓之生跋焦。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
炙勃焦是用羊骨来占卜,羊骨卜这种方法非常古老,至今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这种方法仍在流传。黔西北彝族发现的彝文书籍中曾提到“羊骨卜”起源。据说这种占卜方法是“上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发明的,发明者举腮挨。擗竹就是求签,这种方法与《周易》筮占极其相似,由此可见易学在当时就已传入党项羌并得以运用,中原地区的占卜与党项原始的占卜方法相融合。《周易》的筮占的具体方法已经失传,通过对党项羌擗竹占卜术的研究对现代学者进行《周易》的全面探索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西夏建国后占卜的发展
开国皇帝李元昊称帝之后,从兴庆府到西凉府“祠神”。乾七年(1176年)夏仁宗在甘州黑水河边祭祀、立碑、祷告“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我邦家……”。从这块碑可见西夏建国后任然对鬼神和自然的崇拜。
西夏立国后,在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置“卜算院”,专门派遣一两名官吏管理佛道教以外的民间,仪式事务,各地方也设置有卜算。西夏政府任命的巫师称之为“官巫”。占卜是巫术的一个职能,其目的是问凶说吉,解决疑难,在党项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深深影响西夏的国家政令。
德明对星相、占卜十分迷信。每当有特异星象出现时,就认真预测兵事,析辨吉凶而行之。《宋史・夏国传》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二月,德明第二次出兵侵甘州时,见恒星出在白天,认为不利,就退兵而还。天圣八年(1030)九月,西州有谣言传说:“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很忧虑,就出居贺兰山而攘之。明道元年(1031)七月,镇星犯鬼时,大风扬尘拔木,德明心恶之,祝曰,“州其当之乎”。从上述资料可知,德明精天文、通兵法,对星象等占卜术都很了解并且很推崇。
从史料中得知西夏时期占卜文化中的易学也得到发展。李元昊时,应用和学习《太乙金鉴诀》,它是《周易》与《历法》结合的书。谅祚主要是广蕃礼,用汉礼,向宋仁宗求得《易经》在的《九经》,以为夏国所用。秉常时,因梁氏专权,穷兵黩武。乾时期,为西夏占卜的学习传承创造了条件。党项人盛行卜术,包括出兵打仗的军国大事,在出征前都要先占卜吉凶,吉兆则可行,凶兆则不行。就现存史料可知,李元昊将《太乙金鉴诀》与《野战歌》的基本理论与战术,广泛应用在军事战争中,把党项的“尚武”精神、游牧民族的特有军事战术与中原汉代的军事理论、战术很好地结合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学习应用占卜文化的典范。李谅祚是向宋请回《易经》的第一人,为西夏易文化的学习发展创造了条件,为西夏著名易学家斡道的出现打下了伏笔。
仁孝中兴,儒学大盛,文体大备,易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以宰相斡道的西夏文著作――《周易卜筮断》为代表,表明着党项民族学习华夏文化达到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水准,也表明西夏社走向了一个“文德教化”繁荣发展的文明进程中。孔子曾感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知,斡道西夏文《周易卜筮断》的出,不能看作一简单的个人成就问题,而是西夏社会发展一定进程的产物。黑水城文献中有关对《五星秘集》的记载,该书是骨勒仁慧于1183年编成,是关于星和行星的卜辞,包括对婴儿性别的占卜辞以及用天上云彩颜色占卜吉凶的卜辞。西夏时期的占卜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对其发展和扶植,但是也不开西夏人们对其的推进,从而对国家的稳定发展,文德教化的推行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三、存世西夏占卜文献举例
西夏王国在1227年在蒙古大军的进攻下灭亡,大量书籍也随之消失,但随着近现代考古工作的进行,不断的西夏文献重出于世,其中包括很多关于西夏卜筮类的文献。一些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为西夏占卜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写本《卜筮要诀》的探索,彭向前先生认为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可分别拟作八卦象例、摇卦诀、六十卦歌诀以及六十四卦占卜辞、占诗;并从讳字、出土地点、抄本里的通假字入手,论证了其为西夏时期的抄本。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易学与西夏的占卜文化的都有积极的作用。
黑水城出土的《六十四卦图歌》,有学者认为其底本问北宋初年写本,这部文献的保存完整,长达四十余页,其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各卦图的爻间分注干支、五行、六亲、世应,下注月卦身、飞伏,再下注各卦历史出处的编写体例,乃至正文的“赞曰”,都为获自日本明刊本《断易天机》所继承。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张义乡小西沟出土的西夏文献占卜词,为我们研究西夏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次发现的占卜词有两张,都是用西夏文草书写成,经专家翻译和研究其内容是,第一张为:“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恶。申日万事吉。酉日遇于贼。戌日有倍利。亥日有喜事……”第二张的内容为:“寅后日变甲是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更时安。亥后日变任时安……”这对研究西夏人的社会生活习俗、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写本《瑾算》,涉及五行、八卦、干支,至今还没有被破译,但可以确定是用来占卜的书籍。
结语:
西夏的占卜文化是我国古代占卜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一块特殊的组成部分,其中对于易学的发展研究更是将西夏时期的精神文化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对现代的周易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M],中华书局,1985
[2] 脱脱,《辽史》卷115《西夏外记》[M],中华书局,1974
[3] 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M],中华书局,1975.07
[4] 吴广成,《西夏书事》四十二卷[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05
[5]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06
[6] 吴天墀,《西夏史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
[7] 傅海波,《剑桥中国史・西夏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08
[8] 李范文,《西夏通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08
[9] 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06
[10] 卡坦斯基,《西夏书籍业》[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04
[11]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12
[12] 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