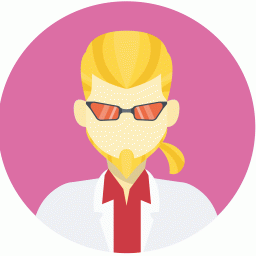学术期刊的学术视野与创新
时间:2022-05-30 11:40:37

内容摘要:敦煌研究已创刊三十周年。《敦煌研究》创刊伊始,就已经注意到开拓学术视野的问题,其作者群体广泛,刊载内容丰富,并将刊发论文范围扩展到了石窟壁画保护等自然科学领域。
关键词:敦煌研究;创刊三十年;学术视野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256.1;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04-03
Academic Vision and Innovation in Academic
Periodicals-for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Dunhuang Research
CHAI Jianhong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73)
Abstract: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inception of Dunhuang Research, which has expanded the academic vision since the beginning by carrying papers on many topics written by a group of authors in diverse studies, in both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including the preservation of cave wall paintings.
Keywords: Dunhuang Research; Thirtieth anniversary; Academic vision and innov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研究》是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从1981年试刊、1983年正式创刊至今,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到2013年4月,共出刊147期(包括试刊2期,特刊8期),成为我国乃至国际敦煌学界认同的标志性领军刊物。
众所周知,《敦煌研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推进中国敦煌石窟的保护与“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复兴而诞生的。1983年8月,由敦煌研究院发起并举办了首届全国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担负组织、团结和协调全国敦煌学研究力量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宣告成立。于是,创办一份相关的学术刊物势在必行。我作为应邀参加1983年敦煌学讨论会的代表和首批学会会员,可以说也是吮吸着《敦煌研究》的乳汁(学术营养)而蹒跚地进入敦煌学的研究领域的。因此,在她三十岁华诞到来之际,愿意将自己的一点粗浅感想提供出来,以寄托祝愿之心意。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因陈寅恪先生的首倡,“敦煌学”被学者们誉之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或称“显学”,或谓之“冷门”、“专学”。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敦煌学百年”的笔谈短文《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中说:“敦煌学是否是一门真正经得起严格科学界定的独立学科,国内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又提出拙见:“要使敦煌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除了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注重本身的学术史研究外,还必须努力梳理厘清它和相关学科的内在关联,而不能只停留在‘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笼统表述上。”(详见《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实际上,一门学科的学术渊源与学术关联还必然要涉及学术视野,尤其是研治敦煌学这样一门在中外古老文明交汇、各民族文化交融大背景中产生的学问,能否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至关紧要。这显然也关系到《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敦煌学辑刊》等敦煌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与刊文范围。例如,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建伊始,有关敦煌学和吐鲁番学是否应合在一起的不同意见就一直没有停歇,而敦煌学和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龟兹学、丝路学的关系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更不用说它和传统的国学以及文献学、考古学、语言文学、历史学、简牍学、碑刻学、民族学、艺术学、地理学、宗教学等的血肉关联了。还记得我们在参与编撰《敦煌学大辞典》时,虽然编委们达成的共识是:这部辞典的词条应该姓“敦”——即围绕敦煌遗存的文物、文献立词条,但是,要厘清“敦”姓的血脉渊源与传承关系却绝非易事,因为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处“丝路咽喉”,是“华戎所交”的文化都会、经济重镇、宗教圣地,可谓“百姓”汇聚,难辨你我。因此,在具体的撰写中,大家又都明确了要“立足敦煌,放眼中(原)西(域)”。
令人高兴的是,《敦煌研究》创刊伊始,就已经注意到开拓学术视野的问题。1981年第1期试刊上所登文章,还是比较局限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所内研究人员所写论述莫高窟艺术的文章。1982年的试刊则开始登载所外学者的非艺术类论文(如张鸿勋的《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一文)。1983年的创刊号中,则登载了丁明夷论述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孙修身与党寿山考释《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日本樋口隆康介绍印度巴米羊石窟以及通报敦煌研究院与印度、法国、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文章。1985年的刊物则开始将刊文范围从单纯社会科学拓展到敦煌石窟保护的自然科学范围(有李最雄等学者撰写的4篇论文),与自然科技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自此,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不仅如此,从1988年开始到2012年,还办了总共10期全部是论述石窟保护、修复技术手段文章的专辑(从2007年到2011年为每年一期)。据我所知,这在全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既是头一家,也是“独一家”。石窟的保护与修复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敦煌研究》将自己的刊文范围拓展至自然科学领域,可谓睿智之举。此外,刊物还根据敦煌学界的研究状况与需要,举办过“敦煌乐舞”(1992.2)、“第一届中印石窟艺术讨论会”(1995.2)、“麦积山石窟研究”(2003.6)、“中国服装史与敦煌学”(2005)等专号与特刊,都在学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迄今为止,《敦煌研究》刊发的文章,已经涵盖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当广泛的领域,充分体现出其“守‘敦’出新”的特色。近些年来,在体制、理念、人才培养、评估体系等等方面,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在大力提倡“创新”。我以为,摒弃“画地为牢”的保守观念,改变“避险求稳”的守旧心理,拓展我们的视野(包括学术视野),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诚然,学术创新不能违背公认的学术“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符合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规范与创新是科学、辩证的关系。总体来说,《敦煌研究》在自己办刊的三十年中,正在朝着符合这个客观规律的方向前行,在遵循学术规范方面也在不断努力之中,得到了学术界的总体肯定。这些年来,在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的评估体系中,有一个被叫做“核心期刊”的名称,而且并非是全国统一,实在也是无法统一的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标准(称为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标准(称为北大核心)、南京大学标准(称为“中国社科引文数据来源期刊【CSSCI】”)。究竟以哪个标准为依据,肯定也应该是见仁见智的,但假若掺杂了某主管部门或负责官员的倾向、好恶,问题就来了。然而,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这个“称号”的影响力可谓大矣,以致全国数以百计的期刊都千方百计地往里“挤”与“钻”——入“围”者喜,出“列”者忧。《敦煌研究》虽有幸“入围”,而且近几年从前两个标准的数据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悉却从“CSSCI”标准中遗憾“出列”。我自己也曾负责过一份全国性期刊的编辑部工作,深知即便是一份很有水平、大有影响力、读者好评如潮的刊物,每一期、每一篇文章的水平,也总是参差不齐的。拿季羡林教授曾经对我讲过的话来说:“每一期有两三篇中看的好文章,我就心满意足了!”即便是最“权威”、“核心”的刊物,也并非每一位作者都是专家大师,每一篇文章都是佳作名篇。至于“引文数据来源”,是应该做具体分析的,如果拿一个时下流行的词汇“正能量”来做比较,恐怕有时“负能量”——负面的奇谈怪论或谬论、伪命题引起的轰动效应会更大些。尤其是一份学术期刊,也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体与“引述者”,是不好与其他刊物作“等量齐观”的。因此,我以为,这个“核心”作何评价与诠释,本身就很难说。《敦煌研究》所刊登的数以千计的文章,同样符合这个道理。我之所以没有将它与《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同类刊物作“优劣”比较,也是这个原因。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专家委员会在每一年度敦煌学奖学金的评审中,非常看重被推荐的研究生在《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上发表的论文,不仅首先注重文章本身的学术水平,而且还关注其发展的苗头与潜力,关心其从事敦煌学研究方向的稳定性。我以为这个做法,值得肯定。现在有些高校或科研机构硬性规定研究生在毕业前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两篇文章就不能进行论文答辩,教师没有在“核心期刊”上亮相就无法提职称等,实在是极不合理的。我清楚地记得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三周年的庆典上,任继愈先生曾当着教育部与一些高校负责人大声疾呼:“谁能首先打破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估体系,谁就是No.1,大家就会跟你走!”我不敢说现行的“核心期刊”评定是否还有某种利益关系,乃至“腐败”的因素在作怪,起码为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计,也应该是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敦煌研究》已经“三十而立”,为这个学术“园地”的百卉葱茏、百花芳菲,编辑部的几任工作人员、编委都倾注了自己的大量心血。从发起办刊的段文杰先生、一直倾心支持刊物的樊锦诗院长,到梁尉英、赵声良等编辑部主任,都值得我们敬仰和赞颂;一直为此刊物贡献文章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尤其是敦煌研究院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也都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我衷心地期待它的“不惑”、“知天命”乃至“从心所欲”,至于是否要如孔夫子所言“不逾矩”,那就要看我们的理解与它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