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词汇的现代性转变
时间:2022-09-28 07:4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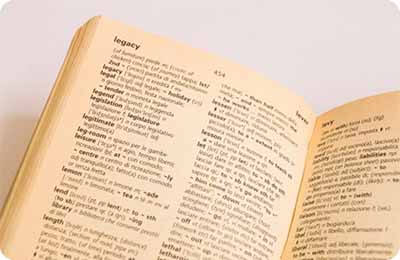
摘要:甲午战争后,日本获胜的消息震惊了中国各界,派遣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书籍等议论如火如荼。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13名留日学生。中国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纷纷翻译日文图书,大批日译新词随之流入中国,对中国文化构成影响与冲击。本文试从日译新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近代学人对待日译新词的态度;词汇的现代性转变三方面展开,对日译新词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日译新词;王国维;严复;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73-03
一、日译新词的流行
后,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汉字数量占“十之六七”的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赴日不久,梁启超即作《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又撰《论译书》,宣传翻译日本书籍的好处。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其中《游学》、《广译》两篇集中论及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的益处。《游学》篇提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广译》篇也极力强调“取径东洋”是学习西方的捷径。
政治见解相左的张、梁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出乎寻常地达成一致,这无疑反应出当时某种时代趋势。明治时代的日文中包含大量汉字,相对于英、法等西方文字而言,中国人翻译日文显然容易得多,日本作为沟通中西的捷径开始受到大量关注。此外,张、梁的言论也表露出近代学人心目中东洋之学与西学的等级关系:从学理的层面来讲,东洋之学不及西洋之学,但从效率、功用的角度来看,学西洋又不如学东洋。
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遣留日学生,此后数年间,科举遭废,赴日留学人数激增。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介绍西方书籍的著作,甚至日本教科书等都纷纷译介为汉语,大量日译新词随之流入中国。所谓日译新词,简单来说,是指近代日本在大举学习西方时借用汉字翻译的西学术语。日译新词虽然在形式上都是汉字,但大多与汉字的传统构词法不同。根据实藤惠秀等人的总结,日译新词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日本人通过组合不同汉字、新创造的词汇,如“哲学”、“说明”等。
2. 中国古代汉语中固有却罕见的词汇,日本人用其表达新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古汉语的词义被改变了。如“科学”在古代汉语中的本意是“科举之学”,日本则将该词用作“science”的对应词,改变了其原始汉译。
3. 十六、十七世纪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知识分子曾合作翻译了一批西书,日本人将其翻刻训点,吸收了其中的汉译词汇。这些词汇在中国长期未见流行,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通过翻译日文的热潮回流入中国。比如“市场”、“民族”等,①属于刘禾在马西尼(Federico Massini)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return graphic loan)。
在追求“效速”的心理以及“和文汉读法”②的影响下,这个时期汉译作品的水平普遍较低。翻译者对日译名词大多生吞活剥,招致很多批评。1915年,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讥讽说:“其中佶屈聱牙解人难索之时髦语比比皆是。”该书作者彭文祖③尖锐批判了带有“日本语臭”的中国翻译。不过,他所攻击的五十九个新名词大多变成了现代汉语常用词,比如“取缔”、“积极的/消极的”、“目的”等。
相对日语原文而言,当时的翻译几乎全是“直译”,汉语译文中夹杂着许多日译新词,由于国内读者对这些新词的涵义不甚了了,译者遂附加冗长的注释,一系列解释日译新词的词典也应运而生,比如汪荣宝等人编的《新尔雅》(1903年)等。日译新词的大量引入对汉语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词汇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进而为现代汉语的生成打下了基础,具体影响表现在双音节、三音节甚至四音节词汇空前增加,改变了以单音节为主的中国传统词汇,其中尤其是抽象名词数量激增,前缀、后缀式构词法变得普遍,比如“性”、“化”、“的”等等。同时,动补结构的新词大量出现,如“扩大”、“加强”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不符合中国传统构词法的新词汇,比如“手续”、“取缔”等等。
二、近代学人的态度
针对日译新词大量涌入中国的问题,近代学人的态度十分复杂。以下拟选取张之洞、梁启超、严复、王国维为代表,考察近代大批日译新词进入中国后,在知识界引发的震动。
1905年,张之洞负责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申明:不准乱用不够“雅驯”的日译新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杜绝使用日译新词,在张氏本人的《劝学篇》中,“代数”、“牧师”等新名词赫然在目,原因是对于传统中国所无之物,如果不用新名词则很难表达。张之洞的态度表明,清末部分学人注意到日译新词对汉语系统的威胁,本能地予以抵制,但由于古代汉语体系不足以应对大量新事物,再加上耳濡目染的“习得”力量,他们仍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汇。从根本上说,这反映出以往稳定的词与物的对应系统在外界影响下发生紊乱。张之洞对日译新词的抵制还反映出在中西碰撞的时代主题下,晚清学人的心理落差巨大,他们虽然依恋并维护古代汉语体系,但却只能为其吟唱挽歌。无论如何,以“雅驯”与否作为接受或排斥日译新词的标准的确缺乏说服力。时任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的服部宇之吉就曾援引唐代译经的例子加以辩驳,说明“雅驯”的标准并不是本质化的:“然学术欲随时而进步,学者随事而创作新语,亦势所不得免也。创作新语,中国不乏其例。……即唐代玄奘等译佛典亦多用此法。……玄奘等所创作之语,在当时未必皆雅驯,而今人则不复问其雅驯与否。由是观之,语之雅驯与否,毕竟不过惯与不惯而已。”④
日译新词流行中国,梁启超应属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使用的重要术语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日译新词。除了动笔翻译以外,他还将新词汇和日本文体风格融入文章当中。然而,梁启超本人对日译新词并非全盘肯定。比如,他在《释革》(1902年)一文中指出日本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当:“革命”一词出自《易》、《书》,携带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意义,与“revolution”在英语中的意思不尽相符,梁启超建议改译为“变革”。梁启超把日译新词放在古代汉语传统中进行考察,由此提出的批驳意见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个人的提议在时代大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后,梁启超本人也接受了“革命”一词:在两年后成书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俄罗斯革命之影响》等篇名。
相比之下,严复的态度更为明确,他坚决反对日译新词,并通过翻译实践自创新词。从1895年《天演论》到1909年《名学浅说》,严复反对移译“东文”,主张自创新词,用文言译西文,而他自创新词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自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他看来,要领会西学的真谛必须学习西文,不应借助日本的媒介;同时,日译新词破坏了汉语固有体系,不值得提倡。翻译时,严复总是竭力从古汉语中找出与西文对应的词汇。比如《与梁启超书》一文中,严复解释了他如何把“economics”译为“计学”:首先考察“economics”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原初意义,然后再返回古汉语中,找到与“economics”古意对应的词汇“计学”。尽管“economics”在现代英语中的含义已变,“计学”不足以概括这一词汇的现代内涵,但如此翻译能够确保“不隔”,胜过日译“经济”。
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批评严译过于古奥,严复反驳说:“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严复的目标读者正是“多读古书”的学者。尽管严复选取的译名大多没有保留下来,比如“logic-名学”;“evolution-天演”;“librarian-秘书监”等,但它们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翻译沟通古代汉语与西方文字,打破中西传统之间的隔断,显得弥足珍贵。当然还应注意,严复师从桐城派吴汝纶,同时又有留学英伦的经历,他所受日本文化影响甚微,使得他的观点有别于梁启超等留日人士。
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王国维对该问题的见解颇为独到,值得详细分析。王国维的态度集中体现在1905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该文开门见山,指出“新语之输入”是近年学术界“最著之现象”。语言和思想之间联系紧密:“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之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这一观点与前文严复所谓“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颇为神似。语言是国民思想的表现,中国人重实际,西人尚思辨,因此西人“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擅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比较而言,“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翻译过程最容易凸显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王国维认为文化差异决定了语言的差异,但他也注意到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与王国维不同,清末主张采用日译新词者大多持语言工具论的观点,认为语言只是媒介。王国维对语言的思考超出了“文以载道”的观念,他认识到语言对思维、观念的反作用,语言即“事物之名”,在概念世界中,人们依赖语言而思考。
语言是思想的表征,因此“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这个看似简单的过渡揭示出,言语不仅仅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它几近于思想本身。王国维将时人对待日译新词的反应归为两类“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两种态度都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增设“新语”的目的不是为求新奇,而是为解决“言语不足用”的问题。王国维据此分析严复的翻译,指出部分严译新词并不恰当,虽然古雅,却失之含混,比如将“space”译为“宇”,将“time”译为“宙”,就犯了“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的毛病。王国维承认,日译词汇有时不够精确,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之而废,因为借用日译词汇不但更为方便,而且更能促进中日学术和思想的交流。概言之,王国维认为,借用日译词有两点好处:“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格之虞,二也。”
日译新词的问题说到底是语言的问题,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王国维的思考更接近语言的本质,得出的结论也更富有启发。在他看来,翻译是以异文化为参照,对本国夙无之学、夙无之物加以命名的过程,新事物自然应该赋予新名,而既然日本已经确定新名,中国何妨拿来一用,如此不但省时省力,还便于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张之洞那种“欲罢不能”、复杂纠缠的心态不同,王国维在论述此事时体现出反躬自省的明察,反映了大学者的胸襟。日译新词能够在汉语体系中扎下根,直到今天仍然广为使用,大概就在于王国维在这里所点明的两条益处。
三、词汇的转变
翻译是在旧有的语言系统中为新事物命名,并确立新词汇在该语言系统中的秩序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会与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发生关联。在现代汉语生成的过程中,翻译功不可没,而日译新词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包含能指/所指、隐喻/转喻、内涵/外延等多重关系的符号系统,能指在其中通过自身的差异性获得意义。据此,能指的迁移未必伴随所指的迁移,翻译不是地在异文化、异语言中单纯寻找对应词,文本在翻译中不断被替补、被更改。日译新词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对西方术语的翻译,当日译新词大量涌入中国汉语系统后,势必会给固有的汉语系统造成混乱。近代中国汉语系统中的能指、所指数量极大丰富,能指相对于所指数量过剩,加剧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混乱。总之,一方面,日译新词的确丰富了汉语系统,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并影响了汉语的文体和句式表达,促进了汉语的现代化转型;另一个方面,日译新词的输入也干扰了汉语固有系统,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汉语系统的混乱,对日译新词生硬的移植,也割断了汉语本身的连续性,使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错综纠缠。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到“词汇”之变与“语言”之变,并以此为标准确定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质变。日译词汇在中国的流行与传统社会的瓦解同步,词汇方面的剧变不仅反映出、而且实际上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语言”的变化。近代历史中,日译新词曾如鸟群般迁徙到中国大地,其中大部分在今天的汉语系统中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当这批词汇在清朝末年与中国学人邂逅时,它们曾被指认为“新词”,但在现代中国人眼中,它们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常用词。这说明,昔日的日译新词早已演变为中国汉语的另一种“传统”,一种活生生的、向未来延伸开去的传统。
社会语言学发展规律表明,语言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渗透,近代大量日译新词进入中国便体现了这一规律。中国学习日本主要目的是以日本为媒学习西方,日译新词原本又是日本借用汉字对西方术语的翻译,从这种纠结缠绕的关系中,我们注意到近现代汉语在中国-日本-西方互动的大背景下生成,其中反映出语言交流所受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影响,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注释:
①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p.318;另见Federico Masin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1898, Rome: University of Rome, 1993, p201.
②据称由梁启超所创。这是一种学习和翻译日语的速成方法:首先找到日语句子的主语,然后从句尾找到动词,最后再回头阅读句子的宾语。根据这种方法翻译出的汉语,虽觉生硬,但句子结构已接近中文,句意也不难领会.
③原书署名“将来小律师”.
④转引自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2]实藤惠秀著.谭汝珍、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
[3]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东京:帝国印刷株式社会,明治37年(1905年).
[5]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评.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6]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
[7]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8]Lydia H.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9]Federico Masin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1898, Rome: University of Rome,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