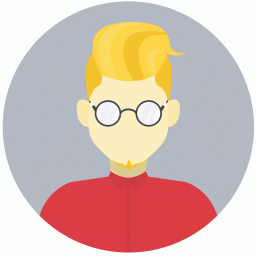“世纪遗痕――应天齐艺术展”学术研讨会
时间:2022-09-06 04:00:40

王林:
应天齐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而且我觉得他的创作状态和思路跟我批评的思路比较吻合,他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艺术家,并不是体制的主角,也不是江湖的明星,一直是处在比较边缘和相当个体的一种状态里边持续地在自己的创作思路当中进行艺术的探索。易英说他是“温和的前卫”,我说他是“匍匐前进”,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其实我们从八十年代以来,不管是从批评的研究也好、美术史的写作也好,应该去做一些在这样的历史经历当中一直持续地进行个体的艺术探索,而且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去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创作过程、去仔细地阅读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中国批评界和中国艺术界还是显得过于的宏观叙事、过于的大而化之,其实我们很少真正去细读一个艺术家,真正有耐心去细读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甚至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其实我们的评价也很大而化之,所以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比较有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范迪安:
我非常赞成这个展览的主旨,就是从应天齐的艺术历程看他个人的探寻,实际上同时也看三十年来中国艺术走过的历程。不见得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能够与这个时代的发展结构具有对比的关系,而一些在这个时代里始终坚持探索,坚持对自我挑战也对今天的艺术个体挑战的艺术家才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时代,回应这个时代。
应天齐这个展览中最早的作品是1972年,到今天的确是30多年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是这一代艺术家特别努力又特别经受考验的时期。天齐的特点我觉得第一是十分的勤奋,他有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根本最朴素的品质,所以几十年来他是在一个高度的艺术热情和极为投入的艺术状态中从事艺术创作。他的确是在与时俱进,这个与时俱进既受到外部社会和文化条件变迁的影响,也有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文化动力。是不断地在这个时代把艺术当做一个思想的载体,所以他的艺术是提出问题的,是不断的关注社会现实同时也关注他自己心灵历程的成长。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能使自己的心灵体验和心路历程与这个时代结合在一起,他的艺术就可以提供我们更多值得琢磨研究的东西。第三,应天齐的确在自己的艺术发展中找到中国当代艺术特别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中国的现实作为创作的资源,而同时又创造出当代艺术的当代内容,文化中的当代属性,我觉得应天齐在这方面的关切特别在这个展览中我觉得体现的非常深度的精神关切。而且找到了跨越传统、媒材和语言的表达方法。
我不能在这里发表更多研究性的思想,只能从我对这个展览的初步体验中感到了艺术既要有视觉革命式的成果,更要有思想的深度。而天齐作为我的艺术家朋友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彭德:
应天齐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近三十年他从木刻版画到绘制同类风格的油画,到从事同类形象的装置、行为和影像,始终没有停息过对艺术语言和内涵的追求。他是将对立的因素统一且万变的高手,比如“怀旧情绪”和“现代意识”,“阳刚气派”和“阴柔作风”,细腻的文饰与机理配以单纯的色块与强劲的轮廓线。应天齐底下那些宽窄不同的横立块面,不同于蒙德里安的构成观念,同样他画机理画的不是质感而是时间,是历史的沧桑和磨难。应天齐一直患有抑郁症,那是厌倦人世的心理反应,他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无人之境,他不动声色的画面使得历史的遗存显得冷峻。画面中反复出现的黑色块面隐含着历史和现实、晦暗以及封建文化的刻板和体制的僵硬。
应天齐曾定点拍摄芜湖老城区的拆迁建筑,在拆迁一周年后将影片投射到废墟的墙面上,变成装置状影像作品,暗含着对现实喧闹的拒绝和对往日宁静的怀念,这一切都表明他没有走出西递情怀。应天齐也将离不开西递,这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初恋情结。
邓平祥:
我现在就谈一谈看了他的画以后两点比较深的感受:
第一,应天齐对“历史主题”和“怀旧主题”的表达是成熟的,在文化上成熟和精神上成熟的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和怀旧,对我们原来要过去的历史中间一个东西的一个非常复杂和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我想谈一下他的形式主义。我刚接触到应天齐的艺术认为他就是一个形式主义,但是这个“形式主义”,我感觉我们今天来看应天齐的“形式主义”不是当年提出来的“形式美”的“形式主义”,很不简单地是他那个“形式主义”,比那种当年的“形式美”的问题的提出要丰富得多,并且是更接近艺术的本体。尤其是视觉艺术的概念提出来以后,每一个艺术家首先都应该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还有他的形式激情。彭德刚才评应天齐就是有某种抑郁性,他这个抑郁在作品中体现得生动、激情,这对一个艺术家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在形式上的一些表达特征就使应天齐的艺术达到了形式的内容和题材内容的整一,他是不可分的,这应该是一个造型艺术家或者是视觉艺术家在本体上应该达到的一种比较高的境界,谢谢大家!
徐虹:
我和应天齐也算是比较久的相识了。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西递村系列》,十年前那次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尤其是《碎裂的黑色》那些作品给我的震撼很大,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在形式上比较讲究画面的结构,这种结构又以一种比较柔和的,不刺伤人眼睛和心灵的,大家看了以后都会陷入一种瓶颈之中的,静静的审美的一种形式。像这样一位艺术家要把他的画破坏,那倒也可以,因为作为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在当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从黑色中走出,不失为当时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一种表现方法,但是使我非常惊讶和使我非常不安的是他把砸碎的黑色又拼贴起来,由砸碎的黑色的裂纹组成了一种美丽的有节奏的现代主义的线条,这个作品还在,今天又看了,我的震惊不亚于当年,我继续为他所震动。这说明什么呢?从某一个角度象征着中国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和现代主义的传统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他纠缠于过去,不能完全自拔,向往于大踏步的前进,但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他现在身在何处,现在如何做都是一种不确定的和犹豫的摸索状态,这种状态恰恰说明中国现代主义的道路,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非常地丰富、非常地复杂、非常地矛盾。这种丰富性、复杂性、矛盾性恰恰组成了他作品的张力。
如果我们抛弃一切现成的关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模式来讨论和解释他的作品,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从作为一个中国的历史语境里边,我们来探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来探讨中国艺术家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语言到目前的状态,我们想他的作品提供给我们很多可以可讨论的空间。
尚辉:
闭起眼睛来,我想应天齐给我最深的印象应该是两个:第一是他的水印版画《西递村系列》系列,或者是也因为他的版画《西递村系列》在中国八十年代版画史上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第二,应天齐本人,尤其是他的眼神,刚才有很多评论家描述了他的眼神,那种忧郁的、深沉的那 种目光,就是他走了以后,你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眼神。
应天齐是大家经常会谈论的一个话题,从版画家的角度来说,他已经脱离了版画群体进入了更广阔的艺术领域探索。就当代艺术家这样一个领域来说,实际上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很多种很多个个案性的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但是我相信今天在这里所举办的展览,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个案,可能更能够为我们同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鸣。我相信为什么这样?就是他所走的一条路线是从传统、从架上艺术一步步演化过来的,这个展厅里所展示的他的艺术的脉络几乎可以概括出我们从七十年代到今天,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所以他的个案就有我们今天艺术发展艺术史的浓缩性。
郑娜:
我注意到展场中间的几幅作品,一幅是《无极》,一幅是《厚黑》,还有一幅是红色的《王者》,这几件作品,应该是近作。他跟我说通过这几件作品一下子打通了,我在想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打通了什么?是打通了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对形式的敏感,还是打通了这次形式美感对他另外一种反向的作用,我想这个对于应天齐来说,他是属于一种个人个体充满个性与探索精神的视觉感受。我想大块的黑、白、红在这个场域中间显得特别突出,他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就是跳离了具象的或者是传统的符号化的指征。从另外意义是一种走远。
刘骁纯:
王林的前言实际上说出了大家要谈应天齐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当代艺术能不能不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应天齐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从自己的性格和心理出发来延续他的发展序列,展开他的发展序列的一个艺术家,这样的一种情况就非常特殊,这都是他自己心理路程,不被西方说的很多当代艺术限定,根据那样的理论去做这么简单。我想这是大家关注应天齐,也希望从他那儿能找到一些东西的原因,因为他是从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心理历程来导引自己创作,他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内核,这个个性内核始终贯穿如一,所以他走出《西递村》以后,这个西递村的幽灵还会回来、砸碎黑色以后这个黑色的幽灵也还会出现,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出现,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个性化的指向,有了一个内核,当然这个内核将来可以发展成什么,还是有很大空间的,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大化的理性,他的理性很张扬,从他的《西递村》到《走出西递村》到《砸碎黑色》一直到他现在的艺术,这个理性非常清晰,跟他的人格也完全一致,他就是把理性神圣化。
第二,计划中的感性,他这个感性和别的理性不一样,是受理性强制控制的,所有的感性都是他计划当中的,就是他设计出来的,这种感性不是放任的,所以你看他做的戏剧里头也有很多很随意、很飘洒的表现,这些都在他整体的设计当中。
第三,多虑的当代性,这里头多虑本身又使他走走停停,走出来就回来,他又走不出去,砸碎黑色也迈不出去,他还有很多矛盾,比如他的很强的反学院性,但是你看完这个展览以后会感觉到强烈的学院情结,跟这个相一致的就是强烈反经典色彩和最后严格地回到经典,就是经典是他的一个情结,放不掉。
杜曦云: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今天对应天齐先生近作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与应天齐先生当时很具有震撼力的代表性作品《西递村系列》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纪遗痕”这个展览之中,他把他在社会现实中的体验和思考进一步地形象化了,以往在《西递村系列》过分具象的语言痕迹在一点点地淡去,进一步形而上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他的独特价值是什么?他并不是走向一种所谓的直白或者是纯粹的观念艺术,他始终是一个用视觉来进行思考的艺术家,换句话说,他注意到在艺术创作本体的重要性。正因为是对于艺术本体的重视,他是非常谨慎、审慎的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一种偏于当代性的观念,这里面强调的是要在具象性之中体现出一种抽象性,和大量地运用现成品或者是模仿现成品的痕迹。
另一个就是要在一种高度物质性之中体现出一种精神性,这样导致他的作品让他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的分寸感来,当然这种分寸感,一方面体现他的控制力,一方面也是体现了刚才几位批评家都共同地谈到他的作品的矛盾与复杂。我个人的感觉,他对于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一些所谓的成果,他是非常审慎地来吸收和提纯,再一个用他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非常本土化的经验,以及他作版画语言的东西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中的一种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王端廷:
看应天齐的作品对他这个人的性格我有一个感觉和把握,就像刚才大家都谈到他的性格和眼神,我看到他的作品,感觉这个人是非常细腻、非常缜密的一个人,他可能是内心世界波涛汹涌,但是他的发表却是一个静如止水的人,你看他非常细腻,以至于他把当年的听劳森伯格的展览笔记作为一种文献来做,这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应天齐艺术中所体现的美学,那种东西恰恰是我们现代艺术中革命的产物,当代艺术再次回到美的殿堂,这是整个世界当代艺术一个总的大的趋势。如果说是我们一定要给应天齐的艺术风格给一个标签,我愿意用“观念现实主义”,首先他的艺术语言是观念的,他用他的观念语言表现了一种现实,是一种现实的图像,不是抽象的,他对我们我们这个巨变时代的文明、生命的命题进行了自己非常深入具有个性的思考。
岛子:
今天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应先生的作品,看到了他在四十年中对现代主义精神,对当代艺术的意象,这样一个方向中进行实验的艺术家,构成了很多话语,构成了很多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样的个案在批评的工作,特别是所有中国当代性问题遇到了很复杂资本化的沼泽地的时候,显现出非常的价值,我们回头看85、八十年代过来现在还在坚守的一些独特的艺术家是非常必要的。刚才王端廷谈的从应先生的艺术风格、文化探索、文化立场上看分析得很到位。在我看来像应天齐这样的艺术家不能再冠以艺术主义者的标签来看,比如他从35岁开始一种现代主义的学习,他已经转向了个体经验性的一种表现,在这里我觉得这种个体的经验的宝贵,个体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的一个历程是何等重要,我们从比较的文化学、历史学来看这些问题,特别是“奥斯维辛”之后可以比较中国的“”,这种对历史的、苦难的追索,我认为在中国当代性里边是匮乏的,这也是当代艺术缺少精神性的一个维度,就是历史价值,历史价值也是历史观,同时也是世界观,这些可能都是整个当代艺术批评、艺术理论建设、创作要面对的一个话题,应天齐的作品为此做出了回答。
杨卫:
我主要说一点,我们知道应天齐先生的作品主要是从《西递村系列》之后发生了一个转折,也就是说他的艺术成熟是通过《西递村系列》往后的一个不断的发展。这批作品是出现在八十年代末,我印象当中八十年代后期一些版画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带有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是出现了版画艺术整体倾向带有一种形而上、超现实主义的特征。但应天齐及作品为什么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它区别于当时85以后一种闹哄哄的环境,突然间出现一种很静穆、很肃然的感觉,开始走出一种超现实的或者是把这样的一种印象通过视觉提高到一种抽象的层面,我说的是视觉的抽象,也就是说他提供给我们的视觉让我们对我们自身的文明也好,对自身有一种膨胀,我看了展览之后知道应天齐先生有很多路,比如说这个展览之后应先生怎么走或者以后会提供我们一种什么样的视觉特征,这也是我特别期待看到的。
从整体而言,应先生这几十年的一个艺术脉络来说,他提供给我们一种文化的凭吊,而且在这个领域应先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