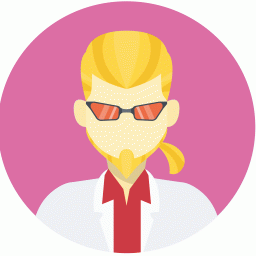我与杨浦 第1期
时间:2022-07-11 08:30:22
一、凤凰村
我与杨浦,说来话长。
我与杨浦区的关系,不是从1978年进复旦大学读书开始的。我进复旦的时候,复旦还属于宝山县五角场镇,属于郊区城镇户口,所以我就没有将上海市区的户口转到学校去。我与杨浦的关系是从1966年开始的,那一年“”爆发,我搬到了杨浦区宁国北路(现恢复旧名黄兴路)控江路交叉口的新村工房,名曰凤凰村。
上海的新村建筑群有个变化的历史。1949年以后,最初市政府是在沪西地带盖起了一片简易的两层楼房,每层楼十户人家。两端各有一套公共厨房和厕所,以解决流浪在城市里无处安身的贫困家庭。这类房子是砖木结构,冬暖夏凉,房间都比较宽敞,一间房里同住着祖孙三代也是常有的事。老居民把这类房子叫作“两万户”,我当时年纪还小,只是跟着这么称呼,却没有探问过这“两万户”究竟是指最初建成的这批房一共有两万幢,还是解决了两万户人家。1950年代末上海人口剧增,对住房的需求急剧上升,这类新村随之增多,房型也不断改变,一般是三楼或四楼,斜顶青瓦,用红砖或青砖盖成,厨房和卫生设备都比较齐全,三四户人家合用。上海市区的四周近郊布满了这样的新村建筑:南有日晖新村,西有曹杨新村,西北有甘泉新村,东北有长白新村,北面稍晚还有彭浦新村,等等,成为当时上海城市建设的一大景观。到了1960年代中期,工人新村的提法慢慢减少了,原因是居住者的成分复杂起来,许多干部和职员也都纷纷搬迁进来,房型和建筑材料又发生了变化,那时通常使用钢筋水泥结构,平顶五层。房型变为一个个小单元,每一单元内两到三间,合用一套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些住房条件较好的一家可以独占一个单元,开始有了“独门独户”的概念,比较接近现在的多层建筑。为了区别旧式的工人新村,人们把原来的建筑叫作“老工房”,这类新型的新村房子叫作“新工房”。
我在1966年搬进杨浦区的“凤凰村”,就属于这类新工房。但“凤凰村”并不是新村小区的名字,而是附近一家饭店的招牌。因为那几幢楼房不属于任何新村,只是独立地矗立在马路边上,无以名状。当时人们都习惯用新村名来称呼住宅,就将近处一家饭店的招牌作了它的代号。那时的杨浦区是工业区,有大片的工厂盘踞在马路边上,居民住宅点不多,商业网点也不密集,我住的那片地段可以算作商业中心,除了一般的商店邮局外还有个文化馆可以放映电影,也有一家小型的书店,这比起我原来住的虹口广中新村还算好一些。
我家住的是一个小单元,两间并排的卧室,右面是厨房,左面是卫生间,显得很有派头。那时还不时兴“厅”,房间面积大一些,吃饭会客睡觉都在房间里,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那套房是我母亲工作单位交换来的,据说本来该给一个什么长的,那个什么长嫌面积小,没要,我母亲考虑到我们都长大了,长期寄住在外祖父家也不够住,而她自己的住房自从我父亲去西安后一直空关着,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所以就提出两处换在一处,搬到了遥远的大杨浦。
那几幢楼房的居民以处长科长级别的干部居多,“”刚开始,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首先倒了霉。那家家长姓方,是个银行的退休职员,两个女儿都是社会青年,没有工作,但长得很漂亮。那时社会青年没有考上大学,都必须到农村或者新疆去,留在家里是被人看不起的,仿佛低人一等,任何小孩都可以跟在他们后面唱“社会青年别老卵,老卵要到新疆去……”这样污辱性的“歌词”。但可能是教育背景不同,那方家很讲究生活情趣,譬如家里放了个外国女人的石膏雕像,小孩见了人,不叫叔叔叫“UNCLE'’,等等,在那个时代都是很犯忌的。尤其是在工人新村里,半大的调皮孩子常常聚集在新村路口,凡看到打扮入时的女人一律叫“野骚鸡”,看到谁家装饰洋派一些的,就骂“资产阶级”,表示深恶痛绝。所以“八一八”(指1966年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编者注)红卫兵运动一起来,同楼的一些干部子弟立刻就上方家的门,去“破四旧”,他们把那两个女儿拉出来“斗争”。所谓“斗争”就是强迫她们站在太阳底下,听任别人对她们的辱骂和小孩向她们扔泥巴,逼她们把一些式样时髦的衣服拿出来烧掉,“斗争会”一直开到那个大女儿被吓昏过去,那些自封的红卫兵才心满意足地在她们家门上贴了一张“勒令”,大获全胜似的回家了。从此以后,几乎天天有小孩上门来丢石子泥巴,我家因为与方家就挨着门,常常被殃及池鱼,砸破玻璃。无理性时代的野蛮风气,我最初就是从目睹这个事件后种下了印象。
不过,对“”的恐惧则是由外祖父传给我的。现在回忆起来,外祖父真是个极其智慧的老人,他博古通今,谙熟历朝掌故,但现实处世却极为谨慎。我曾听他说过,1957年大鸣大放,某单位曾请他去开会,要他给政府提意见,他去后,见别人都说政府这不好那不好的,轮到他说话时,他就说他没意见可提,如一定要说,那就建议政府可以在马路边多种些树,搞些绿化。结果那些提意见的人都被打成“”,他却安然无事。不过后来又听他说起这件事时,他没有说是他自己,只说是听来的。“”一开始,他就拿了的照片反复看,看后自言自语地说:原来以为是个吕布,结果是个李儒,看来是不长的。我小时熟知《三国》故事,知道吕布是董卓手下的猛将,而李儒则是个谋士,“凤仪亭”一出戏里李儒是小花脸,他劝董卓将貂蝉送给吕布以收买人心,董卓恨恨地骂,你怎么不把你妈送给吕布!李儒就仰天长叹:我们完了。外祖父这个比喻,我一直闷在心里不敢说出去,到1971年摔死在蒙古时,外祖父已经患老年性精神分裂,不再操心这些事了。老人晚年对时代充满恐惧,几乎是足不出户,先是在家里把一些旧时的照片、图书和他长期做下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手稿全部烧掉,后来渐渐的连家里的事情也不大管了,像只地洞里的老鼠那样惊恐万状地生活着。
于是,才14岁的我就不得不担当起家里的“主管”任务。那时学校里闹革命,斗教师,搞武斗,外祖父坚决不让我到学校参加任何活动,“他们是不长的”,他反反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反正也闲着无事,妈妈就把每月大约60元钱交给我,由我来负责开销这个家,上有外祖父和外祖母,下有两个妹妹,一家的柴米油盐酱醋和三顿饭菜安排全要管。我人小,管不过来这些琐事,外祖父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准备许多空火柴盒,上面分门别类地写了“房租费”、“水电费”、“菜金”等,里面放了相应的钱,按月支付,到月底各个盒子全空了,就算收支平衡。
那时父亲在西安被隔离审查,经常一两个月没有信来,母亲心里暗暗发愁,在外面还要装得无事一样,老人们一天天衰老,而我,就在那个独门独户的单元里悄悄地长大。
二、邻居老方
家住杨浦的那四年,是我的人生成长经历里最难忘的四年。1966年我在12岁到13岁之间,1970年我是16岁到17岁之间,是整个青少年时期转型和完成的过程。在我的记忆里,我住别的地方的时间都长于四年,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段大杨浦的经历。电许是一个人最刻骨铭心的感受来自他的青少年时期。
我在前面提到一位姓方的邻居,那个家庭的悲剧性遭遇是我对于时代和人性的最初认识。这以前,我还是一个孩子。
只有到那一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头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街头到处涌现出自发的中学生组成红卫兵进行“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革命”的感受才变得直接了。孩子天性都爱热闹,天上突然掉下个大自由,可以无法无天地满街奔跑,看见穿着时髦的青年男女就冲上去指着骂“资产阶级”、“流氓阿飞”,看着他们哭丧着脸求饶认错、抱头鼠窜的尴尬洋相,或者被中学生剪了裤管,剪了头发的狼狈不堪的样子,都会被刺激得兴奋莫名。但是我对这种活报剧的兴奋几乎没有延续几天,因为就在一开始的几天里,邻居老方家两个娇滴滴的女儿被拖到大门口被围攻和批斗的场景,让我倒了胃口。对于街上不认识的青年男女的遭难我或许有点兴奋,但一旦灾难降临到平时关系很好的邻居头上,我再也兴奋不起来,反而感到了恶心。
让我继续感到恶心的悲剧还在继续发展下去。老方是个退休的银行职员,平时一举一动在我们眼里很有派头。他退休后参加里弄居委会工作,这种工作本来就是义务的,但也算是基层的权力机构。老方性格有些方正严肃,有一次带了人来检查卫生,我外祖父自夸说,家里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是经常洗刷的,不用检查。老方当场就指着白瓷马桶里一块黑斑说,这不是脏东西吗?弄得外祖父下不了台。但过了一会,老方带了洗刷工具又跑来,帮着外祖父洗擦,结果发现是一块瓷掉了,老方才道歉,承认是他看走眼了。外祖父对这样一个银行职员热衷里弄工作很不以为然,他虽然长期无业在家里,但除了去领什么粮票肉票以外,是坚决不参加任何里弄组织的活动的。
大约是过于较真的性格,加上他有文化、懂英文,整天与那些婆婆妈妈的家庭妇女一起搞里弄工作,难免会发生龃龉。私下的矛盾是早就有了,与他对立的一派中,有一个湖南籍的妇女,丈夫姓唐,是一位老工程师,家境也是不错的。结果退休银行职员与老工程师的太太较劲了。据说,那天煽动红卫兵来抄家、把老方的女儿当作流氓阿飞批斗的幕后教唆人中,就有那位唐太太的份;但是不久,老方的报复机会来了,那位唐工程师在单位里也被揪出来了,遭遇了批斗。老方闻风而动,连夜组织人轰轰烈烈地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唐太太在里弄里的“言论”。那天晚上他急吼吼地跑来找我外祖父参加写大字报,被外祖父一口拒绝。外祖父很有心计地对他说:老方啊,我们是隔壁邻居,他们说你不好时,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你让我揭发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唐太太,她的罪行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知道了不就成了同谋犯?我记得那天老方激动得满脸通红,连老花镜都忘记戴了。
问题就出在老方没有戴老花镜。他老眼昏花地写大字报攻击唐太太,却没有注意到,当时写大字报用的全是旧报纸,而那时候的任何一张报纸上都印了各种图案的领袖像。他在一张领袖头像的背面写了“诬蔑”两个字,这两个字正好写在领袖像的脸上。第二天大字报贴在门口墙上,马上被人发现了:老方犯了“诬蔑”领袖罪!以后的情况我已经忘记了,反正老方三天两头被带到红卫兵那里去审讯,连带了两个女儿也经常被哭哭啼啼地带去审讯。“红卫兵”其实也只是“中学生”而已,他们审讯人感到好玩,尤其是“审”那些漂亮的女人,这件事好像并没有公安机关插手。后来红卫兵忙着自己学校的争权夺利,事情也不了了之。但老方全家则一蹶不振。
又过了几个月,老方一家突然搬走了。那时候搬家都是悄悄进行的。前一夜老方和他的女儿突然上门造访,告诉我们搬家了,就此别过。他们是与一家住在徐汇区安福路的医生交换住房。那时的住房都是租赁的,可以自由交换。对方那家的主人是一对医生夫妇,在杨浦区的医院里工作,他们换过来,工作单位就近了。而老方一家似乎是为了摆脱杨浦的厄运,希望换到市中心“文明”一些的上只角去平静地生活。那天老方的小女儿情绪很好,天真地说:“那里淮海路上的风吹着了也是香的,不像这里,一开窗就是灰尘和臭气。”这话也不假,当时我们住房边上就是上钢二厂,一路都是废气和金属粉,相传是有毒的。
老方搬走以后,我们两家起先还有些来往,但后来慢慢就失去了音讯。外祖父他们说起老方,总是说,像这种人家,还是住在“上只角”比较适合些。此番搬家,也是得其所哉。但是,大约一两年后,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张贴着上海市公检法革委会审判犯人的布告,上面印着一连串的犯人头像,这种布告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人们也习以为常不甚关注。但这一张布告里,赫然有三个我们熟悉的名字:老方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罪行是组织叛国外逃集团,被破获后,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但也好像判了十几年。
三、做父亲的人
邻居老方的故事,是我少年时期关于“”上海的第一个记忆,其实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只是我年幼无知,毫无社会经验,初次遇见这种家破人亡的惨剧未免目瞪口呆,悲哀中人生开始有了精神阅历。当然这种精神阅历是一种复合型的成长,并不是单单遇到了邻居家的惨剧才发生的。究其更为隐秘的原因,是我自己家庭里也正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磨难。记得在1966年8月以后的几天里,母亲变得特别不安。原因是有关我的父亲。
父亲在西安工作,一年回家探亲半个月,来去匆匆,总是不停宴请会友,旧雨新知川流不息,不是出去应酬,就是在家里醉醺醺从中午吃到晚上,酒菜余韵数天绕梁不去。反之父子间个别交流极少,好像本能里父子之间互相有些排斥。举一个例子,我的大妹妹和小妹妹都分别去过西安小住,得到过父亲的直接照顾,而我则从没有去过。每次父亲回来,与母亲住回他们自己的居所,那是在四平路上的一处工房,他们经常带我妹妹一起回去,但从未带过我回去享天伦之乐。所以父亲在我的印象里非常淡漠,非常遥远。这种感觉很早就发生了。我后来无意中读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亲刚去西安支内时给母亲的信。那是一封普通的家信,里面谈到了对我的教育,父亲还特别l叮嘱了一句:“对阿和(我的小名)的教育要多费心,特别注意改掉坏习惯。”我算了一下,当时我大约两岁半。不知道坏习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那时候已经需要他特别费什么心来教育我。随着岁月的推移,父亲也没有特别关注过我的教育,他好像把教育我的工作完全放弃,把权利和责任都交给了我外祖父去打理。但他
又似乎对外祖父给予我的影响不很满意,或者说根本不满意。我中学毕业没有上山下乡,在家里当一个闲散人员,这是很不符合他的期望的。但他从未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甚至也没有怎么过问我的毕业分配诸事,完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父亲的职业也很奇怪。在过去读小学开始就要经常填写表格,每次填写总是有父母的名字、成分、单位等内容,父亲的成分是店员。“店员”这个成分类别在“”中被取消了,之前是有的,我外祖父的成分也是店员。店员成分好像是比产业工人低一个台阶,比一般公司职员又要“革命”一些。我父亲本来的职业是教员,也做过都市小报的编辑,后来在一家私人饭店里工作,从事设计宣传工作,公私合营后大约因为追求进步,被领导看中担任了公方经理,他自以为是干部。在1955年上海有关领导要求上海服务行业支援大西北城市建设,他积极带头把一家大饭店迁移到西安,那是西安第一家来自上海的粤餐馆,曾经显赫一时,后来渐渐衰落了,父亲也因为与当地北方干部意见不合,被几次调动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店员”=我的父亲身上始终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与这个时代总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从主观上他是一直很自觉地在追求进步,追求与时代步伐的合拍。这一点他与我的外祖父很不一样,也许是在这种裂缝中,他把我看作了外祖父培养的人,他是不以为然的。
“”爆发以后,他也自身难保了。我不太了解他在西安的处境,但母亲是清楚的。我母亲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出去做童工养家活口,那是在沦陷区的上海,外祖父声称不与日本人合作,就躲在家里当闲人,当时家里房产早在“一・二八”轰炸中化为灰烬,一贫如洗,于是母亲就出去工作来养家。她与父亲结婚后生活条件才改善。父亲支内以后,她被安排在一家局级单位担任电话接线员,成分算是技工,按理说,没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但是母亲对于单位里发生的阶级斗争发自心底害怕。有一天她回家,一声不响地开始清理父亲的旧书柜,我第一次发现旧书柜里堆满了纸张发黄的剪报,大约都是父亲当年编小报时的积累,里面有父亲写的文章,用的是笔名,都是一块一块的豆腐干文章。母亲开始处理这些陈旧的报纸刊物,先是她把自己关在厕所里,用火烧报纸,然后把灰烬倒进抽水马桶用水冲掉。后来发现这样会有烧纸的焦味传出去,于是她又把这些报纸放在水里,像洗衣服一样,把纸搓烂,再放到抽水马桶里销毁。――所有这一切都做得神秘兮兮,母亲不要家里任何人插手,一切都由她自己来完成。终于有一天,她突然把家里人召到一起,告诉我们说,她单位里已经有人在议论我父亲的情况,很可能会来抄家,她要我们保持冷静,抄家的人来了千万不要争吵,要拍手欢迎他们,除了背诵语录外,什么话也别说,等等。乌云压城城欲摧。母亲说她无所谓,她的一切都是父亲带给她的,现在也因为父亲而被拿走,大不了她离开单位,到基层去工作。外祖父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外祖母直流眼泪,妹妹还懵懂无知,而我,正处于刚刚懂事的年龄,有点兴奋有点紧张地期待着一场噩梦降临。
结果那个噩梦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年父亲照样回来探亲,兴致勃勃地描述单位里某某人被批斗,某某人被抓了。父亲很天真,只要自己没牵连就心安理得,他还说运动初期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要整他的黑材料,令人发指,说着还把“令人发指”四个字写在纸上。他在上海到处买做工精致的红色语录袋,里面各放一本“小红书”,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说要带回去送给单位里的造反派。上海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以自己的手艺精致而自豪。当时流行穿草绿色的军装,但大多都是民间自制的,我搞到一套真的旧军装,还带军帽。其实我不喜欢军装,而父亲却穿了我的军装每天外出活动,临回西安时竟把我的军帽顺手牵羊戴在头上走了。回去不久,他就被单位里的造反派隔离审查,前后有两三年,一直到1970年才解除隔离。那时我们已经搬离了杨浦,搬到淮海路的飞龙大楼居住。算起来,我父亲在凤凰村只住过半个月,不过他很喜欢那里的居所,以后也一再说起。
父亲被隔离以后,母亲陷入了恍惚之中,常常六神无主地叹气,但是她外表一直很坚强,外人很难看得出来。但她的忧愁唯有我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深深地爱恋我的母亲,仿佛一下子长大为成年人,我挑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操持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六口之家。当时我大约十四岁。感到庆幸的是,父亲是在外地工作,他的被隔离审查并没有影响我在中学里参加所有活动,我照常加入红卫兵,积极参加所有的教学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但是在这个唯成分论的环境里,我填了许多表格,再也不填写父亲的成分是“店员”,而是填写“干部”,后来干脆填写“工人”,我对于那个时代完全采取了虚无态度。但我的内心不是没有隐忧,这些隐忧和内心折磨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精神成熟。我与时代的主流不自觉地保持了精神上的距离。
四、隐忧与成长
上一节我写到了隐忧与精神成长的关系,所谓隐忧,指的是一种心理。如果别人知道我父亲还在隔离审查中,我就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另类。回想起来,当时我并没有具体的恐惧感,因为我父亲毕竟是个积极上进的“干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与时代合拍的人,这样的人即使被误解一时,也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真正敌人。这是我内心的坚信。
其实当时审查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现在说起来也是稀奇古怪的。父亲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一生遇到两个老师。一个是张亦庵,“五四”时期的翻译家,小说理论家,也许还做过别的什么文艺创作。关于这个人,我以前在文章里写过,父亲是在他的培养下走上文学道路的。他们编辑的第一个杂志叫《蓓蕾》,这是我父亲走上文学编辑道路的第一个台阶。他后来告诉过我,那封面是一幅木刻画,一个女孩手里举着一枝花蕾,就是张先生教他刻的。还有一个老师是左翼诗人白曙,在孤岛时期,白曙对他也有过影响,后来突然消失了。张亦庵是一位旧式文人,因为张的介绍,父亲担任小报编辑后曾经向一批旧文人约过稿子,如包天笑、周瘦鹃等。父亲从来不对我讲这些历史,直到70年代中期,当他知道并阅读了我偷偷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后,才兴奋起来,有几次与我彻夜畅谈那段孤岛时期的历史。可惜不久以后他就在西安因脑溢血去世。一年以后,我考上了复旦中文系,研究起现代文学,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多了解父亲那一段经历。
但是父亲还是在办小报时掉进了陷阱。也是交友不慎,他结识了一个小报记者。据说这个人正在筹划一个文艺社团,拉拢了一批艺术家,也有我父亲在内。结果社团未办起来,那个小报记者已经被日本特务抓去了,还牵连了一大批朋友,父亲因此而逮捕。经审查后,
被保释出来,从此父亲就远离文艺领域,转到餐饮行业去了。尽管也是作餐饮业的文化策划和宣传,还办过几种广告性的小报,终究与文艺是越来越远了。但是这个被捕的“事件”――如果这也可以算“事件”的话,后来一直成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抗日分子,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而已,在法西斯专制的时代,任何打算组织文艺社团的计划都会被视为危险分子,被误捕而保释,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一再被猜疑审查而不得信任?我从未觉得父亲会有什么“问题”,只是默默地等待父亲的问题早日被审查清楚。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的无知导致了无畏。在“”时代无数被打入另册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哪里有过真正的“问题”,哪里是真正的“敌人”?不过我想当然地以为,既然父亲没有被定性就不能自轻自贱。我还是很坦然地参加了社会上的各种活动,自己不先被自己打倒――这个性格,后来轮到我自己人生道路上遭遇各种风波时,我也是这样来激励自己――要相信自己没有错,自己先不要被自己打倒。
但隐忧还是深藏于心间。隐忧的先决条件是相信自己没有错误,才能暗暗与社会主流保持距离。“”时代,个人微不足道,从众才会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可是你心里一旦有了隐忧,你就无法完全泯灭自己,因为你主观上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乌合之众的不一样。
我前半生的道路都与这种隐忧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我本性上与父亲很接近,这也许是遗传的力量,尽管父亲几乎没有与我一起生活过,但是他的天真、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潮流。追求理想,有时候会本能地支配我的行为,让我感到身心快乐;但是我从小接受的是外祖父的言传身教,外祖父对于社会主流基本上是采取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保持着孤独的怀疑精神。他对社会现象有很多智慧的判断,后来证明他总是正确的。这种怀疑精神在潜移默化中也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支配着我的理性。这两种力量在我的少年时代是不协调的,甚至是相互敌意的(至少我自己认为是这样)。我在杨浦四年的成长史中,这种角力几乎贯穿始终。
我的外祖父很快就要退出我的人格发展之路,他对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主要是时代的影响力弥漫了整个社会空间,当我不出门的时候,外祖父是我理解外部社会的主要渠道,但是随着我的年龄的成长,一步步迈出家门,走向更加广阔而复杂的天地,外祖父就逐渐成为一个过时人物。当时老人的身体逐年衰弱,渐渐地有了老年性臆想症的病状。记得有一次他睡午觉醒来,突然指着一本画有图画的书说,快把它糊起来,里面的老虎要出来吃人。大家都说他在讲胡话,他却真的用浆糊把一本图书一页一页地糊得密不通风。这以后外祖父的精神越来越差,整天在疑神疑鬼,不得安生。我觉得他一辈子都被内心中的隐忧折磨着,三十多岁日本人占领上海他拒不做任何事情,1949年他才五十岁不到,还是不找任何工作去做,做了几十年的闲散人员,安然无事。到了“”时代,他的内在意志终于崩溃。我似乎走出了隐忧,但其实,我一生都没有走出隐忧,也没有走出外祖父的影响,仿佛是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