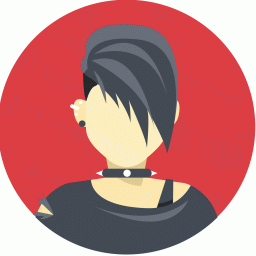黄凯:一路走向电影
时间:2022-05-12 08:23:57

黄凯(Kevin)小传:就读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四学生,正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实习。代表作品有《但我知道》、《大城市》、《去去来来》等。其中,由他担任导演和剪辑的剧情片《但我知道》在2004年获"第一届上海大学主题DV影像大赛"、"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剪辑奖"等多项奖项。他一手包揽导演、编剧和剪辑的剧情片《大城市》在上海12所高校巡回展映;2005年1月获得“影像新生力SONY全国青年DV大赛”之“最佳个性大奖”。2004年11月,这个酷似周杰伦的大男生从香港浸会大学“吴宇森电影导演大师班”结业,还被江苏文艺出版社列入80年代出色青年系列之一。
第一次见到黄凯是在上海美术馆,当时他正在专心地拍摄展厅里的作品。站在他身边的我显得十分拘谨,很留心地躲过他的照相机镜头所“占领”的地方。他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你就站在那边看画吧!这时的我才知道,他想记录的是完全真实与自然。
当天他带了一张光盘,里面是他的3部DV短片。黑底白字的封套蕴藏着神秘色彩。“这是我的作业集。”他把光盘递给我。“哦,作业集!”我喃喃自语,“为什么叫作业集?”
从意外到机遇
别看我现在已经拍了这么多短片,大大小小的奖也拿了不少,其实我第一次接触DV也仅仅是四年以前。高考时,我最初报考的是上海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但是由于分数等因素,我最终主修了上大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时我才开始对DV有所了解,不久后我发现我还挺适合做一个导演的,这是一个意外发现,但我就是这样,很容易爱上我所做的事情,并且想方设法要把它做好。
刚进大学还不到半年,当别的同学还在上影视解读课时,我已经萌发了拍一部DV短片的念头,我提议朋友们和我一起来做这么一项“工程”。可他们却回答我:“有必要这么早就拍DV吗?我们才大一耶!”
但我还是坚持最初的打算,大一那年,我学着自己拍摄短片,《台湾乌鲁木齐》就是我的处女作,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部作品会在“首届西安DV电影原创制作大赛”上获得剧情类二等奖。这一切的意外都在转瞬间成为了我的机遇。
《大城市》里的故事
《大城市》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王贝贝,他原来是一个做营销的小职员,有一天挤轻轨去上班时摔倒,在医院醒来时却发现所有人都叫他“王医生”,于是他将错就错地做起了医生;当时,城市里开始流行一种新的传染病――自言自语,而只有王贝贝可以医治这些病人,药方是一只口罩。起初这还很奏效,甚至电视台也来采访他。但后来医好的病例逐个复发,而且还更加严重,结果王贝贝被医院开除了,但他发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在欢迎他,于是他也戴上了口罩……
这部短片只拍了四天,共花费了1000多块钱,这些钱都是由学校提供的。可就在这四天里却发生了不少的故事。
剧中有好几场戏都是在轻轨的车厢里拍摄的,画面中看上去好像车厢里只有男女主人公,但其实那天轻轨上有很多人,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当时我们在拍摄现场放置了三个机位,一个是专门用来拍男主人公的,一个是专用来拍女主人公的,还有一个就是用来拍他们对话的场景的。其实当时的车厢还是比较拥挤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分镜头拍摄的方法,即把一个主人公的戏份一次性拍完。然而之所以会给观众以车厢空空如也的视觉感受,是因为我们总是趁每站人们下车后的一瞬间,用摄像机向主人公扫两秒钟,最后就成了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了。
其实我们原先并没有打算把拍摄场地定为轻轨,而是大巴士。当初,我们的剧组人员已经联系好了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同意借给我们一辆大巴士。且让我惊喜的是,那还是一辆美国巴士,简直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除了汽车,我们还有一些戏是要在车站上完成的。在我的设想中,我需要那种宽敞得可以给人以足够的视觉冲击的大型车站,我希望车站后最好还要有一幢象征大城市的宏伟建筑。很幸运的是,我竟然找到了这样一块场地。那就是上海科技馆旁的一个大型停车场,我看见它的时候简直无法想象,因为它完全符合我最初的要求。
只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我们最后还是错过了。
看守停车场的是一位老头儿。他听说我们想借用这块场地拍短片时,对我们这么说:“不久前也有一个剧组想要到我们这儿来拍戏,但要通过我这关,所以他们出价4万块1小时来和我商量,最后才拍成了他们的片子。现在我看你们都是小孩子,就便宜一点吧,400元1小时,怎么样?”
所以我最后不得不放弃那块我做梦都梦到的拍摄场地。
《大城市》里还有很多戏是在一家医院里拍摄的,那天已经是我们这部片子拍摄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打算把所有医院里的戏份在这一天里拍完。
那天下午,我们剧组的全体人员来到了这家医院,安排好一直拍到傍晚6点,然后大伙儿一起高高兴兴地去吃一顿关机饭。但是由于我们当时对医院的环境很不熟悉,仅仅是王贝贝在医院里醒来的一场戏就拍了整整一下午,剩余的戏都是晚上才拍完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一直到半夜12点才完工,别提什么关机饭了,一结束,我们就作鸟兽散。
我有我风格?!
以前有很多人都问过我一个同样的问题:“黄凯,你觉得你拍的片子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每当这时,我总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反问道:“我的片子有既定的风格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后来有一次,我大学里的一位专业课老师很明确地告诉我:“黄凯,其实你拍的片子是有风格的,而且还是一种很独特很强烈的风格,但你不要问我那是什么,因为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这一点其实我很明白,作为一个导演,他一旦意识到了自己拍摄的风格以后,他就很有可能不能再拍出优秀的影片了。
所谓的风格对我们来说有时会是一种束缚,因为强烈地感受到某一种东西的存在时,人脑就会产生一种意识。搞艺术的人不应该让这样的一种意识来牵制住拍片的灵感。对我来说,能把自己在生活中的点滴感悟付诸影片,灵感不用受到压抑,这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试着放下
其实我最终想做的事是拍电影、当导演,但是现在我还没有钱,所以拍DV短片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我一直都很明白,DV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我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拍电影胶片的真正的导演。
我是一个特别追求细节的人,所以经常要熬夜来完成剪辑、制片等工作,有时甚至会为短片上字幕的方式研究一整天,而拍摄往往只花了四天。每晚总有一堆的事情让我放心不下,于是,我就在自己的电脑上贴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试着放下!”这让我有时不得不告诉自己,放下了,能去睡觉了。
有的人认为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但我想,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把这张光盘起名为《黄凯作业集》而不是《黄凯作品集》也正是这么一个原因。我觉得我还没有那样的资质来称它为“作品集”,我毕竟还是一个学生,一个面临找工作难题的大四毕业生。
可是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信念:“无论我最后会去做什么职业,我都一定会成功。”或许也就是这份自信,才让我有现在这样的成绩。
采访现场再现
记者:你能谈谈对成长的看法吗?
黄凯:可以。这里我就以我的拍摄经历为例。我进大学前并不爱电影,只是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看喜剧,因为开开心心看看笑笑没有负担。我想这就是成长的最初期――无知。
在我接触了专业的课程和优秀的老师后,大量的欧洲艺术片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艺术影片的“感觉”令我们这些学生着迷。这也就像我们在成长路上,势必会有一、两件事情,或大或小,激发我们去尝试、去学习,然后渐渐长大。
经过一年的专业学习后,我又制作了12分钟的纪录短片《去去来来》和丁薇旧曲《女孩与四重奏》的MV,后两部看起来都比我的处女作《台湾乌鲁木齐》更加精致,构图、镜头的活动方式的设计等方面较之《台》也成熟了很多。在我们的成长中也必定会经历这个过程,从量变到质变,自我的蜕变总是在无数挫折的考验之后才出现。
此外我还想强调一点,“态度”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才能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我来说,正因为有这样的“态度”,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会设法苛求自己的作品接近完美,虽然它们都还不完美。
现在的我仍处于成长阶段,虽然无法预测未来的我会是怎样,但从小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一定回成功,无论我最后会去做什么职业,哪怕是做清洁工,我扫过的马路也一定会比别人的干净。
记者:你能不能向少女朋友们推荐一些你认为比较适合她们的影片?
黄凯:好的。
一部是美国导演史帝芬 斯皮尔伯格于1993年拍摄的《辛德勒的 名单》,在我看来人类都需要去看它。还有就是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斯基的“三色系列”――《红》、《白》、《蓝》,让我们来看看少女经常思考的“自由”、“平等”、“博爱”,看看大师是如何来诠释它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