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物理学家束星北与两位高徒的过往
时间:2022-10-20 04:4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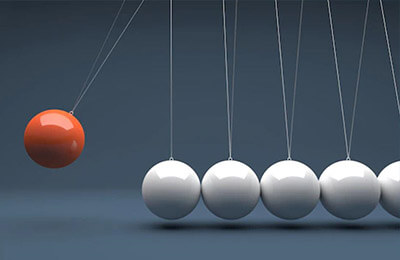
1995年9月30日,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隆重举行了“青岛市文化名人雕塑苑”揭幕仪式,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束星北的塑像就在其中。
束星北最欣赏的学生之一,2013年初去世的我国著名科学史专家许良英,评价他的恩师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束星北的一生的确是传奇的一生,他于1907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1926年起负笈欧美,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到过九所大学,未能在一个地方系统地学完四年的大学课程,却以四年半的时间,历经七所大学而拿到硕士学位,其间还担任过20世纪物理学泰斗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一生涉猎物理学的多个领域,在量子力学、相对论、电磁学、热力学以及气象学、海洋学、航天航空等研究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他既能动口又能动手,讲课不用教科书却出神入化;既能修理诸如心电图仪之类的仪器,又能制造出诸如雷达一类的大设备。
束星北高徒众多,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名扬世界的女科学家吴健雄、著名科学史专家许良英和2013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程开甲等。晚年,更是为国家培养了二十多名海洋学急需的骨干人才。
老师与学生之间,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这里讲述的是束星北与他的学生李政道和许良英之间发生的故事。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李政道”
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组织两万余名专家学者,取精用宏,历时十五载,终于编纂成《中国大百科全书》这部辉煌巨著。书中的每一个条目,都经过反复核实才能定稿。该书中的“李政道”条目写道:“1943年―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该条目在发排前曾送给李政道本人审阅。李政道对该条目多处做了修改和补充,唯有对这句话只字未动。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例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当时李政道很想见他的恩师一面,可是未能如愿。于是他给束星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二十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时束星北已经被下放到青岛北镇果园内劳动。因业余时间修理好了一些仪器设备而名声很大,驻青岛部队的雷达坏了都请他去修理。他还受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委托,进行金属胶粘剂项目的研究。他知道李政道想请他去北京相见后,却谢绝了。他认为,按中国的传统,只有学生拜谒老师的,没有老师拜谒学生的。1972年10月20日,束星北给李政道回了信,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二十八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
虽然李政道年轻时在浙江大学期间聆听束星北的教诲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受益之深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1931年束星北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一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学术风气非常浓厚。这使得当时的一大批学人的才干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也使得当时的学生受益匪浅。
1943年的暑假,李政道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他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束慰曾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很快,李政道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这年8月的大部分时间,李政道常盘桓在双修寺。他经常听到束星北和王淦昌平易近人的谈话,感觉很亲切。年仅十六岁的李政道,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并不很清楚,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性,对物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李政道是在贵州永兴上的一年级,此地离湄潭约三十里。当他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他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过一两个星期束星北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每次束星北来永兴,李政道都是唯一的学生,而他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教学关系下,束星北帮助李政道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
1944年暑期,李政道的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他去看望母亲,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李政道搭的卡车失事,人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的一部分压在李政道身上,使他的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天,束星北被聘去了重庆。
束星北一直牵挂着李政道这位好学好问好动脑筋的学生。1944年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民众人心惶惶,浙江大学的教学无形中停滞下来。恰好束星北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李政道就随束星北一起去了重庆。束星北考虑到自己在重庆研制抗战急需的雷达,没有时间亲自带李政道,加上浙江大学的教学已经基本停滞,于是建议李政道投奔昆明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先生。李政道欣然接受了恩师的建议。
在重庆告别时,束星北送给李政道一本国外学者写的物理学名著《电磁学》。这是束星北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教授做研究时用的(这位达尔文教授是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孙子)。《电磁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的汇考题,都有一定的难度。李政道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里,就以这本书为伴,把所有的题目都做完了。
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促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与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李政道回国访问浙大时,又多次提到恩师束星北对他的启迪和教育。他回忆道,束星北的讲课不限于课程内容,可涉及引导到整个物理学科。他深情地说:“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自重庆分别以后,尽管李政道自1972年以后曾多次回国,但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过面。
束星北于1978年被调到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工作后,就开始为培训海洋动力学人才而奔忙。有一次束星北到北京开会,当时李政道恰好回国到了北京。学员们都知道他俩的师生之谊,以为这对师生几十年未见面,一定会借此机会见面叙旧。没想到束星北很快就回来了,而且回来后马上就上课。有学员问束星北:“这次去北京,您一定见到李政道先生了吧?”束星北回答说:“没有,北京我有那么多学生,我怎么能单单去见他,我现在有了你们这些学生,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你们现在最需要我回来讲课,我们的时间很紧,我怎么能有时间去访友呢?”
束星北去世时,在美国的李政道发来唁函:“束老师是中国物理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他的去世是世界物理界及全国教育界极重大的损失。”
最想见的学生许良英
束星北桃李满天下。在与他关系最亲密的学生中,除了李政道自分别以后再没有见过面,还有他最想见的学生许良英,也是分别以后终生没有再见过面。
许良英是中国著名科学史家,2013年2月去世。他是《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2008年曾获美国物理学会“安德烈萨哈洛夫奖”。
许良英于1942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束星北和王淦昌都是他的老师。1945年他在浙大物理系任教。1946年夏天,他甘冒风险去重庆的新华日报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几经周折,他终于如愿以偿。1947年,他回到杭州,担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
许良英称束星北为他的“科学启蒙老师”,并对束星北的教学水平赞不绝口。他第一次听束星北的课是1939年10月。上课前,听说这门课是从最基本的牛顿运动三定律讲起,心想这内容早就学过好几遍了,听起来一定很枯燥。但一堂课听下来,他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后来束先生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而且回味无穷。
束星北十分痛恨的腐败,对共产党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他觉察到许良英的变化,因而非常看重这个变成共产党人的昔日的学生。1948年7月以后,浙大“舜水馆”物理实验楼成了浙大地下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不但地下党浙大总支会议在这里开,有些分支部的会议也常在某个实验室里开。而当时在浙大七个学院三十个系中,物理系是地下党员最多的,许良英他们在“舜水馆”频繁活动。束星北和其他一些进步教授始终是默默保护着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1949年年初,许良英他们不小心丢了一本宣传革命的“违禁”书,束星北捡到了,把它秘密保存起来,避免了一起在那个年代会有的险情。许良英后来回忆:“对束先生仗义支持我们的斗争,我无限感激。”
束星北1944年曾在重庆的军令部技术室研制雷达,因为这段经历,按照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划定标准,束星北够得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当时杭州市公安局准备将束星北列入镇反名单。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讨论这件事情时,许良英坚决反对。他阐述的理由是:束星北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会上其他同志都同意许良英的意见,于是束星北就被保了下来。由此,束星北更是认定许良英这样的共产党人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是值得信赖的。
自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被调到山东大学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1978年以后,他们却为“爱因斯坦”问题产生了严重误会,以至于终生未解。
许良英在《爱因斯坦文集》三卷出齐后即寄赠束星北一套,并题词“敬请束老师指正――学生许良英”。许良英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三十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十六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时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但实际上束星北并没有将这几本书“束之高阁”,之所以这么说是另有原因的。束星北当时正在青岛办海洋动力学培训班。他看完《爱因斯坦文集》后曾对自己的学生和子女都说过:“这本书不管他翻译得怎么样,但他能在困境中,在劳动之余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学习。”那时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在学英语,经常请教父亲。束星北在强调翻译的重要性时说:“很多翻译书的译者自己本身就没有搞懂,中文又并不好,往往让别人越看越糊涂。”有一次他顺手拿起桌子上放着的《爱因斯坦文集》说道:“可惜这本书好多地方都翻译得不准确。”束星北虽然认为许英良在书中好多地方翻译得不是很准确,但他不愿意过多地对别人提这件事,怕给许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只是想有机会当面和许良英谈谈。毕竟自己在国外留学六年,而许良英并没有多深的英语根基。这也就成了束星北急于想见许英良的一个原因。
但许良英却认为将书“束之高阁”并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另有隐情。束星北于1983年10月30日去世。但是许良英又在2005年谈起了这段隐情。2005年曾有一本关于束星北的传记出版,面世后好评如潮,多家媒体称束星北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许良英发表了《我所认识的束星北》一文。文章在谈到束星北和爱因斯坦的关系时,则认为束星北声称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是“伪造”。至于为什么会伪造,“唯一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 。
但是,几乎所有束星北当年的同事和学生,都对许良英的这种说法反应强烈。许多浙江大学老校友和与束星北有过交往的人,例如杨竹亭、王彬华、孙沩等都撰文证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听说束星北担任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事情。当年《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的采访记者宫苏艺也回忆,他是通过时任《光明日报》科学副刊组组长的金涛,获知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信息的。1979年2月22日,宫苏艺找到束星北,束星北口述一个小时左右。23日上午宫将文章交束星北审查,下午寄回报社。宫苏艺以此说明是先在北京知道了这个线索才前往青岛的。采访和束星北接受采访都是偶然的,说是有意伪造确实难以讲得通。许良英的另外一位恩师、束星北的挚友兼同事王淦昌也认可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之说,他在1992年为束星北遗著《狭义相对论》所作的“序言”中就提到束星北“曾任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后来许良英又出示了一封证明束星北与爱因斯坦没有交往的英文信件,结果束星北的亲友们都指出了许良英的理解错误,特别是程开甲还对那封信件进行详细的解释。程开甲1946年至1950年在英国留学四年,后来还出版了英文专著《超导机理》。他在谈到那封信时指出,这封信恰恰证明了束星北曾和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
束星北之所以最想见许良英,还有一个原因是曾目睹许良英当年在浙大的突出表现,他非常相信许良英的能力。1982年,束星北以前的学生周志成到青岛疗养。他们见面后,束星北特别兴奋,说了一个晚上话。束请周转告许良英,要许帮助找一些好的学生,“像李政道那样的学生”。许和周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是束星北最早接触的几位共产党人。周志成在谈到束委托许找学生这个问题时,认为束在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后,还是把他一生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信任的学生身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束星北和许良英终未能见面。许良英后来回忆:“1982年,束先生通过周志成和束美新一再邀请我去青岛聚谈,说他有很多心里话要向我倾诉……我准备待书稿《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完成后,于1984年去看望先生。孰料先生竟于1983年10月30日猝然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