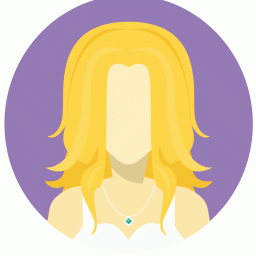从藏族与羌族的形成与发展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时间:2022-10-07 01:39:27

作者简介:徐伟(1981.10-),男,汉族,籍贯成都,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09级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于“藏”、“羌”两个民族的谈论,史学界颇为热闹。作为现在生活在祖国大地四分之一领土的藏族与现今主要生活在四川阿坝一带(及绵阳北川、贵州铜仁等地)少许地盘但历史上曾遍布大半个中国的“羌”来说,无论是从现今角度还是历史角度来说都可称其为大族。但本文欲站在一个时空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族群,特别是要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理性地看待两个民族的演变过程,从而得出现在我们如果研究民族史基于太片面或站在太唯我的立场皆不可取,最终抛出“藏”、“羌”及其他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必然性。
关键词:藏;羌;泛羌;民族;多元一体
一、藏、羌的来历及说明
(一)关于藏族来源,众说纷纭,有猕猴与岩魔女结合,传出人类之说;i亦有“猕猴变人”的神话传说;还有印度来源说,这只是由于佛教发展源于印度,佛教徒在追溯本民族族源的一种附会学说(从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藏区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属于蒙古人种,而与印欧人种毫无关联);当然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国内较为流行的“氐羌说”。关于“氐羌说”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任乃强先生《羌族源流探索》及黄奋生《藏族史略》等皆谈到藏族来源于羌族。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对于“羌”这个概念,古人在界定中原周边诸族时常谈到“北狄、西羌(戎)、南蛮、东夷”,这里的狄、羌(戎)、蛮、夷仅为中原民族对周边民族的一种泛称,既然是泛称,那么在当时的中原民族以西的广大区域生活的各部落都被称作“羌”(戎),“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泯间”ii针对此,古人还将其意想到“发”(音同“蕃”)而将藏族与氐羌民族的“发羌”联系起来,后人及今人不加思索地沿用,故将羌族扩大化了,由此产生上述观点亦难免了。
如果从最近的一些年的考古挖掘以及从一些史料与民族的自身发展演变来看,我认为藏族应该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不同地域,特别是在山南的雅隆河流域的“鹘提悉勃野”部壮大以后,兼并了其它一些区域,逐渐从多元的一种状态走向了一体。待到囊日论赞及其子松赞干布以至后来的噶氏家族时期,以古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朝疆及极致,其先后征服了苏毗、羊同、白兰、党项、附国、嘉良夷等诸羌部落及吐谷浑等。诸羌的“羌”本来就是不为一体的,“羌”前面已经谈到仅为泛称,不能界定为羌族,当然在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以至后来的上千年时间的融合,诸羌部逐渐被“藏化”,而在民族识别中遵从“科学的识别及名从主人”的原则将其化为藏族。现在的安多、康巴等一带的藏区藏族应该是民族融合下的产物,故而与卫藏的藏族在体质特征、语言、风俗习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当然也与各地气候、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也不足为奇了。
吐蕃的盛极一时对藏民族族体的形成及藏民族的分布区域是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了的。即使当吐蕃王朝衰落以后,也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一种民族融合的作用。后来的宋代以文人治朝,军事实力也仅及“宋挥玉斧”的大渡河一带,更不及藏地了。再后来在元朝政府的治藏策略下,藏地的八思巴不仅与忽必烈有师徒关系,且被封为帝师。当时的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并实行了人口清查,派兵清剿异己、干预藏地矛盾也从此时开始。后来,明朝政府分封“法王”及“王”,扶持各教派,以教治乌斯藏,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清朝更是设驻藏大臣,派遣军队,册封达赖与班禅,将作为大清疆域的一个地方机构来进行统治。尔后到清朝末年,英人两次侵藏,企图将从萎靡的中剥离出去。甚至在当时的民国政府看来也鞭长莫及,并筹划建西康省以治边地,并以防藏军进一步往金沙江吞噬。这些史实从历史的角度的确证明了辛亥革命后到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期间在英人等外部势力的操纵下变相“独立”,但也不足以抹煞前述的从元至清八百年与中央的关系。但同时也说明的一点就是地区融入到中国版图是历史的选择。还说明了藏族经过各个部落的融合统一而向各向发展(以东为主)而与诸羌等部落融合,这也许是藏族部落最终走向与中原民族,也就是与他的东边民族成为不可分离的原因之一。当其强大的民族融合靠近汉地时又遇到了文化较为先进、各方面更加强势、包容性又很强的汉民族时虽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是经过你来我往的长期交流,其也与其接壤的民族间的融合却进一步加深并唇齿相依了。民族间只有交往才会彼此了解,虽有矛盾但只要相处方式、统治者施政方针正确更是能够促进民族间的关系和谐。这样就形成了藏族从自身的“多元一体”走向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二)关于羌的来历前面已谈到古有西戎、西羌之说,也常将氐羌连用,《诗经•商颂》中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现在中国的民族大系划分也将氐羌与壮侗、百越等齐名。故而至少氐羌应该是一个大的系统,许多从事民族史的学者亦把西南诸多民族与氐羌联系起来考虑。但究竟是否与氐羌有联系,或者与氐羌有联系的民族是否曾经都发源于甘青地区,有待从考古、历史史籍、人类学等方面作进一步研究考证。这里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将“羌”称作一个泛称,因为中国先秦时候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稳定的民族,汉族也是将华夏族这个族团历经秦汉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时汉族也是一种他称,既别的民族的称呼后来也被赋予了汉族。羌也是中原民族对其西边广大区域的诸部落的一种泛称,再次强调一下:本文的观点就是羌族只在今天四川阿坝一带,今天的羌族并非历史上的羌,今天的羌族也与历史上的羌也有一定的关系。应该可以肯定的是现如今的羌族应该是古时泛羌族称中的一支或几支而保留了古羌民族的相应风俗而历史遗留在今天的一种写照。(就泛羌来说各部落民风也应该不一样)。
《说文•羊部》解释为“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杨光成《西羌壮歌》解释“羌”与“美”有关。当然古人有解释羊大为美的说法,不过将“羌”与美联系起来有附会之嫌。在许多学者看来皆把羌作为一个大的概念,并从浩瀚的史籍中将其与“姜”、神农氏、禹、周人等联系起来。而且在划分民族时不仅将羌族作为一个单独的族群划分出来,也将羌语划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羌语支,并与其他如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普米、景颇、怒、独龙族等藏缅语族的民族联系在一起。认为以上的民族历史上与羌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及马长寿的《氐与羌》书中将羌扩大到一个较大的范围。马长寿先生认为羌族“自古以来从今河南一直向西,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向南直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iii,任乃强先生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我国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都与羌族有关”iv。两位学者研究的是历史上的一种泛羌,而与羌族肯定是有联系的,但就目前国家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与其他许多民族的完全牵强附会的假说就不足为据了。这也反向的导致了许多藏族学者大多强调“藏族完全本土化”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名称是近代抵御外国侵略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族觉醒或民族共同体,但是它内部的56个成员间有些民族与民族之间历史上、现在及将来必将产生这样那样你来我往、此消彼长、共依共存的局面。所以说基于“泛羌”或现今羌族来说都只不过是我们研究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一个取材、一个立足点而已,在本文中也不是过于强调并区别他们的不同。
二、(一)藏的族体扩大及藏族的形成
目前比较公认且较为合理的是在雅隆河流域的“鹘提系勃野部”经历了“天赤七王”、“上丁二王”、“中累六王”、“地带八王”、“下赞三王”直到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囊日论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又兼并了周围诸部,在遭毒害后,其子松赞干布又继承父业,兼并高原上的泛羌诸部:苏毗、羊同、白兰、党项、附国及鲜卑人建立但民众仍以泛羌为主的吐谷浑,之后的噶氏家族使吐蕃王朝的疆域发展,与唐、南诏的你往我来、尔虞我诈、战争与结盟,“舅甥关系”、“兄弟关系”间,互有胜负,但总的来说促进了交往。待到各自几乎同时代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之后又经历了各自的混乱时期。但是由于吐蕃又有了自己的文字,加之又在藏传佛教的庇护下使得吐蕃化的民族在余后的几百上千年中仍然维系了一个大致的实体,无论“番”或“西番”的称呼以后大部归于藏族实体中了。
必须承认的是藏族实体的扩大至少就现在有史可查及保留的民风民俗来说就有木雅藏、嘉绒藏、白马藏、及蒙古的“霍尔”和木氏土司的移民纳西(么些人)等。当然还有许多已经很难区分开来了。所以说,,藏的实体扩大以及藏民族的最终形成本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产物。
(二)羌的族体缩小和羌族的形成
从泛羌到真正羌族族称的形成,其实也就是中国西部大多民族的形成过程。西羌、西戎、氐羌的分布在历史上基本上涵盖中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及少部中原一带,甘肃、青海、新疆、、四川以及陕西、山西、河南皆有他们的影子,甚至西南诸多民族,特别是云贵一带的氐羌系统民族也或多或少与羌等联系起来。由此,羌人的分布区域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证明这些历史存在的泛羌与现在的羌人至少可以说明的一点就是羌这个感念的缩小化。但将现在的羌族完全与历史上的羌等同的观点是无多大意义的。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羌族所分布区域为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县、松潘县和绵阳的北川、平武县一带以及甘孜的丹巴县和贵州的铜仁石阡、江口有部分人口。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羌族人口为306072人,地震中北川县城亡灵就3万余,第六次人口普查可能有些变化。
三、从藏、羌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中国当今的民族格局的形成及中国作为“多元”而成“一体”的原因既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其形成的必然,同时也可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加以分析。
谈经济首先要从自然环境说起。藏族几乎分布于青藏高原带,青藏高原的东部又是与内地的山地、丘陵、平原相连的,是属于民族融合、交流的集中区域。羌族所分布的阿坝一带又是与汉藏等民族杂居在一起的,地处汉藏之间,属于高原边缘,气候属于高寒地带至低海拔地带之过渡地带。青藏高原是中国三大河流的发祥地,著名的三江源就在青海。三江孕育了中华民族,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其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谓名正言顺、实至名归。青藏高原多产耐高寒的动植物,而大米、面粉、油等除了现在察隅、门隅一带为的粮仓以外v,许多地方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以及大量的放牧。所以,实际上特别是藏东一带的民众与其相邻的汉、回等民族间长期互依互存,相处甚好,不因战争或政权的更替。藏羌人民的牛羊肉及奶制品销往内地,内地的大米、面粉、油等则运往青藏生活区域。特别是藏民族喜好的酥油茶、清茶都是用大茶制作而成的,原料非取茶不可,茶对于藏民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vi著名的“茶马古道”既有从云南至藏的滇茶,又有从四川雅安至藏的川茶,后者只是更为主要一些而已。另外现如今的经济更是一种启蒙状态的依附式,外来的帮助虽然还仅仅是一种“输血型”经济使得走上了较为发展的道路。藏羌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的亲情也是建立在一种民族感情、一种地理渊源上的。这种天然赋予的联系不是哪位领导人、哪位英雄欲连就连,欲分就分的。它不仅是人为的历史,更是自然的历史。某些所谓的民族代言人在政治上吹捧的“民族独立”永远也割不断民族间的山水相连,人民的友好往来以及经济上的优势互补。
至于文化上,羌族更是追溯到了三皇五帝,将姬姓炎帝、大禹等中华民族的祖先与民族的发展联系起来,在民族认同上其更倾向于中华民族间的“同源异流”。藏民族与祖国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可谓也是历史悠久。唐与吐蕃“舅甥关系”、文化交流:吐蕃派贵族子弟入长安求学,佛教、中原文化传入藏地,吐蕃的文化也让中原的民族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形成及以后的传播发展等;元朝时在藏地扶持萨迦派,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藏传佛教也传到蒙古地区;明清民国时期继续进行着扩大化的文化交流(即使在被英人操纵的一段时间);和平解放以后,藏区与祖国各地的文化更是得到了空前的交流与发展,这种交流是互动的,它也使得藏族文化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藏族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进一步发扬壮大。
在政治上羌始终与中央王朝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和平也好、战争也好。藏地与祖国的联系则是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舅甥关系”、“唐蕃会盟”等又为元朝最终形成对行使起到了铺垫作用。“如果没有7世纪以来吐蕃王朝和唐朝在政治上建立起来的联系,没有自6世纪以来形成的古代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那么13世纪中叶元朝在行使也必将是不可能的”。vii元朝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在实行了统治。明朝也延续了元朝的治藏策略,只是采取了不以一派为主要的扶持对象。清朝在前人奠基上进一步加强了对的统治,于1720年驱逐了侵扰的准噶尔军,又册封班禅、达赖。清末由于清廷的腐败,中华大地“四面楚歌”,深处大西南的藏地也遭受到英帝国主义的两次侵略直到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与达成一揽子协议,在民国时期一些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人士欲达到自身的相关利益,曾经在帝国主义的协同下欲谋取独立的阴谋宣告破灭,再次真正意义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中来,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新篇章,所以有唐以来,与祖国的关系就是在政治上密不可分的。历史及政治上的长期发展、自然的赋予、经济的互补、文化的相连、民族情结的互融等使得藏羌与祖国的关系是逐步而来的,并非一些独立分子鼓吹的“军事占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版图等也是藏羌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说是此地区漫长历程中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viii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各民族共同的产物,需要我们共同珍惜,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民族安宁。只有各个民族间的团结与努力才有中华民族的兴旺与复兴。那些各怀鬼胎的民主国家的卫士们在今天一个中国日渐强大并和平崛起的世界诏言下仍然挖足心思、居心叵测地大打“民族”、“民主”之牌来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必须加以警惕,警钟长鸣!(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 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40――43
[2] 《新唐书•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6071
[3] 马长寿《氐与羌》绪论
[4]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序言
[5] 况且历史上这些地方也不能(实质上也不可能)供应整个藏区的粮油,现在印度又占据门隅一带,问题又使得那里变得复杂起来。
[6] 我个人在藏区的几年拿上一段时间不喝茶心里就有点痒痒的,何况是出生就生活在那样环境的人们呢?
[7] 王仁辅《论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原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8]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