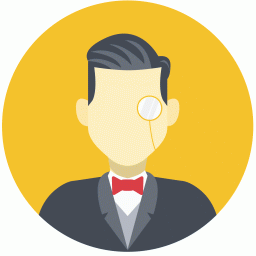略论曾国藩对桐城派后期文风的修正
时间:2022-09-28 02:39:44
摘 要:曾国藩对后期桐城派空洞的文风和树立门户之见的流弊进行批判,并改变自方苞以来桐城派只重视唐宋散文的阅读习惯,广泛涉猎秦汉、魏晋文章,把骈文与辞赋的写作经验引入创作之中,注意修辞与声调的运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洁的单调贫乏之弊;他还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理论,在遵从“道统”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后期桐城文风进行了修正,并获得了成功。
关键词:曾国藩 桐城派 修正
文坛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对前一时期或同期文学创作弊病的反拨。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是对明前期文坛馆阁文学的死板文法进行反拨,兴起于“宗秦汉”还是“尊唐宋”之争尚未停息的康熙时期的桐城派,也是对明代以来拘泥复古而导致为文“模拟剽贼”局面的反拨。
但是,也正如曾为文坛带来新风的前后七子最终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复古的道路;“文必秦汉”最后反阻滞文章真正地向秦汉之风靠近一样,虽然反拨了别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无物,兴于康雍、盛于乾嘉、影响经过同光直到民初还饶有余音的桐城派,其在经过了康乾时期戴、方、刘、姚诸人带来的发展盛状后,在清中后期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向死守“义理”、拘泥“文以载道”的“道统”观方向前行,而逐渐走入空洞无物、不合实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叹:“时文之法者陋矣。谬然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1](P88),在清代后期由桐城派主导的文坛上,这种曾为“时文”所有的弊病也显于“古文”中来。曾国藩就说过:“乾隆、嘉庆之际,学者研练经义,负声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词丰而义寡、栀蜡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坛创作不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为显,排句叠调以为劲”,还在文风上“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2](P288-322)正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文风的纠正势在必行,而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2](P248)的曾国藩正是以自己对桐城文法的秉承与超越,在“姚门四杰”相继去世后的清晚期,针对文风之弊做出种种革新,试图一挽桐城于颓败。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讲求“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非阐道益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3](P35)这成为桐城派创作的基本守则。作为桐城后学,曾国藩自然也继承这一创作主导思路。他的《致刘蓉书》说:“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4](P7-8)虽然这里是在倡导对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离不开以“人心所载之理”主导着“人身之血气”的大前提――仍然是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的再阐释,只不过是用“血气”承载“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图解而已。
不仅如此,《圣哲画像记》里标榜:“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径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2](P248)《书仪礼释官后》认为:“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2](P302)将“道”具象成以“礼”为核心、以“仁”和“义”为两大准绳的思想体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维护着理学的权威。
以桐城所宗为自己所旨,表明了曾国藩与桐城派的渊源。但面对日渐偏离康乾时期文风,从思想到笔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刘蓉于《复吴南屏学博书》中评价为“惟宗派之云,甚至谓句法之短长伸缩,声音之抗坠疾徐,皆有一定绳尺,如词曲之有谱然,寻声逐影,良可厌薄”的桐城末流,曾国藩又严肃地与之划清界限:在《覆吴南屏》这封信中,他点评说:“至尊缄有云:‘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着痒处。”并表示:“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5](P13797)对梅曾亮等人渐趋仅以姚鼐为正宗,树立门户之别、失之狭隘浅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桐城后进,在末流以宗派之说当道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敢于品评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与刘霞仙》里认为方苞成就尚未达到“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的地步,其在“发明义理”与“学为文”之间“两下兼顾”,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以致无可怡悦”[4](P247-248);在《覆吴南屏》里评析姚鼐“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5](P13798)。这些无疑都表明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又自觉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创作视角。
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上,曾氏主动地对桐城派进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丰六年十一月谕子函》中说:“余平生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又在《覆邓寅阶书》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选》之尽善。”还对吴敏树说:“弟尝劝人读《汉书》、《文选》以日渐腴润。”(《覆吴南屏》)平生好读之书除桐城派一贯尊崇的韩愈文章外,还有《史记》、《汉书》、《庄子》,而且认为《文选》集粹的古文质量最高,并爱向他人推荐阅读《汉书》、《文选》――曾国藩的古文视野已然跳出了桐城派传统上以唐宋家为核心的阅读习惯,向前延伸到了先秦、两汉、南北朝;同时《庄子》的“入选”也表明他对刻板“道统”的扬弃,为求古文真谛而不过分计较作品是否出自先贤大儒之手。
在阅读习惯方面,曾氏不仅从选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传统的唐宋两代限制,还在选文的体裁上跨越方苞设下的藩篱。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古文中不可录……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力求“雅洁”。而曾国藩在日记中自叙:“余近年最好班马扬张之赋。”力推“文章之可以道古适今者,莫如赋”(《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孙南归序》里强调:“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独不然。”将古文和骈文的关系阐述为奇与偶的相对与相补充,从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对骈文的过激排斥。
在对骈文进行高度评价的基础上,曾国藩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文论,并指出在音节方面,“声调铿锵”是汉魏文人“有两端最不可及”的高处之一(《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子函》)。这自然超越了方苞写文章排斥“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这一截然分离散文与骈文联系的论调。吴汝纶在《与姚仲实》中评价曾的文论是“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大家”[6](P1168),足见时人已经认可了曾国藩结合骈文特点、改进古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过,虽然对桐城文风进行了一定修补,但曾国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导致桐城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来文章空言无物的核心原因: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导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诗集序》宣扬:“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7](P289)粗看之下,似乎是将一直以来对立着的“文”与“道”进行糅合,将“文”通过被人为地定义成与“道”相合的“艺”,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实质上仍是和从“文以明道”向“文以载道”的转变那样,通过将“文”定位在“艺”,使“道”完完全全地统辖着“文”,让“文”仅仅成为因“道”而存在的技术性附庸,抹杀了“文”的本体特征。
而在《与刘霞仙》里,曾国藩对“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尽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廖廖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录》、《思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4](P247-248)
他承认“文”“道”是可以“兼尽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笔下,“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并以方苞为例证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在这种不可调和性面前,曾国藩同姚鼐一样,仍然是遵从着“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评判文章的价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札,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文阿娜之声,历唐而不改。虽韩、李锐复古,亦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苏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2](P319)
在这里,他将“习于情韵”与“习与义理”两者一视同仁,公允地认为各有特色的同时也各有弊病,同属于“偏胜”。但又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束缚,对宋以来的“法韩氏”、“习于义理”做出了“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的好评,在一视同仁的基调上最终还是偏向了“义理”代表的道统观念。
参考文献:
[1]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徐珂编.清稗类钞选・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
[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C].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6]吴汝纶.吴汝纶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2.
[7]姚鼐.姚鼐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