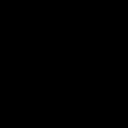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负面影响与干预
时间:2022-09-24 03:20:31
摘要:艾滋病污名主要包括实际污名、感知污名和自我污名,这些不同形式的污名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社会资源的剥夺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归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道德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学、社会不平等和文化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从这些机制出发,减少艾滋病污名可以结合接触假设、知识传播以及认知行为疗法,并注意改变艾滋病患者的自身观念。未来的艾滋病污名研究应更多地从社会文化以及道德的角度进行跨文化的量化研究。
关键词:艾滋病;污名;归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文化道德理论
分类号:B849:C91;R395
“污名”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由Goffman重新提出后,对污名的研究至今从未中断过。根据Goffrnan的定义,污名(stigma)指的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具有耻辱性质的特征”fGoffman,1963)。随着对污名现象研究的细化,研究者们逐渐区分出不同的污名类型,受到较多关注的有精神疾病的污名(corrigan,2000;Rfiseh,Angermeyer,&Corrigan,2005),传染疾病的污名(Des Jarlais,Galea,Tracy,Tross,&Vlahov,2006;Mak et a1.,2006;Zhang,Liu,Bromley,&Tang,2007),性取向的污名(Neilands,Steward,&Choi,20081,性别(Herek,2007)、种族的污名(Dean,Roth,&Bobko,2008)以及肥胖的污名(Roehling,Roehling,&Pichler,2007)等等。在传染疾病的污名当中,艾滋病污名是近些年来倍受重视的污名现象之一。艾滋病,医学上称之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导致免疫系统的摧毁。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应用于艾滋病治疗之前,艾滋病被普遍认为具有高度致死性,因此导致人们对它产生本能上的恐惧;不仅如此,由于艾滋病的传染通常与一些被公众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如使用注射针具吸毒,同性恋或易等相联系,因此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常常伴随着道德上的谴责与排斥(Deng,Li,Sringemyuang,&Zhang,2007;Liu&Choi,2006,杨清等,2007)。加上艾滋病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文化方面的关注(Choi,Hudes,&Steward,2008;Goffman,1963),都使得公众对艾滋病的污名无论是程度还是范围都远远超过对其他传染疾病的污名(Mak et a1.,2006)。
1 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
1.1归因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通常采用社会认知理论对艾滋病污名的成因进行分析,其中主要是归因理论的运用。1988年Weiner在研究中让被试判断十种不同污名情况的发生原因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并记录被试在面对这些污名情况时的情绪反应,由此将污名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Weiner,Perry.&Magnusson,1988)。根据Weiner的归因理论,对致病原因的归因会导致个体对患病者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其对患者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在这一归因过程中,可控性(controllabilityl是最为重要的维度,如果致病原因是不可控的――即不管患者是否预期到其行为所能导致的后果,只要致病行为并非其能够控制的―那么人们对因此而患病的人会产生同情,进而导致了人们将对患者做出帮助行为;如果某一疾病的致病原因是患者可控的,人们对患者的情绪反应则变为愤怒,认为患病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会做出歧视行为(Weiner et a1,1988)。换句话说,对可控性的认知导致对患者致病责任的判断,是产生污名情绪以及污名行为的主要原因。
归因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明确了污名现象的形成过程,为大多数的污名研究者所接受,并不断被应用于研究各种疾病的污名现象。2006年Mak等人的研究中。对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sARs)和肺结核三种传染型疾病的归因模型进行了检验,得出了由归因模式导致公众污名的模型(见图1)。其中,相比于非典型性肺炎和肺结核,艾滋病患者受到更加严厉和公开的污名,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罹患艾滋病的患者是咎由自取,感染艾滋病毒是由患者自身可控的行为所造成的,因此艾滋病患者更应该为自己的病情负责,也受到更多的指责,这一系列的归因导致了公众给予艾滋病患者更多的污名(Mak et a1.,2006)。
然而,归因理论有时候并不能完全解释艾滋病污名的发生原因。Peter等人1994年的研究中以小品文的形式控制了艾滋病患者得病的可控性,即情景描述分别为个人可控的和个人不可控的原因,要求被试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进行评价,尽管对疾病来源的归因能够解释部分污名的减少,但艾滋病的致死性,感染的风险等其它变量相比归因更多地解释了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反应行为(Peters,den Boer,Kok,&Sehaalma,1994)。因此,尽管归因理论在对各种疾病,包括对艾滋病的公众污名的解释,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可,但在艾滋病污名的发生过程中,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可能对污名的形成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有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1.2社会文化理论
在归因理论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的同时。2003年Parker等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污名的概念框架fParker&Aggleton.2003)。Parker认为以往研究中对污名的研究存在概念上的局限,对污名的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偏离了Goffman对污名的经典定义。污名,归根结底,应该是一种能够降低个体社会地位的属性,污名他人的过程是通过建立各种规则而提升优势群体的利益,制造等级观念和次序,并进一步用制度化的手段使等级观念和等级次序合法化的过程。归因理论过于强调对个体的研究,强调个体的知觉以及这些知觉对社会交往的影响,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污名和歧视是与整个人类群体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的结果。Parker援引法国哲学家Foucault和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对权力和社会文化的观点,认为污名作用于文化、权力和差异的交叉点上,污名和歧视不仅仅在差异中出现,而是更加明确地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相关联。污名他人是社会生活中复杂的权力斗争的部分内容,是一部分人通过制度或霸权而追求权力、地位和社会资源的过程,并且在获得优势地位之后继续污名他人,以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实现他们的优势地位合法化。
社会文化理论提出后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支持。Padilla等人以一个特殊群体,拉丁美洲双
性恋艾滋病男性为被试,考察他们对其父母及配偶公开其性取向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污名经历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对70名被试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的结果发现,这些被试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挤,而导致他们从事易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年他们早年的无家可归、贫穷以及被虐待的社会经历(Padilla et al…2008)。社会的不平等使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为了获得社会资源,他们选择从事易活动,但这导致他们被污名情形的出现,而且会进一步的加剧他们社会资源的缺失。
对巴西艾滋病儿童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文化习俗、社会不平等以及权利差异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对艾滋病儿童的污名fAbadA-a-Barrero&Castro,2006)。研究者对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艾滋病儿童进行访谈,发现艾滋病相关污名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而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不仅仅提高了艾滋病儿童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它使这些儿童有机会获得这种帮助其抵御艾滋病的医疗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的不平等,进而降低了艾滋病儿童的污名。
1.3 文化道德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提出之后,被一些研究者所采纳并发展。2007年Yang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污名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D,,他们认为污名最主要的特点是使人感受到其珍视的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名誉,地位等)面临即将失去或减少的危险,或正在遭受着损失(Yang et a1.,2007)。污名他人,是为了应对知觉到的威胁或真实的危险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它不仅是污名者自我保护和心理防御的一种机制,而且已经上升到了道德的层面。对于被污名者,污名使其痛苦复杂化,即不仅要面对自身某些缺陷,更重要的是,还要面临精神世界的损失(地位,声誉等)。污名的跨文化相似性表明,污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认知适应能力――通过排斥那些具有(或可能具有)某种不良特质的人来避免群居生活中的潜在危险(Major&OBrien,2005)。Yang等人将污名的概念模型应用于中国人对“面子”的研究,综合了近年来对中国艾滋病患者和精神分裂症的污名研究,提出了如图2所示的中国人的污名三层次模型,用以解释污名的社会特征是如何产生恶劣影响的(Yang&Kleinman,2008)。模型的最上层是影响污名的社会因素,它包含污名情形的公共观念和污名的制度形式,具体到艾滋病患者的情形中,前者包含公众对艾滋病的刻板印象、社会的等级结构等,后者则代表了由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对艾滋病的歧视方式。这两个因素是决定艾滋病污名在社会中存在的宏观因素,与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阐述相类似:模型第二层为污名的道德变化,具体来说,就是“丢脸”或失去获得社会资源的象征资本。尽管“丢脸”与污名的发生是不可分离的,但对道德的评价在污名的发生过程中具有媒介的作用。艾滋病患者通常被认为“丢脸”的原因,就在于对其患病原因的道德评价。有研究表明,通过献血、卖血或输血等无关道德评价的方式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更容易获得同情,也不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在这中间,对患病原因的道德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zhou,2007);模型的第三层包含了三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方面,这三者共同作用于污名对社会中个体的影响:在主观或个体层面上,道德的变化影响情绪的变化,在道德系统中丧失声誉导致情绪上的低落,如艾滋病患者道德上的“丢脸”被强烈的感知为羞愧或屈辱。另一方面,污名的道德变化还导致生理变化,正如“丢脸”有其心身表现一样,个体的社会价值也是有其生理机能的,颜面扫地或者没脸见人都会导致其生理上的变化。在集体层面上。污名是在家庭成员之间或社会网络中间发生的。“丢脸”会成为一种集体的感受,一名艾滋病患者公开其患病身份后,其整个家庭或整个社交网络都会共同感到羞愧。这一集体的羞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个体之间的语言、手势、含义、感觉和个体自身的感觉在产生污名的过程中同样重要。污名的人际层面包括所有个体对个体形式的歧视和社会排斥,如在艾滋病污名中普遍存在的医护污名和家庭成员的污名。另外,关系(或社会资本)的缺失同样是人际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艾滋病患者,这种关系或社会资本的缺失则可能表现为在求职、租房、受教育等方面的歧视。
2 艾滋病污名的影响
2.1 对艾滋病患者的影响
污名对艾滋病患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艾滋病患者在承受疾病痛苦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污名化程度越高,其心理压力越大(steward et a1.,200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艾滋病污名所带来的伤害,不亚于疾病对他们造成的伤害(Bogart et a1.,2008;Link&Phelan,2006;Mak et a1.,2006)。由于害怕面对因为疾病而引发的污名,有些艾滋病患者可能会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病情,或拒绝求医和接受治疗,这一行为进而会加剧病情的恶化,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对艾滋病的污名能够导致对其治疗作用的降低,还可能会导致艾滋病毒的进一步传播(Anderson et a1.,2008;Liu&Choi,2006)。对于已经暴露病情的艾滋病患者而言,普遍存在的污名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和生活上陷入巨大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失去工作或不被雇佣。租不到房子,被亲友所疏远或孤立等等(Lj et a1.,2008;Link&Phelan,2006)。
Scambler根据对癫痫病的观察提出了疾病污名的隐瞒―痛苦模型。他将污名分为了两种类型,即感知污名(felt stigma)和实际污名(enactedstigma)。感知污名是指担心被侮辱或被拒绝的感受,即没有受到实际的污名或歧视时对可能发生污名的担心,实际污名是指被污名者遭受的公开歧视或敌对。隐瞒一痛苦模型主要有4个主张:第一,已确诊患者在没有遭受实际污名之前,已经感觉到强烈的感知污名;第二,感知污名驱使患者首先选择隐瞒自己的病情,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实际污名;第三,由于较少人意识到患者的病。情,因此实际污名发生的机率和实例都是非常小的。最后。由于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影响患者生活较大的是感知污名而非实际污名(Scambler,1998)。
这一模型已经在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多种疾病污名研究中得到了证实。Steward等人(2008)在隐瞒一痛苦模型的基础上对229名印度艾滋病患者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实际污名通常会导致感知污名,但实际污名往往出现较少,而感知污名反而被更多艾滋病患者被试报告。Bogart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感知污名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影响非常大,几乎比疾病本身带来的伤
害要多。尽管这两种污名实际上是分别发生的,但它往往对艾滋病患者知觉为一种感受fBogartet a1.,2008)。这为我们试图消除或减少有关艾滋病污名的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消除患者的感知污名可能是比消除公众对他们的实际污名更加直接而有效的办法。研究者认为,当个体没有经历过实际污名时,他们有可能通过观察学习从其它艾滋病患者那里体会到实际污名的痛苦,称之为间接污名(vicarious stxgma),它也同样会导致感知污名的出现。遭受感知污名痛苦的艾滋病患者通常会隐瞒自己的病情,而在这一避免暴露的过程中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除了实际污名和感知污名,有些艾滋病患者还会承受自我污名(self stigma),即患者认识到公众对自己的污名后,认同和内化这些信念、态度或行为(comgan&Watson,2002)。在Mak等人对150名香港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污名的调查中发现,艾滋病患者自我污名的程度因人而异,但这种自我污名对他们的心理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自我污名也会降低其知觉到的支持程度,这将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心理痛苦(Mak et a1.,2007)。
2.2 对艾滋病患者家庭的影响
艾滋病污名不仅对艾滋病患者造成影响,还会伤害患者的家庭和亲友(Li et a1.,2008,曹广华,支玉红,刘莉红,刘高旺,张世霞,2009),发生连带污名。连带污名(Courtesy stigma)是指因为与被污名个体或群体有联系而间接获得污名的情况。研究表明,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和歧视在家庭中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这一现象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减弱的趋势。它不仅会影响到家庭的脸面,使整个家庭的社会交往圈变小,也可能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和睦甚至导致家庭的破裂(Li et a1.,2008;Zhou,2007)。但是,艾滋病污名对家庭的影响中也有积极的一面。在度过家庭最初的排斥和孤立后,艾滋病患者会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家庭能够为其中的其他成员提供支持以应对他们所遭受的污名和歧视。对艾滋病人自杀意念的研究中发现,家庭的关怀能够增加艾滋病患者生活的信心,让患者感受到关心,爱护,以及自身的价值(吴红燕,孙业桓,张秀军,张泽坤,曹红院,2007)。因此,有研究者由此获得启示。建议将家庭纳入将对艾滋病污名的干预范围以内,很多家庭在经过特殊的艾滋病教育和培训后,能够找到有用的应对策略,通过与其它艾滋病家庭建立联系获得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对于重视关系的中国家庭来说,这种针对家庭的污名干预计划可能会更加的有效(Li et aI.,2008)。
3 减少艾滋病污名的干预措施
3.1 接触假设
接触假设指的是被污名者与公众的任何形式的相互作用,它是污名研究中用来减少污名的一种办法(Heijnders&Van Der Meii.,2006)。心理学家Allport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提到,不同群体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地位平等的接触而减少彼此间的偏见(Herek&Capitanio,1997)。在艾滋病污名的干预过程中。接触被认为能够起到减少污名的作用。Herek等人1997年进行的艾滋病污名的追踪研究中对接触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与艾滋病患者有过直接接触的被试比那些没有过直接接触的被试更加同情和理解艾滋病患者,也较少回避或责备他们(Herek&Capitanio,1997)。Brown等人认为,与艾滋病患者更加个体化的接触能够降低对艾滋病的神秘感与误解,增加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Brown,Macintyre,&Truiillo,2003)。Zhou等人对北京的21名艾滋病患者进行的访谈结果表明,非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的积极接触,不仅帮助他们正确的理解了这一疾病,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艾滋病患者建构起一个良好的支持环境(zhou,2007)。然而,目前为止在艾滋病污名领域对这一干预措施的实证研究还十分少见,已有的结果或是从其它污名干预中的借鉴,或是对已经实际发生相互接触的结果的调查,还没有出现专门针对一般民众与艾滋病患者的接触而设计的实际干预项目。
3.2 知识传播
针对普通民众进行的艾滋病污名调查中,研究者普遍发现民众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常识缺乏了解,主要表现为对何种途径不会导致艾滋病毒的传播存在极大的误解(Herek,Capitanio,&Widaman,2002),而在艾滋病患者实际遭受到污名中,大部分的拒绝和回避是来源于对艾滋病毒传染的恐惧以及对病毒传播途径的不了解(B0gart et a1.,2008),甚至有的医护人员或艾滋病毒感染者本人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毒(Bogart et a1.,2008;Pisal et a1.,2007),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可以将艾滋病知识的传播作为减少艾滋病污名的一项干预措施,并且已有研究者以此作为干预艾滋病污名的实践项目。对928名纽约市民进行的电话调查发现,对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越多,对艾滋病患者产生污名和责备越少(Des Jarlais et a1.,2006),国内研究也表明,对艾滋病没有歧视和偏见的调查对象比对其有歧视和偏见的调查对象所掌握的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多(郭欣等,2006)。并且,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较高的学生群体愿意与艾滋病患者交往的比率也较高(邹艳杰,潘京海,马立宪,朱林,2006)。但是,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发现,仅仅向民众传播艾滋病知识来达到消除或减少艾滋病污名是不够的。一项在加勒比地区进行的艾滋病污名调查发现,在已经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对罹患艾滋病的人表现出歧视行为,这种污名来源于根植于文化或当中的信念,使人们认为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都是“罪孽深重”的。而感染这种疾病就是对他们的罪孽的惩罚(Anderson et a1.,2008)。以中国人为被试的调查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公众对疾病的传播知识有所了解,但这与他们对患者产生污名几乎没有相关(Mak et a1.,2006)。遵从归因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对患病原因的归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框架模型。在这一框架中,对疾病真实情况的了解对产生污名几乎不起作用,这种大众的观念或信念才是污名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建议在减少污名的努力中,不必大费周张的宣传疾病常识,因为这些常识与公众的基本信念相悖,不容易对公众的污名态度产生较大的影响。更多的努力应该放在改变公众对传染性疾病的归因方式上。
但大量的研究证明,知识传播确实能够对不了解艾滋病毒传播方式的民众起到教育作用,并减少他们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污名,因此,对艾滋病知识的普及与传播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由
于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不仅仅由于对艾滋病传播方式的误解和恐惧而造成,也有艾滋病的致死率高和一些信仰的原因,因此,仅仅对民众灌输艾滋病相关知识并不能导致污名态度的彻底改变。与其他干预方式相结合,如与艾滋病人增加接触或培训艾滋病患者的社交技能,可能会更好地减少艾滋病污名(Heijnders&Van Der Meij,2006)。
3.3 艾滋病患者的自我观念的改变
通常人们认为,减少艾滋病污名的方法主要是针对施加污名的人,目的在于改变他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但是近年来对感知污名、实际污名和自我污名的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被污名者所遭受的污名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源于自身对污名的预期,以及自我污名的影响。Thornicroft等人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中发现,感知污名与实际污名是彼此独立的,没有经历过实际污名的个体也有很大可能遭受感知污名的困扰(Thomicroft,Brohan,Rose,Sartorius&Leese,2009)。Heijnders等人在综合比较了多种污名干预策略后指出,污名并不是某些个体的行为,被污名者在对抗污名的过程中并不是消极的接受者,他们同样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Heijnders&Van Der Meij,2006)。已有研究中有一些是通过心理咨询的方法来达到减少污名的效果的。一项针对香港的艾滋病患者的认知行为干预的项目(Cognitive-behavioral Program,CBP)帮助患者辨别并改变关于自身疾病的不正确观念,提高他们应对压力的技能。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并减少心理压力。与没有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艾滋病患者相比,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心理压力明显的降低,同时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Chan et a1.,2005)。类似的实证研究虽然不多见,但该疗法在精神疾病的污名干预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corrigan,Kerr,&Knudsen,2005),可以认为减少被污名者的感知污名和自我污名,提升其自尊,是减少艾滋病污名困扰的重要途径。
Brown等人在综述了不同的艾滋病污名干预项目后也发现,多重干预措施或多通道的干预方法在许多研究中都出现过(Brown et a1.,2003)。综合不同学者对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艾滋病污名是由社会和个体共同的原因导致的,因此,对艾滋病污名的干预也需要是多方面,针对不同的对象的(Link&Phelan,2001)。
4 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针对污名现象的形成机制,归因理论往往作为一种较普遍为研究者接受的理论解释。但是归因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艾滋病污名研究的结果。这一方面与艾滋病污名的复杂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艾滋病污名的社会制度或文化原因造成的。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提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污名的问题,这提示我们对不同文化下的艾滋病污名现象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以验证社会文化对艾滋病污名的影响。因此,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归因理论,更多地尝试从社会的文化的观点来探讨污名的形成机制并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对艾滋病污名进行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当前研究通常以访谈或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较少有实验或准实验研究。早先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应用质化访谈,对艾滋病患者或普通民众的某一群体进行访谈,考察他们的态度以及所关心的问题。近年来,在UNAIDS(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发展各种艾滋病污名的测量问卷后。出现了许多开发验证测量工具,以问卷法调查艾滋病患者或民众的态度的研究。然而,无论是访谈法还是问卷法,最大的限制就是可能受到社会称许性的影响,而且由于没有对照组的比较,使得结论的推广受到一定限制。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采用更多的实验或准实验设计,或在调查研究中结合一些实验的处理。
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特点,尽早深入开展针对我国民众艾滋病污名的研究势在必行。根据UNAIDS的报告,截至2007年,我国估计有大约70万的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而且发病情况近年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UNAIDS,2008)。与世界各国类似,艾滋病相关的污名现象在我国也是十分严重的(Lee et a1.,2005;Liu et a1.,2006;Stein&Li,2008;Wu.Sullivan,Wang,Rothemm-Borus,&Detels.2007)。针对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污名研究已经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一些艾滋病高发地区,和艾滋病毒易感人群中进行(Deng et a1.,2007)。但艾滋病污名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艾滋病高发地区和高危人群中,普通民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民众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污名态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文化道德理论,探讨我国民众艾滋病污名的特点并针对具体国情制定相应的减少艾滋病污名的制度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