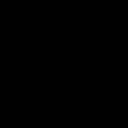从群众到公民:不可忽视的社团整合功能
时间:2022-09-02 08:40:16

摘要:西方国家的公民表达的是每个独立的个人都有他的抽象的天赋权利。这些天赋权利不仅表现摆脱贫困这样的经济性权利,更表现在享有政治权利方面,而西方的框架保证了这些公民权利的可实现性。相比之下国内群众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概念下公民所内含的政治生命力消失殆尽,所以建设中国的公民社会,应该从重塑公民观念入手。而社团的整合功能正是联系群众到公民的桥梁。
关键词:社会;群众;公民;结社权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1―0132―06
群众和公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从群众向公民的升华过程中,社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纵观西方国家公民观念的演变过程,很容易发现与社团的逐步壮大过程呈现高度的同构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西方国家发达的社团,也就不可能有今日内涵丰富的公民观念。
一、公民和群众: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西方国家,公民的概念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十八世纪的人权到十九世纪的政治参与权利再到二十世纪公民自治运动,公民的内涵逐渐丰满,表达的是每个独立的个人都有他的抽象的天赋权利。这些天赋权利不仅表现摆脱贫困这样的经济性权利,更表现在享有政治权利方面,而西方的框架保证了这些公民权利的可实现性,所以奥克肖特提出“主体在他们与授权的管理者和法律的执行者的关系方面来讲才是公民。”可以说,公民这个概念已经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表现在公民拥有免于被侵犯的权利,拥有公权不能进入的私域,也就是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即公民可以自由地决定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因此,柏林把不被侵犯和允许个人成为自己看成是个体和共同体两方面都是高度文明的标志。公民这个概念的政治生命力还表现在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方面,是去做某事的自由,它所回答的问题是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根据柏林的两种自由理论,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的界分,“积极公民资格型塑了政治议程:他们精心思考着这样的目标,即政府现在应该追求怎样有效的公共部门项目,以及如何评价公共部门项目的有效运作状况。”在这个概念中,已经不只包括直接选举权、结社权、表达权等,而且包含了社区自治、自组织和治理的理念。
相比之下群众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这个词就经常和群众连在一起使用,很快人民群众又被简称为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含义逐渐退却,直到其所内含的政治生命力完全消失。邹谠认为,中国的群众概念是从阶级的观念中引申出来的,“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例如要土地,要求男女平等。中国革命是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开始的,进而要求政治权利,要民主。”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并不是群众在中国的全部内涵,而只是其中之一,当然是最重要的一层含义,即群众对社会、经济权利的偏好,准确地说是政治精英们认为群众应该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社会、经济权利;第二层含义是:群众的概念通常蕴含着思想觉悟低下,类似麦格雷戈的x理论对人性的假设,认为普通人不仅懒惰、缺乏责任心,而且总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的要求和目标漠不关心,并反对变革、不求进取等,因此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所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建立在群众观念上的国家一定有一个强势的、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的产生基本不会受到群众的意志或者偏好影响。精英群体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和保护群众,这是时下地方政府改革中部分地区出现强人政治、推动地方经济超常规发展、并得到相当多民意支持的原因之一。第三层含义是群众参政能力低下,因而不能享有太多的政治权利,反对直接选举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一个反例就是村委会直选中的贿选问题。这里面被忽略的问题是,民主是一种习得的能力,尤其是从错误、失败和混乱中学习。因此,在发达国家的选举史中不难找到贿选和政党分肥这些与现代民主相悖的东西,这绝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知识;但正因为经历了这些磨难,发达国家才能够建立今日成熟的民主制度。或许可以说,西方国家公民较高的民主素养,得益于那里的公民拥有在民主程序中行使自己权利的学习机会。最后一层含义是,群众是没有自治能力的,因此群众要常怀感恩之心,接受各级组织的领导,听话和服从是好群众的最重要标准。而结社至今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还是一个负面寓意很强的名词,似乎人们只有出于不好的动机才会聚集,这种片面认识直接导致民间社团在中国的缓慢发展,进而严重影响了公民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二、社团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社会共同体,构成这个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自治的社区、丰富多彩的社团、成熟的慈善组织,以及依托社区而建的学校,它们是公民社会的中流砥柱。而被埃莉诺称为“自主组织”的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本文把这些自主组织看成是公民社会的毛细血管,它们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微循环系统,“很多成功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冲破了僵化的分类成为‘有私有特征’的制度和‘有公有特征’的制度的各种混合”。应该说,公民社会的上述构成要素不分伯仲,但是笔者认为建设公民社会的切入点应该是社团,社区自治正是建立在丰富多彩的社团组织基础上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结社权对于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堪比直接选举权对于民主的意义,所以下面简单梳理一下西方国家社团的发展,用以比较国内的差距所在。
西方国家的社团基本是建立在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基础上的,“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哈耶克认为人类是在不知不觉中,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因此人类才能够繁衍生息下来。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这种自发秩序的发展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各种丰富多彩的社团发展提供充分自由的生存空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民主制度的成熟与其结社权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当托克维尔惊讶地发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的时候,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仅四十余年。而托克维尔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法国,创办新事业都是由政府出面的,而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只有美国人选择组织社团,美国人甚至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似乎把结社视为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其次,政府为自治的社区和慈善组织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萨拉蒙的研究表 明,政府对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投入是十分巨大的,来自政府的支持是非赢利性组织的第二大收入源。在所有领域中34个国家的平均值是34%,但是在健康和社会服务领域,政府的支持超过收费性收益,成为第一大资金来源,分别达到50%和42%。最后,政府通过税收等政策对慈善事业进行引导。在慈善组织和各种基金会的运作、发展过程中,西方政府基本上置身事外并坐享其成,唯一做的事就是政策支持,既包括直接的立法支持、免税政策、资金支持,也包括政策的间接引导,例如西方国家普遍征收的遗产税,累计税率非常高,而慈善捐款则有种类繁多的免税政策,这也间接促进了一些富翁的捐款决心。
三、影响社团在中国发展的原因
相比之下,国内的社团运动尚处于缓慢发展状态,难以担当道德建设的重任。首先,结社权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1965年全国性社团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约6000个;进入80年代中叶后,伴随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的社团建设开始出现勃兴之势,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已猛增至1600个左右,地方性社团约20万个。但是89年‘’之后,社团批准权收归民政部,社团的发展脚步明显放缓:1997年全国性社团有1848个,地方性社团近18万个。能够查到的最新数字是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社团总数是191946个,分别为部级社团1730个,省级社团21506个,地级社团56544。一个好的趋向是2006年新增社团数是22308个;不好的趋向是,社团仅仅作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的中介角色并未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原体制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非行政隶属关系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情况下,主动敞开自己的组织系统,通过挂靠关系、业务主管关系、党组织延伸、官办、半官办全国性社团组织扩张与延伸的关系,将各种民间组织联系在扩张了的行政组织系统之下”。这种社团的独立性很差,“国内77%的社团领导位置由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的领导所占据。”例如司法部就通过其创建的全国律师协会制定律师事务所的行业规范,每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审查等对律师事务所进行行业管理。
其次,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国内的社区自治存在先天不足。社区自治存在的前提是有限权威的形成,即人民让渡出来的公共权力不是被某一级政府所独占,而是被某一些政府所分割。表现在西方国家框架下的两权分立和三权制衡的共存格局,这种格局一定是多中心性质的,其中“没有一个机关或者决策机构对强力的合法使用拥有终极的垄断,‘治人者’与‘治于人者’都能够接受法律的‘统治’,并被要求服务于‘治于人者’。”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可以说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而且在权力绝对集中的模式下,地方政府的独立政治之生命力也极其有限。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全面确立,中央集权的体制发生了很大改变,放权、放松管制和管辖权下移,都是把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现在,地方政府已拥有很大的自,但是回归社会的权利却十分有限。笔者认为这是体制改革中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中央集权的弊端不会因为变成地方集权就消失,其危害可能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国家药监局从独立到回归的10年风雨历程就是一个显例。权力下放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如直接选举权、结社权、表达权的完善,否则将意味着权利对权力制约的失灵。如果这种情况下中央过度下放权力,那么在既没有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又没有权利对权力制约的情况下,等于让地方政府拿到了一个在贡斯当看来必然带来罪恶的武器,“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必定构成一项罪恶……应当反对的是武器,而不是掌握武器的手臂……对于人的手来说,有些东西的分量是过于沉重了。”所以发达国家的权力变更的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使权力回归社会,美国自里根时代就开始了社区自治热潮,公民享有的民利不仅保证了社区自治的可实现性,而且保证了结社运动在西方的多元化发展。也就是说结社并不总是和功利目的相结合的,虽然这可能是结社的最主要动力;更不是以政治目的为主,虽然一直不乏社团把某种政治宗旨当成社团的目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缤纷:娱乐性、公益性、服务性、发烧友,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目的,例如今年年初发生在北京王府井的“快闪定格”,这样的聚集很难用是否有意义来形容,但是毫无疑问它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事实上这样做让这些网友感觉如此好玩,以至于他们打破了“快闪客”快来快走的规矩,自动聚集在一起鼓掌庆贺,并在20分钟之后重复表演一次,过足瘾后才散去!
第三个原因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力,和发达国家对社团发展的普遍性政策支持相比,中国尚存在很大差距。以免税为例,国内的免税手续十分复杂,恐怕这些繁琐的手续本身就足以让国人对捐款退避三舍。不仅如此,由于对公益性捐赠的界定十分模糊,国内有关部门在执行免税政策时经常出现偏差,例如为农村兴建防洪改造工程等公益事业都得交税,已经严重挫伤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一位人大代表在参加‘两会’时就公开抱怨自己的100万捐款,居然要缴60万税。他认为很多企业家都很有爱心,是捐钱扣税让很多人失去了动力。2006年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曾经这样抱怨,“中美人均GDP相差38倍,但中美人均慈善捐款额相差7300倍!”此言一出即在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但真的仅仅因为中国人没有爱心吗?也许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弗。威茨的话才道破了真谛,“现在中国的慈善捐款少,不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恐怕是现实的体制问题。”
最后,有关政府部门对社团的不信任,导致现有非政府领导的社团难有用武之地。应该说,近年来志愿者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了蒸蒸日上的良好势头,除了奥运会对志愿者的强势拉动和各级组织领导的志愿者队伍以外,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自发的志愿群体,一些非政府性的组织对志愿者的动员能力也得到空前提高。例如2008年年初南方发生冰灾、冻灾之后,志愿者就迅速行动起来,仅广东省动员的志愿者就累计达6万多名,志愿服务人次超过20万,服务总时数200多万小时。但是这些风光数字背后的隐忧也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志愿者的漠视和不信任。据东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拓展服务总队的负责人介绍,在广东春运滞留最严重的几天,志愿者在东莞火车站却遭遇冷遇,两天后志愿者协会通过对火车站的“公关”,才找到一些协的工作,但志愿者们的积极性却因此大受影响,“我们在火车站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旅客,却不知道从何做起,最终变成无所事事。”笔者注意到广东市民参加志愿者十分踊跃,仅几天时间网上报名就召集到志愿者4000多名,但是经历这样的尴尬之后,不知道这些人今后是否还能保持做志愿者的热情!
东莞火车站和相关领导部门为什么不欢迎志愿者?相关部门后来的回应是因为机制不健全,目前 志愿者并未被纳入到广东应急方案预案中。但是这些恐怕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志愿者不归他们直接领导;不像武警战士那样不折不扣地执行任务,不好指挥调动,难以和政府步伐一致;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即一旦社团性组织介入,日后总结成绩时也很难划分清楚,毕竟中国人已经太习惯于在大灾大难过后听到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人民军队之类的话,虽然这场冰灾、冻灾之后也有部分媒体喊出了‘感谢志愿者’这样的话,但是尚不能成为主流声音。而且政府部门总是很骄傲的,至少目前还不习惯与民间组织并肩作战。因此,在这样一场百年灾害面前,我们只看到政府一个救助主体就毫不奇怪了。虽然政府的动员能力很强,包括调动4300名警力,对广州火车站进行全方位防控,武警和警察组成“人墙”,将旅客分割成小方块以防止踩踏事件的发生。但是却无法解决数十万滞留旅客对食品、饮用水和大衣、棉被的需求,而这种状态整整持续了数十天,“不时有乘客晕倒,被送到临时医疗中心治疗”。笔者查到的最早来自个人的救助食品是一位来自深圳的、以嘴巴写书法为生的残疾乞丐,他与父母及多名朋友自费2604元购买84箱共1008碗碗面,让罗湖区春运指挥部转赠给滞留在深圳火车站的乘客。就这样,中国“社会”在这场百年不遇的雪灾降临之际变得无动于衷。而更值得我们反思的也许是,这些数以百万计被饿在、冻在路上的、却大多没能得到社会及时关爱和帮助的人们日后将会怎样回馈社会?
四、让社团成为公民的精神家园
杜威认为,工业化和社会流动的增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回归地方家园的行为,也不会摧毁人们的社区情感,相反,“它能够刺激新思想的产生,能够防止过去因为过分专注稳定性而导致的僵化和停滞不前。”民众时常在情感上强烈地归附于他们的社区,将社区视为大都市生活的避难所,因此杜威强调,民主必须始于公民的家园一即我们所在的邻里社区,社区应该成为培养公德的首要组织,“借助于家庭和邻里组织,公民性格得以稳固,公民所特有的草根思想得以逐步确立。”这意味着植根于社区的各种社团、慈善组织不仅是公民道德的塑造者,而且为公民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使社区居民和大量的外来人口都能在那里找到归属感。对于独立的个人而言,归属需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马斯洛把人类对归属和爱的需要看成是人类的最基本需要,它们在马斯洛的需要等级中处于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的连接处,是一种具有社会倾向的需要,“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满足了,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他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做出努力。”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斯洛归属感的构成部分――朋友,远非在汉语中现在已经被相当功利化地使用的‘朋友’一词所能涵盖。马斯洛所说的对朋友的需求实质是个人对来自社会关爱的需求,这种需求在西方社会表现为个人对自己所属社区的精神依赖,以及公民对自己所加入的各种社团产生的归属感。所以马斯洛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应该包括两个完整地构成部分,一是个人对家人和朋友的强烈依恋,这相当于国内所说的个人小天地,如果没有这部分个人会产生马斯洛所说的“空前强烈的失落感”;另外一个构成部分是对来自家庭、朋友之外的关心,也就是来自邻里社区和社会的关爱。事实上只有区分开这两种不同的关爱,才能解释国内普遍出现的归属感缺失:因为大多数中国成年人不仅有家庭,还有朋友,但是依然感受到了马斯洛所说的没有朋友和爱人才会感到的“强烈的孤独、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浪迹人间的痛苦。”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来自小圈子的关爱与来自社会的关爱是不能够相互替代的。准确地说,这是个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归属感需求,其不同程度可以用赫兹伯格对满意和不满意关系的论证来说明。赫兹伯格认为正如增强或减弱刺激视觉的光线不会对听觉产生任何影响一样,消除导致员工不满意的因素,并不能使员工在同一过程中获得满意的感觉。换言之,消除了工作中的不满意因素,只能使员工产生没有不满意的情绪,而只有消除了影响员工工作的没有满意的因素,才能使员工达到满意。就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本身而言,如果我们借用赫兹伯格的这个理论,就可以这样说,来自家人的关爱和家庭产生的归属感,就像赫兹伯格提出的保健因素一样,如果没有会造成强烈的不满意感,但是得到满足后却只是消除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但并不会给人带来满足感,这时候的人们处于一种“既不是满意,又不是不满意的中性状态。”而来自社会的关爱和由此产生的归属感,则相当于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只有这时个人的归属感才会真正得到满足,个人的孤独感、疏离感和无助感才会消失;而没有孤独感的个体才会产生幸福感,由充满幸福感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社会。因此西方国家的公民通常“有较强的社区归属感,虽然他们比较频繁地从一个居住社区迁移到另一个社区,但所到之地总对该社区有一种认同,并产生强烈的社区环保意识、邻里互助意识,并参与到社区的各项活动中去。”也正因为如此,奥斯本和盖布勒才把来自政府的帮助叫服务,而把来自社会的帮助叫关心,认为关心和服务是不同的,“关心是人类给予伙伴的真正的温暖;关心是家庭克服悲剧时亲人的支持;关心是一个人卧床不起时帮助者伸出的仁爱的手。”而政府提供的服务则是冰冷的例行公事,得到社区关心的人会产生幸福感,但是得到政府服务的人却依然会感到孤独。萨拉蒙等人对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后得出很多惊人数字,但是公民社会的功用远非上面那些惊人的数字所能涵盖。西方的志愿者不仅仅提供服务,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表达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倡导功能,发现那些被忽视了的问题、保护基本民权,允许愤怨的群体将其所关注的问题扩散到更大的公众,引起他们的关注,并汇集各方力量去改善这些人的境遇。第二文化建设功能,例如为艺术、娱乐等活动提供载体,建立交响乐团、足球俱乐部、读书俱乐部、兄弟会、行业协会等,通过这些来丰富社区生活。第三参与社群建设、累积社会资本的功能,因为“参与结社就是在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它教给人们合作的规范,从而把它带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萨拉蒙的研究表明,在33个国家中32%志愿者的活动集中在这个领域,表现最明显的是志愿者在文化和娱乐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这占所有志愿者工作时间的41%,而据研究者估算在36个国家中“志愿者的平均人数至少达到1.32亿,”这样换算下来志愿者总计花在表达性工作上的时间是相当惊人的。
从这样的视角看,社会归属感对和谐社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社团就是公民归属感的承载主体,国内也正是因为这部分功能的缺失才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就在2008年的情人节,北京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丈夫入狱后携5个月大幼子跳楼自杀,《京华时报》在报道的最后这样写到:邻居们认为该女子令人同情,但是其行为却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如果纳入本文框架,这种悲剧就很容易理解!所以,如果说西方社会是个人为社区作贡献(志愿者),社区为个人服务(志愿者的服务对象)的良性循环,那么国内的基本状态就处于个人既不为社区作贡献、也得不到社区关爱和帮助的恶性循环中,而这种状态的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