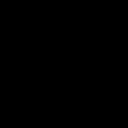孙隆基:旧的精英阶层正在被摧毁
时间:2022-08-28 08:21:32

整个20世纪从启蒙到革命后,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时期的“到民间去”,体现了知识界对底层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知识精英承担了启蒙的任务,“群众”成为精英主义理念下的他者。到20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思潮汹涌,知识精英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与大众的关系逆转。孙隆基先生从 “群众”概念的建构,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本质,谈到今日的精英与士大夫传统的区别,让我们在重新审视20世纪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时,获得新的视角。 精英和作为他者的“群众”
唐小兵:回首整个20世纪,知识界和政界对底层社会有一个浪漫主义的想象,尤其在革命文化里面,一切美好和道德都在民间。“五四”时倡导“到民间去”和新村主义,1930年代在《申报》、《现代》提倡“大众语”,认为“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太精英和欧化。一方面是在“群众崇拜”的时代里将民众无限神化和美化,另一方面是这100年来,传统中国的“夷夏之辨”论述在20世纪初被西方人“文明-野蛮”的分析框架取代后,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一直到今天都是主流话语。台湾的作家柏杨、李敖、龙应台也在“国民性批判”这个文化脉络里面。
孙隆基:中共里面也有本土派和国际派。有一些是留洋回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就更乡土化,所谓“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矛盾。1919年以前,引用勒庞的话来说,群众形象是负面的,甚至陈独秀都怕学生上街以后会变得非理性,那时候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和还是不完全相同的,一个还是精英,另一个是走上街头。精英看见民众走上街头还是会有不安。当时元老胡汉民却写了一篇文章肯定群众。1919年以后中国的政党都开始肯定群众的价值。
唐小兵:清末随着科举制度废除、王权瓦解、城乡之间的士人流动,家族、宗族制度的衰落,一个谭嗣同所谓的“冲决网罗”的个人呼之欲出,但10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并未随着传统的共同体的瓦解而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自主的个人,反而在消费主义文化下,借用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中所讲的,变得更加狭隘、平庸、自恋,“可悲的自我专注”;在传统的社群文化瓦解以后,个体的生命意义来源更加单一了。传统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立人”的资源?
孙隆基:传统包括很多面相,我们不能将它单一化。不要以为西方只有个人主义,其实西方还有社群主义。近来,社群主义在美国大众文化中也开始抬头。1960年代的婴儿潮那一代人,个人主义搞得太厉害了,核心家庭瓦解。好莱坞也想补救这一块,好像又和美国的宗教右翼有些合流。这两种思潮都是现代思潮,所以社群主义不等于传统。要在传统中找无政府主义也能找得到,比如老庄;无神论也可以找到;嬉皮行为也可以找到。就是儒学也有很多种,比如“内圣”,有人认为“内圣”和“外王”应该分开,要讲“政治儒学”。但是政治儒学是不是现代的发明呢?因为儒学历来就是政治的。你刚刚讲到群众的问题,群众也是一种论述,不要将它本质化。
唐小兵:但是革命论述往往是将群众本质化的、纯粹化的。
孙隆基:革命论述不是实证的,也是建构起来的。革命论述中可以建构群众,超人哲学中也可以建构群众,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话语。比如“自然”这个意符需要他者的对照。如果他者是“文明”,或者是“超自然”,那么同一个意符的意指就不同了。还有“不自然”,就是“变态”的意思。“群众”也是,你到底是共产主义语境里的“群众”,还是无政府主义语境里的群众,还是尼采派语境里的“群众”?二战以后,西方世界暴民心理学没落了。这有学术的原因,比如行为心理学的挑战,认为个体心理是不成立的、不可测量的。这样一来,个体心理学就被瓦解掉了,更不用说集团心理学。另一方面,美国人强调理性的控制,一个人没有理性控制就完蛋了,而群众正是淹没个人的东西,因此这个概念缺乏卖点。
因此,今天讲“群众”,可能还是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精英是主体,群众是树立的一个他者。鲁迅先生一直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的“群众”是指哪一群人呢?全体中国人还是一部分精英?在20世纪的中国,“群众”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政治的概念,甚至是美学的概念。 今天讲“群众”,可能还是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精英是主体,群众是树立的一个他者。在20世纪的中国,“群众”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政治的概念,甚至是美学的概念。 俄国民粹主义:“赎罪的贵族”
唐小兵: “五四”新文化的时代也被称为是现代中国的启蒙时代。你提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这3种类型的个体。有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就有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的“被启蒙者”。“启蒙”一词本身,如它的英文“Enlightenment”,就有一种像要把光明(light)召唤出来的意味。中国现代的启蒙者更多是现代知识分子,包括严复、梁启超还有胡适等人,都是来自一个独特的时代―张灏先生形容为“过渡时代”,而启蒙的对象则更多是像鲁迅先生讲的那些需要被启蒙的蒙昧之人。从20世纪的10年代到20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潮从启蒙到革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比如陈独秀就是一个典型,早期是启蒙者,后来变成革命者,当然革命在他看来可能也是一种启蒙,一个要唤醒和动员民众的过程。
时代就有一个说法,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或者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可以看出,他说自己是“高等游民”、“废物”,觉得自己身上有“文人意识”是不好的,他是把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角色整个投射到自己身上。恽代英也感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个工人”,还有的秘书李锐与妻子范元甄的通信集《父母昨日书》、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的《李慎之检讨书》等出版的文集、日记、书信、检讨,从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中被迫接受改造的处境和命运,更不用说已成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知识人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在革命中倒转过来,降落到被改造的地位,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整个20世纪从启蒙到革命后,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的巨变?
孙隆基:革命是启蒙的结果,像法国大革命之前有启蒙运动,罗伯特・达恩顿有本书叫《启蒙运动的事业:〈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对那些愚昧的群众,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将他们唤醒的过程,比如他们以前只会逆来顺受,现在也可以做人了。不是说旧日的群众今天倒过来对知识分子施虐,而是说,他们本身的启蒙过程是暴力的,知识分子只是摇摇笔杆,顶多当个文化官,而群众是经过革命的洗礼的。当然很多劣根性也跟着显示出来,中国人卑劣的行为多是躲在群众里做出来的,叫他一个人做绝对不敢。
唐小兵: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传播到中国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本来的面目是怎样的呢?
孙隆基:俄国的民粹主义,我觉得跟斯大林的统治还不完全一样。而且“民粹主义”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名词,最早民粹主义还是有点精英主义色彩的,像赫尔岑(著有《往事与随想》)的主张是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他主张要结合俄国自身道路,结合特有的“村社”制度,这是一种斯拉夫本位主义的话语,认为“我们俄国人天生就是社会主义,不需要输入”。但西化派认为,俄国“村社”根本不是现代的组织,不过是输入北欧瑞典、波罗的海(普鲁士当时还未崛起)一带的国家机器,为了便于组织农村、征收赋税才塑造成的,是源于德语区的,后来俄国皇后凯瑟琳一世也是从那里来的。 真正的俄国“民粹派”叫作“还罪的贵族”,是去赎罪的,所以要到民间去。他们认为,自己祖宗多少代都在剥削农民,而自己现在又不劳动,是多余的人,因此必须跟农民结合。
这样一来,村社就成了笑话了,说是公社也不像,是彼得大帝制造的一个其实摧毁了俄国社会的国家机器。为了征税方便,把一个村子的人集中在一起。但到了托尔斯泰则不是这样。托尔斯泰的主张可以说是“越愚昧越落后就是越完美”,他把这叫作新基督教,而且很肤浅,他深刻的思想在如此“民粹化”后就化为乌有了。真正的俄国“民粹派”叫作“还罪的贵族”,是去赎罪的,所以要到民间去。他们认为,自己祖宗多少代都在剥削农民,而自己现在又不劳动,是多余的人,因此必须跟农民结合。于是穿农民的衣服到农村去,手里不长茧,从来没劳动过。农民不知情,怀疑他们是密探,或者是捣乱分子,就将他们举报给警察,最后被抓,这就是“到民间去”了,很反讽的结局。过了这股热潮,后来到民间去就非常清醒,是半启蒙的态度。比如他们是教师,或是乡村医生,但认为自己是来为农民服务的,因为掌握农民不懂的专业知识。这大概是1870年代以后,亚历山大二世要搞地方自治、地方建设的时候。这时“到民间去”,就不是救世的了。这与之前不同,1870年代最狂热的那种赎罪的民粹主义也就是昙花一现。 将精英与传统士大夫区分开来
唐小兵:很多年前,余英时先生发表过一篇长文《反智论与中国的政治传统》。今天回头看20世纪中国的历史演变,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关联?比如说在今天,公共知识分子在成为一个贬义词,被称为“公知”,这些人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的言行被认为不务正业,写政治评论被指责是跨界说话,甚至被认为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所以知识论述也站不住脚。如今好像变成这样一个状态,知识精英近乎全部破产。而对民间社会,我和鲁迅先生看法相同,我并不认为它就是乌托邦式的,也有很多恶的力量,比如“全能神”教就孕育于民间。如果精英崩溃了,民间也黑社会化了,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孙隆基:说到精英的“崩溃”,台湾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比如“黑金政治”。精英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和传统士大夫分开来。今天的华人知识分子,像余英时,他们的形象总是和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现在的“精英”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娱乐界、工商界,文化界只是一部分。而且在文化界,现代主义是最精英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去精英化的。
比如现代主义艺术品,越看不懂的价值越高,只有参加私人俱乐部才能看得懂,是圈内人才懂的笑话。而且,现代主义的艺术品多是在台座上,背景多是纯白的,而后现代主义强调艺术品要跟环境融在一起,多用玻璃来反照周围环境。后现代主义很多东西包括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贝多芬的音乐,变成了“小众”的,或叫作“特殊的观众”。现在,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量身定做,现在的消费群体已经有很多种,不只“精英”和“大众”两种。因此现在是大众文化胜利的时代,但大众文化胜利也并不是说精英文化就被消灭,它只是变成小众化,变成了“副集合”(subsite)。精英文化也只是文化中的一种,认为一些人有特定需要就为他们定做。比如好莱坞走的路线,得奥斯卡奖的那些作品都不会很俗,但也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作品。
后现代就是这样,但中国传统士大夫就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觉得天下没有我们靠谁呢?所以叫作“当仁不让”。
但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精英,有些甚至连那个行业都是刚刚出现,我们都没听过。因此旧的精英阶层被摧毁,但我们的社会本身在发展,会不断制造新的行业,而每个行业都不断制造新的精英,正如以前讲的“行行出状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一本书《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群众的智慧。而群众未必是非理性的,他们做的决策很多是集合集体的意见,有时候胜过一个他们的首脑。我后来有一篇文章,《从十个角度分析“现象”》,就是从暴民心理学开始,说到暴民心理学为什么不流行了,尤其提到写《群众与权力》的埃提亚斯・卡内提,他1960年的东西到198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时才公布,这时候已经过时了。暴民心理学真正最流行是在勒庞、索烈尔的时期,还有弗洛伊德也写过群众心理学。弗洛伊德是在1930年代初期,用精神分析学来谈群众心理,认为群众是没有超自我的潜意识流,超自我就指领袖,即群众只有一个头脑,而事实上,本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识―“超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