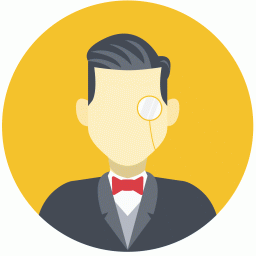怀念洪门口
时间:2022-08-28 07:20:34
一
多年前,同学从上饶回鄱阳曾亲历这样一则笑话。
放暑假,长途汽车上。因离家大半年了,同学突然想起家乡这时节应该到了收割稻子的时候了,于是便随口问起坐在前排的一位从家乡来上饶的女士,家乡的稻子是不是成熟了。不想那位女老乡语出惊人:“我不知道呀,我是洪门口的!”
同学返校后跟许多老乡用戏谑的语气绘声绘色地讲起这个笑话,笑爆全场。
洪门口是家乡一座不大的煤矿,与乐平接壤,毗邻我们村,所以我们对洪门口的了解,并不亚于我们对隔壁村的了解。
在那位女老乡眼里,洪门口不属于乡村,仿佛是一座城市,自然对农事不了解。这本是人之常情。对一般人而言并不可笑,但对于了解洪门口前世今生的我们来说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用现代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说就是“雷人”!
洪门口一个多大地方?除却私人开采的煤矿,国营煤矿只有立新、八一、九一三眼矿井,煤矿工人充其量不过200人,且都来自周边农村;矿工家属房基本上沿马路而建,或傍水库,或靠山脚,与农村并无二样,周围都是田野,一出家门放眼就是连绵不绝的田野,蛙声,稻香,农耕……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即使不种田,耳濡目染,真是土生土长的洪门口人,就一定能知道稻子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就像他们熟悉什么是煤炭,什么是煤矸石一样,了如指掌。
所以那位女老乡高高在上的“城市人”的本位思想,在我们看来,固然就有无自知之明之嫌疑,更何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计划经济的自然瓦解,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今的洪门口煤矿早已今非昔比。体制的转变,资源的枯竭,那红红火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国营煤矿早已经解体,绝大多数工人都已“告老还乡”回家种田种地去了。留下的也只能靠基本的退休金生活,因没田没地绝大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不上农村人。作为现代的洪门口人,哪里还有骄傲的资本可言?
但就情结而言,曾经的洪门口,在童年,还真就是一座我心目中向往的城市!
二
已经记不起自己第一次到洪门口大概是多大了,但第一次去洪门口绝对是受童年的伙伴――明生所怂恿,这点毋庸置疑。
理由非常简单。明生家世代都是洪门口的煤矿工人。每日深夜十一二点或下午三四点都是煤矿工人准时上班的时间点。明生的外公、父亲和舅舅他们一大队人马都会用长长的斧头柄背着一只黑得发亮的蛇皮袋从村口的新桥走过,他们神情凝重而庄肃,似乎每次的上班都是一次与家人的生离死别。用煤矿工人自己的话说,他们都是吃了中饭还不知道是否有晚饭吃的人。高危险的行业,锻就了他们沉默寡言的性格。
他们是村里最守时的人,只要听到他们早起的咳嗽声或匆忙赶路的脚步声从窗前穿过,大概就知道到了几点了。他们像生物钟一样,作为洪门口煤矿临时的职工在村里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为了讨生活,俨然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传承。
当然,明生带我们去洪门口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向我们炫耀他有家洪门口的亲戚――他大姨家。
在那个计划经济束缚的年代,特别是在上个世纪那个国企最辉煌的八十年代。在我们眼里,洪门口的煤矿工人俨然过着城市般的生活。因为他们远离了繁重的农耕劳作,也因为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热切向往,固然让我们这些与洪门口八竿子打不着的农村孩子,对明生无比的羡慕。
记得明生的大姨家就住在进洪门口矿区马路边的一个山窝窝里面。那里有纵横两排低矮的青砖瓦房,住着洪门口煤矿最底层的井下职工。拥挤、脏乱、嘈杂,是我对洪门口的第一印象。屋里一片漆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纵使白天每家都点着一盏昏黄的电灯。
印象中最深的是明生带我们去看他大姨家卧室内的一个大坑。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床底下,黑漆漆的陷下去了一个足有我们那时身高一半的圆形大坑,类似于一口废弃的水井。现在想起,这些深坑的形成都是因地下被掏空而引起的土方塌陷,对那二排低矮的危房而言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那时,我却对他大姨家充满了盲目的向往。冬日的中午,煤炭在火炉子里肆无忌惮地燃烧成淡蓝色的火焰,舔舐着屋内狭小的空间,给人无比的暖和与温馨之感。炉上的开水壶喷着热腾腾的水蒸汽。从小小的窗口呈烟雾状迅速地逃离。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温暖的中午,致使多年后每当读到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俄罗斯贫穷的村庄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明生的大姨家。想起那煤炭燃烧时特有的蓝色火焰。
在我那时幼稚的思维空间里。洪门口什么都是好的,甚至包括那个深陷下去的大坑。就像小时候表哥国荣对我发的一个誓言:长大了,一定住在水泥厂里。在我们幼稚的心里,一个人所居住的地方和环境将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繁重而艰苦的农村体力劳动,从小就促成了我们背离农村逃避苦难的心愿。
明生与我同龄,出生的月份比我还小,但他说话非常具有鼓动性,经常会诱惑我们陪他一起去他大姨家。今天明生说洪门口水库边上有一片杉树林,那里有许多八哥,很容易就可以抓到。对一帮天性好动的男孩子而言,这是极具诱惑力的,但往往是去了多次都没有抓到一只,好不容易抓到了一只,当然得留给明生了,因为是他洪门口的建华表哥带我们去的,这点时务我们还是懂得的。明天明生又说,洪门口子弟学校门口有蚕买。蚕只吃一种叶子,会吐丝结茧,能抽丝织布,产卵多,第二年春天会孵出好多好多的小蚕。于是我们一伙人便冒雨带上平日里舍不得花的零花钱兴冲冲地赶上五六里山路。就为了看看或买到明生所说的蚕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虫子,怎么会那么神奇。作为领路的报偿,买到之后我们每人还得贡献一只给明生。
这就是明生带给我对洪门口最初的记忆。
三
真正摆脱明生的诱惑并开始了解洪门口。是在读三年级之后。
印象中,洪门口最令我神往的就是那幢坐落在最繁华地段的电影院了。这是一栋老式的俄罗斯筒子楼建筑,是中国五六十年代特有的建筑模式,与我以后看到的其他地方的老式电影院没有二样。虽然仅有一层,但在我心目中却是那个年代最恢宏的建筑。电影院不亚于是洪门口的心脏。就如同天安门之于北京一样重要。洪门口煤矿每年都在这里请县里的赣剧团唱戏。请县里的赣剧团唱大戏,这是洪门口一年之中最盛大的事情。据说开戏的那几天电影院门前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热闹非凡。这是那个缺乏娱乐、对戏剧着魔似崇拜的年代,周围十里八村做点小买卖的,有点闲钱的人像潮水般地涌向洪门口,享受一次感官上难得的精神大餐。因买不起门票,我从来没去过。
据母亲回忆,小时候外公曾带她去过一次。每次说起那次看戏经历都让母亲心惊胆寒。那时母亲只有九岁,外公给她买了一根比她当时的手腕还粗的甘蔗,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母亲幸福地把它扛在肩上,一直舍不得吃。
幼小的母亲被推推搡搡地夹在拥挤的人群里甜蜜而艰难前行,一不留神,紧紧握在手里的甘蔗竟在光天化日下被一个男人给抢走了。也许,正是母亲这份遗传的恐惧,才让我抵制了每年想去洪门口凑热闹的诱惑。
直到读三年级的“六一”儿童节,因为听说那天洪门口电影院会专门为孩子们放一场电影,洪门口的孩子看电影是不要票的。我们系上红领巾混在洪门口煤矿子弟学校的学生队伍里,也可以轻易蒙混过关。在表哥国荣的怂恿下,我终于决定陪他一起去冒一次险。
国荣从小就胆子大,刚到电影院门口我还没有摸清楚地形,他就钻进了第一批进入电影院的队伍,轻轻松松地进去了,他坦然自若,全然没有一丝做贼心虚的表情。看着他镇定自若的样子,我既羡慕又担惊受怕,仿佛是自己犯了错一样。呼吸急促,冷汗直流,满脸涨得通红。眼看整个电影院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焦急却又顾虑重重,在国荣榜样的驱使下,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在最后一批进人电影院的学生队伍后面,手足无措地踟蹰前行,心头那种紧张感,时时撞击我脆弱的心脏。
时至今日我依然还能记得当时的紧张与害怕,如果不是那位领队老师的疏忽大意,我想我肯定是第一个被赶出电影院的人。
也许正是因为那次“偷窥”的得逞,近三十年过去,我依然还能记得那场电影的内容――《闪闪红星》,对潘冬子勇敢、机警和聪明的记忆竟然是那么刻骨铭心。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以后我和表哥国荣隔三差五的就会去洪门口电影院碰碰运气,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站在场外的院子听里面激烈的枪声和紧张的鼓点,全神贯注地陶醉在对电影的想象当中。纵使看到了,也只是卖票的偶尔大发善心,在最后几分钟让你挤在门口看看演员表而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洪门口电影院率先引进了录像机。那时。港台武打片刚刚在大陆流行,像《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霍元甲》《再向佛山行》等一系列经典武打片如海潮般地铺天盖地涌来,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港台热”、“武侠热”,当然也波及了小小的矿区――洪门口。
当时,年轻人都以能看到港台武打片而感到自豪。但票价很贵,每场6角至1元不等,对我们这帮身无分文的农村孩子而言,简直就是天价啊!每次挤在电影院门口,我们也只能是感受下武侠的气场而已,每当散场,看到一个个情绪激昂、热情饱满的年轻人雄赳赳气昂昂地从电影院里神气地走出来,都会引起我们无比的羡慕和景仰,仿佛他们就是刚刚从录像里走出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大侠。
但我们有个同学却每次都能自由出入电影院。他就是洪门口煤矿矿长的小儿子――小徐。矿长是我们村里人,平日里喜欢耀武扬威装腔作势,好像谁都是他的部下一样。不过。我们很难得见到他一面,虽然我跟他儿子小徐非常要好。
小徐比我大,高我一级,是我印象中第一个冬天用保温杯带包子吃的人。
每当矿长父亲不在家时,小徐就会带我到他家看小人书。那个许多家庭连吃饱饭都要精打细算的年代,我这位阔少爷同学就拥有了一整箱子的小人书,他把箱子一扣,小人书就山一样地堆在我面前任我挑选,实在令我羡慕不已。他偶尔还会带我去洪门口他姐姐家玩。他姐姐在洪门口车站卖票,单身一人就住在电影院附近,所以小徐只要到了洪门口,他姐姐就会送他进去看电影或录像,而我只好在电影院外整整等上一个下午,然后津津有味地听小徐给我们讲电影或录像里的精彩故事。
记得一次,也许是因为录像不是很精彩,观众不是很多的缘故,放到一半的时候,电影院突然决定降价,小孩子只要1角钱就可以进去。相比较平日里6角至1元的票价,我真的是心动了,便向小徐的姐姐借1角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向别人借钱,也是继《闪闪红星》之后,我看得时间最长的一次电影。
对于那1角钱的记忆,我依然记忆犹新,心存感激。
四
在童年,洪门口不仅是座我心目中的城市,更是一座浪漫之都。
农村的年轻人每当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髦点的男青年结婚前都会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把害羞的女孩驮过新桥去洪门口逛街购物,就像《人生》里高加林和刘巧珍“进县城”一样,引来河边洗衣服的女人许多的艳羡和嫉妒。
说是街。其实只是一条铺了沥青的柏油马路。路旁有寥落的几家小商店,洪门口供销社,便是整条街人气最旺的地方。供销社的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印象最深的有画着两条红鲤鱼戏水的搪瓷脸盆、高级的茶色玻璃杯、土灰色的凤凰肥皂、各种纯色的布匹,还有柜台上玻璃罐里装满的水果糖……货架被木制的货柜围着,年轻漂亮的售货员慵懒地靠在货架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有说有笑地聊天。每次看到她们那傲慢而休闲的眼神,都会使我自卑地缩小成一团,纵使想买东西,也是带着敬畏小声敛气地询问,从不敢理直气壮地吆喝,更不用说挑三拣四了。那时,我认为当个供销社的售货员应该是吃香的职业。要吃有吃的,要喝有喝的,她们的服饰应该是当时洪门口引领时尚的风向标,她们的高贵在多少年轻男青年心中已远远超过了童话世界里的白雪公主,让人望尘莫及。
我喜欢趴在柜台上闻百货的香精味,如果运气好,还能舔到散落在柜台上的红糖或白糖的颗粒,或是几粒灰色的盐巴,但这些微不足道的牙祭往往会带给我一整天的愉悦。
当然,年轻的恋人最浪漫事莫过于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我三姨恋爱那年。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三姨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被三姨父载走,无论我怎么玩命地追赶最终还是被远远地抛在了后头。看着他们最终消失在尘土飞扬的机械路上,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自己能快快地长大,也能骑着自行车在傍晚时分一个人或者也带着自己心爱的女友去洪门口电影院看场电影。
除了对电影院的热衷之外,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供销社对面的新华书店了。相对供销社而言,新华书店就显得有些寥落了。简陋的柜台,空空的书架零散地摆着几本书。小人书专门摆在书店右边角落的一个陈旧的柜台里,隔着上层被磨毛的玻璃,我们吃力地辨认着封面上的文字,陶醉于那模模糊糊的彩色封面之中。
记忆里第一本《新华字典》就是在这里买的,1元4角5分。红色的塑料封面,横向排列的四个烫金大字,完全模仿《语录》的式样。我没有赶上那个把《语录》奉为“红宝书”的年代,但我却把那本《新华字典》当作了我学习的宝贝,一直用到初中毕业。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文字的爱好,我人生中的这第一本《新华字典》功不可没,时至今日,我仍然保持着有事无事就翻看字典和地图册的习惯。
所以,对于《新华字典》,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情深。就像洪门口――一个与我毫无任何瓜葛的小型矿区于我一样,赋予了我童年生活的精彩和美好。
我说不出,也说不清,那种对洪门口的感觉到底该用一种怎样的词性去定义。
离开故乡多年了,每次都还是在洪门口下车上车。坐在颠簸前行的车内。路两旁的店铺仿佛依然保持着三十年前的原貌,萧条的街道,陈旧的屋舍,平坦的柏油路已经变成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车轮扬起的飞尘乌云一样地遮天蔽日,看到她的衰败和破落,内心深处偶尔会闪过一丝丝的伤痛,仿佛是看到了一个远房的亲戚逐渐老去的脸颊和佝偻的背影。这本是一个与自己生命没有任何瓜葛的地方,但那丝丝缕缕的血脉真情却往往会在某个特定环境里突然进发。交织成一种莫名的伤感。
突然想到很想统计一下那些因矿难而被埋没在洪门口地里下的尸骨。虽然血肉模糊的灾难和冰冷客观的数字无法粘连成一段段完整的历史,但绝对震慑人心。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不是我要故意在文章的结尾抹上一层凄凉的色彩,不仅仅因为我想要标榜他们是建设洪门口的功臣,不仅仅因为我为他们健壮的生命在突然间的灾难里戛然而止而惋惜,仅仅因为他们用生命的陨落点染了洪门口曾经辉煌的一丝光彩。仅仅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洪门口今日的衰败而产生一脸的忧伤,他们是何其的不幸却又是何其的幸运!我相信他们短暂的生命对洪门口的最后的一次回眸,带进天堂的记忆应该是洪门口红红火火年代的永恒。
我们是否应该像悼念烈士一样地悼念这故旧的一切?
我们无法把握情感在物质世界劣质的退变,只是当深夜里突然惊醒,那份沉静中的回忆可以填充白日里忙碌生活的虚空时,那刹那间的永恒不就是对心灵的清澈过滤,对灵魂的自我掂量,对人生一次次缺憾的短暂慰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