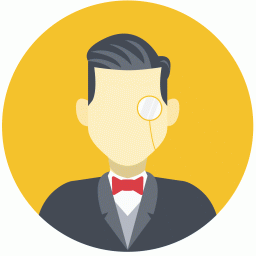紫薇古井 第5期
时间:2022-08-24 11:47:12
他看着我画画,然后说:“画画真好。手艺人好吃饭。下乡插队就可以靠画画吃饭了。”
有一段时间我并不上课,而是被安排在“大教室”的西厢里,远离了同学,一个人画政治漫画。我想这多半与我的美术课的成绩有关。画漫画,是一项任务。每画完一幅,我就把它挂起来。缘屋子的四壁一路挂过去。那时候,我对这个纷繁的世界充满了畏惧,不知道如何对付。
我们学校叫小学,最早叫学前小学,与一座很大的孔庙并排在一起。那庙很大很深,有好几个殿。早在多年以前,我进庙去看过一回。庙场上整齐地摆着近十口棺材,是两个派别的群众用真刀真枪互相残杀之后的产物。棺材是新的,涂着没有亮光的黑漆,有些肃穆。其中一口,是我的一个姓邹的邻居的,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口。一个老头看守着它们。几棵古银杏树,枝干也是黑的。风过去有叶落下来,铺在青白的地砖上。与孔庙相比我们学校的建筑很单薄。孔庙的柱子要两个人合抱呢,墙更是厚得难以想象。后来在里边办了个工厂,机器的噪音居然传不到学校这边来。
进学校大门,正对着的是一个池塘,名叫泮池,一座石拱桥从中穿过,石缝里长着星星草。池塘的水面漂满绿萍。绿萍很能长。常见城外的农民把绿萍捞起了挑走。翻了身的绿萍,背后是紫红色的,根系细且长。可没隔多久,绿萍又满塘了,看不见水。水底有没有鱼,不知道。只知道有蛙。雨后,阵阵蛙声传得很远。给沉闷里注几许清凉。
看门人叫老吴,大家都这么叫。看门人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只记得我刚进校时,批判老吴的大文章没有贴到大批判专栏中去,而是贴在两张竹榻上。竹榻竖起来靠在路边的冬青树上。我们班同学整队路过,我看到竹榻上方的题头处画了一只面目可憎的老鼠。同学说那就是老吴。传达室的后半间就是老吴的家。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老大与我姐姐一个班,女儿与我妹妹一个班。我从来没见过他老婆。老吴负责开校门关校门,负责打钟,负责烧开水。我曾随同学到老吴家去要开水喝。他的家实在没有家的样子的,一只煤炉,一张竹榻,两口木箱,两条板凳,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这也算家?当然是家。老吴每天开校门关校门打钟烧开水,闲了,就把学生弄坏的课桌课椅搬来修理修理。早些时候,那池塘里是扔满了课桌课椅的。早上我到校时,见他两个孩子还在吃粥,吃得“忽落忽落”响。补了铜钉的青花瓷碗向上冒着热气。老大总穿得很单薄。他不怕冷,每天清晨在操场上锻炼身体。他说坚持几年就强壮了。待初中毕业他要插队去,好让妹妹留在城里。
我画漫画所在的“大教室”是独立的,与其他教室有很大的距离,紧挨着高高的围墙,高墙外便是街巷了。它的西边,隔一块空地是厕所。厕所的粪坑很大,一半在校内一半在校外。有一回一个学生方便时往坑里多看了一眼,就发现了一具死婴,,皮肤雪白,腹上还连着根脐带。有同学说是:“私囡。”“私囡”就是私生子。谁家的呢?没人知道。调皮学生拣碎砖块去砸死婴,老吴见了便骂。有人就说那私囡是老吴的。老吴也就不骂了,走他的路。
“大教室”走廊一侧的墙上,石灰有些掉了,斑驳中裸出一根根的小木条,里边竟是空的。“大教室”一共才三间,朝南一字儿排开。东边的那间做了音乐室,常有学生在那里边很投入地歌唱。有一回办“戴帽初中”,一个初中班就占了那间音乐室。所谓“戴帽”是由小学办的初中,非常时期才“戴”。就像人冬天戴帽子,待天暖了是要摘去的。自然,天天要做广播体操。正是初秋的季节,阳光很好,有些红。下早读课的钟一响,同学们便鱼贯而出,到操场去排队做操。戴帽初中的一个圆脸(特别圆,还特别鼓出腮帮)的女生,突然口吐鲜血!操场上不长草,经常浮着一层软得被风吹来吹去的细腻的黄土。那血便把一摊黄土凝固住且合成了另一种颜色。那女生竟然无事人一样,继续按着高音喇叭中的节拍做操。我的心悬挂着,不时地朝她那边看,然而,及至早操结束,也没再发生什么。这事一直让我吃惊着,在我以为吐血是极严重的病。而那个女孩表现得不惊不慌。
“大教室”中央一间比东西两间要大得多,屋顶也高出许多,上面有一排气窗,吊下来几根可供控制的细绳。东西两间似它的一对羽翼了。这中央间一直做体育办公室。里边有两张办公桌,两把藤椅,空档里放满了各式体育器材,如跳箱、山羊、垫子、球等。但还是感觉空荡,因为屋子的空间实在太大。我们学校没有专门的音乐办公室。体育办公室内的另一张办公桌便是音乐老师的。两张办公桌面对面。教体育和音乐都比较清闲。没见过有学生要补习体育和音乐的。音乐老师是个年轻姑娘,刚从师范毕业,没地方住,就住在紧挨着孔庙北墙的单身宿舍里。音乐老师连走路都要唱歌。我想到了那个池塘,而她无疑是水面上的一阵清风。让人也相跟着英姿焕发。可是后来就不唱了。人也变了。才到深秋就穿得臃臃肿肿的有些老态。过了寒假,开学去,我们就再没见过那个年轻的音乐老师。办公室门前的空场上,有几张青石板叠的乒乓台。青石板是一块碑,上面有碑文。一块碑躺下来便是一张乒乓台。天天有学生排着队在那儿打乒乓擂台,我们土话叫“霸大王”。大王者,可挨个接受排队学生的挑战,如果大王输了,那就得让位。这样一点小事都会引起大争执。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姓毛,是个男的,四十岁左右,眼睛很大,大得向外突出来了。老吴的儿子跟他有交往。他也很乐意教这个未来的“知青”强身的几种方法。但不知为什么毛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很凶”。――有架子,不耐烦,动辄呵斥,甚至动手,大不同以前那样可亲近。我们小小年纪怎么会体谅他的寂寞和苦闷!“黄帅反潮流”风盛行时,同班同学虞一东首先贴出的那张大字报就是针对体育老师的“凶”。也怪,学生轰轰烈烈贴大字报时,毛老师生病不在学校。不知是什么病。后来,我看见毛老师来了,一个人站在孔庙墙下看大字报,看十二、三岁的学生写的大字报,看大字报上他自己的形象,郑重其事。
与毛老师面对面的那张办公桌一直空着。我想象着闲下来坐在桌前的毛老师抬起头来的情形。
还是说西边的那间画室。整天一个人在里边画,很是寂寞,听着钟声响后,外面或是静了,或是闹了,便就是上课与下课。我总是关着门画,想自己班上该上什么课了,也想那些同学。他们是很羡慕我可以不上课的。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令我很震动――是老吴的儿子。他看着我画画,然后说:“画画真好。手艺人好吃饭。下乡插队就可以靠画画吃饭了。”“……”我真的很意外!“那你一起来画吧。一学就会。”“你不怕别人抢了你的饭碗?”“这我倒还没想过。”他沮丧地摇摇头:“牛吃稻柴鸭吃谷。”他说这句话时还笑了笑。隔了会,他说:“你画吧,我不影响你了。”他就走了。出门时还不忘把门小心地带上。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我的肩上有前所未有的负重感。我不能不想他们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
如果不是后来,班主任又派了两个同学来帮我一起画漫画,也许我的古怪念头会像青藤似地越长越无边际。漫画日积月累很多了,挂满了墙,就堆在一起,堆得压抑凌乱,就像我的心情。于是,想办法用铅丝从屋子这头拉到屋子那头,拉了许多道天网,那些完稿的漫画就夹在铅丝上了。我至今没弄清,后来那些漫画派了什么用途、都怎样了。恍惚间挂起来的漫画是片片婴儿的尿布。我对长大充满了畏惧……
老吴的儿子第二次找我时,拿了顶旧草帽。他是跑来借笔和颜料描一描旧草帽上已淡化了的红字(字是一句当时的流行口号)。旧草帽上的那行字已旧得灰头灰脑。老吴儿子描字的手在不停地抖。这样红颜色就不听他指挥跑出原来笔画的规格了。破了格,他就擦去重来。如此,反复了多次。我看得心痒,说:“我帮你写。”
“不不,还是我写。”
我决定不去看他。他兴许能自如些。我便转身去随意翻那些画。
有个小女生在走廊里尖着嗓子喊:“哥,哥。”老吴儿子直起腰来在窗口露了露脸。他的妹妹就一阵风似地进屋来了。
“呀,哥,你写得跟刚买的一模一样。”
老吴的儿子揩揩满头的汗,无声地笑了。
学校请了摄影家来拍漫画小组开展活动的照片。几个同学集中在画室里围着一堆。我想手上该有一支画笔,可找来找去竟然没有画笔的踪影。情急之中,我掏出随身的一支钢笔替代。画笔的失踪一直是个谜。西厢里又剩我一个人了。老吴的儿子也不再来,他写了血书,提前下乡了。学校组织我们到接知青的大卡车必经之路夹道欢送。车过时,老师领着我们高呼无数次的口号。胸佩大红花的知青在插满彩旗的卡车上激动地向我们挥手,一路放歌。
一人一西厢,一画一世界。
东边的教室里有学生在深情地唱歌,一个叫杨老师的女人踩着一架风琴笨笨拙拙伴奏。中间的那间办公室呢?很冷清。门前碑做的乒乓台也很冷清。就像碑上的那些字,从来没有人去认一认写的究竟是什么。
那一年我读五年级。那时实行五年制,到夏天,我就毕业了。老吴的钟声也辽远。
那段生活让我不能忘怀的有两物。
一、 紫薇。我们叫它怕痒痒树。其状纤纤,树皮呈淡色,很薄。
二、 古井。一口青石井栏的内圈已被井绳勒出道道深沟的古井。
这两物都在校园的东南侧,而且彼此离得不远。每次走过,我总要探头看看平平静静的井水。古井的底下也有一个圈口,也有一个斜背与军装同一色书包的小儿――扮一个鬼脸,倒映的天幕很蓝。然后再去搔紫薇的树身。紫薇的枝枝叶叶便抖动起来。其花发于夏。不知道现在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