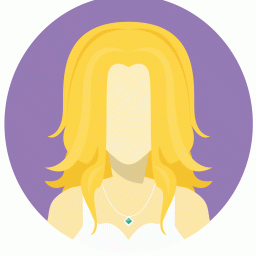黑色刻度 11期
时间:2022-08-19 01:25:22
作家简介:
刘志成,1973年生于陕北,2007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青年作家班,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文苑・西部散文家》选刊执行主编。散文《怀念红狐》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著有散文集《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等12部作品。主编《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上下册)等散文选集15本。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奖、2010年华北五省份优秀教育图书奖,内蒙古政府第八届、九届、十届索龙嘎奖,内蒙古第九届、十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等100多个奖项。曾被文学界誉为“2003年内蒙古文学年是刘志成散文年”,获评内蒙古本土十佳作家,参加过全国第六届、第七届青创会。内蒙古作协签约作家。
我知道我已死了,但黑暗还在。
我是被坑道坍塌砸死的。我很清楚地记得临死前的那一幕:骡蹄像田间水壕现身的格扭(蝌蚪)拖着的黑糊糊的尾巴,从井下坑道的煤面上抖出一串清脆的,很有节奏的滴答声。“想亲亲想得咱胳膊腕腕软,拿起了筷子端不起个(碗)……”哼着小曲儿与黄虎骡并肩走着的我,正要将那个“碗”字抖出的刹那,身子猛得颠了一下,一团黑雾在眼前真实地晃起,一股强大而灼热的气流迎头盖脸冲过来,紧接着天崩地裂一声爆响,我像被大风扑倒的树和野草,重重地滑在了坑壁上。脑袋嗡地一响,我的世界就坍塌了……
森黑流进了眼窝,森黑染黑了心田。这就是地狱吗?回答我的唯有呛人的硫磺味直冲鼻孔。连续的咳嗽像蒺藜从腔子抖出后,我的意识瞬间翻转。用手在大腿上狠狠地拧了一把,疼痛如割,这才确信自己还活着。
坑道失去了颜色的锋芒。黑把一切色彩和声音都掩埋了,把我所处的世界竟然给缩小了。我试着站起,稍一动弹,头部左侧和左肩部揪心地像铁器在裂响,右手一摸,头的左上侧如挨了一重锤,手就冷丁丁地颤着缩回。再摸,脸上血痂凝结,额上点点冷汗渗出。抬左手臂,左肩部传出的痛感在心里越缠越紧,又摸,肿得馍馍一样。黄虎骡难道被砸死了?咋听不见叫声呢?矿灯甩到哪里去了?难道眼睁睁就成了一个睁眼的瞎子?咬着牙挣扎着坐起,摸索。左边是坑壁,潮呼呼的;右边是坑道,格底格簸(凹凸不平的意思)。身子如放大重浊心跳和痉挛的音箱,挪着向前摸去。范围逐渐扩大,矿灯和安全帽终于在黑暗中跳出。灯光在黑暗里打了几个漩涡,这才看清在距离我十几米远的坑道口发生了坍塌,被煤块堵了个严严实实。黄虎骡还活着,还套在车里。四条目光扭结在一起。我浑身抖了一下,努力站住。而骡子头一摆,一声咴咴咴的亢叫在光亮中甜甜出口。
挣扎着站起。骨头散了架似的,疼痛火烧火燎地滋长。一阵头晕目眩。踉踉跄跄,走过去抱了骡脖,贴着骡脸,泪珠就扑簌簌落了下来。骡嘴不住地蹭我的身子,两股粗气热烘烘地在我的手掌间弹跳。它的两只大而明亮的铃铛也闪着莹莹的光……我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工友们都歇车了,我还想多拉一趟,把日子填得实实在在。但黄虎骡走到入井口就喷着响鼻停下了。吁――驾!骡头摇了几摇,一声咴咴的嘶鸣甩得蛮高。传骡子,跟上鬼了?手扯了一下缰绳,骡的两只前蹄在原地晃了几晃,又不动了。手不耐烦地举起,一掌撂下。三声两声,骡竖起两个长耳,捣毛操蛋的嘶鸣镀亮了要落下来的太阳。黄虎骡今儿是怎么啦?以往拉十几趟,每次一吨多炭,一溜上坡路,一低头,一展腰,一口气就出了洞口。缰绳头终于扬起,狠劲抽下。骡蹄拂动,极不情愿地走进矿洞……
卸下骡套,拎了车上的大方锹,我开始寻找逃生的路。身后是炭堆,炭堆后面是采掘面。我处在炭堆和坍塌处之间三四十米长的一段坑道。煤尘渐渐落下,空气清新起来,我的呼吸畅快了许多。近前细照。塌陷的大炭块互相挤压着,镶嵌着,密不透风。没有先进的掘进设备,人工休想挖通一寸。我难道就这样被活埋了!眼前的事实像这些有棱有角的炭块一样坚硬,扎得心里的火星熄灭了。我成了根瘫软的麻绳,堆在地上。两只大了起来的手掌叉在头发里,点点冷汗渗出,从头凉到了心里。偶一抬头,顶上晃着碗口粗的一砣婴儿般柔嫩的亮光摄入了视线。我知道那是通风口。由于这么一砣砣亮光温暖的气息,我判断出,现在是白天,应该是第二天了。
黄虎骡咴咴咴的嘶叫声又在冷不丁加重。我知道黄虎骡饿了,要吃。以往,套一卸,先要让骡子打个滚,然后拴在槽边,歇上一刻就给饮水、喂草、喂料。可在这鬼门关里,去哪找草料呢?老伙计,忍着点儿,我好一阵心疼,折回去抚摸着骡子说。忽然,骡脊上的一片血迹吸引了我的目光。猫腰细看,发现有块指头肚大小的炭渣子扎在了骡脊上。我心疼得直咂嘴,再看,枯涩的眼光就被骡脊上七八处殷红黏住了。僵硬的手指一抠,一粒一粒的炭块就咣当咣当滚到了地上,那声音比针还细,直往我心里钻……
闲驴啃干柴。骡鼻嗅着车辕,嘶鸣稠得像粥一样,空气里遍布饥饿的恐慌。我记起采掘面里支顶圆木上的树皮,于是窜到采掘面,从顶矿顶的圆木上剥了些树皮,夹在胳膊窝里折回。起先,骡子只闻了闻,仍然一个劲地叫。我故意不理它,蹲下闭目养神,意念葡萄藤一般窜向了家。我看见了两周岁多点儿的小儿虎子精得会说话的眼睛……每当下井回去,我伸一个懒腰,虎子就会将枕头抱来。“爸爸快歇着”,他的细声嫩气令我的疲倦一扫而光。小睡醒来,如果虎子还没睡,他就会到我怀里撒出一串一串的梦想和欢笑,一会儿叫给他讲故事,一会儿让和他猜中指。可如今十有八九见不到儿子了,我的心乱成了蜂窝,眼含苦涩自言自语。坑道内终于响起了骡子嚼树皮的圪嘣嘣声音。那声音像一个无形的钓饵,钓得我肚里的馋虫叽里咕噜地闹腾起来。显然没被压死,可就要被饿死,渴死,恐惧一滴一滴渗入了骨头。坑道的气温开始下降,裹着夹袄还觉得发抖……
通气孔处的那砣亮光亮着亮着就变得黑咕隆咚了,坑道内的黑又把我裹了起来,我知道第二个夜晚降临了。起伏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将坑道推向了寂静。睡在哪呢?我的目光盯向了平板车。卸下车上的炭,扬起车辕磕尽炭沫,就躺上车休息。虽然睡不着,但为了省下生命,去浇灌我的虎子和家,我必须节省体力,保持一动不动。我甚至还想了个忽略黑暗及黑暗笼罩的一切的办法,那就是强迫自己数数,先从一数到一万,然后从一万往回数,这样数着数着竟然睡着了。
我是被骡子咴咴咴的声音惊醒的。骡子一夜要吃三十多斤谷草、六七斤豌豆料。给它吃了点干树皮,只怕连垫牙缝也不够。开了矿灯,见黄虎骡不停地用前蹄刨地皮。抚摸着骡鬃,我的心碎为九瓣,像被骡蹄子刨着一样难受。骡头蹭着我的上身,尖厉的嘶鸣遮盖着饥渴的惶恐……
第三次看见那砣砣亮光闪耀成钻石时,口渴像核桃壳,在嗓子里轻轻迸裂。我的嘴唇已干裂开许多血口子,连的声音也很难发出。伸出失去了伸缩灵性的舌头一舔,觉得那些血口子里有黏稠的糨糊流出,又腥又咸。满脑子只想着一个“水”字,这个字已践踏了我的身子,烧痛了我的灵魂。难道就这样被渴死吗?可水从何来?脑海里忽然闪过小时候老人们讲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饿了吃皮带,渴了喝马尿的故事。一想到尿这个词,僵硬的舌头禁不住又舔了舔嘴唇。开了矿灯,我的眼睛直直地盯向骡。黄虎骡烦躁地在缰绳制约的范围内来回地走,前蹄时不时刨着铁硬的地面,时不时抖出三两声咴咴咴的嘶叫。可此时的我已无暇顾及骡的痛苦,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骡。它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又缩回去。过了好久,我的两眼也发困了,头也发晕了,骡才终于向后退了半步,身子向前伸了伸,伸出半尺多长。我知道骡要尿了,赶紧双手捧着安全帽对准它,又等了一会儿,才哗哗啦啦洒了出来。
骡尿有半帽壳子,臊臭弥散,叫我好一阵干呕、恶心。但那浑浊的水汽在不断地诱惑着快要成了烟洞的喉咙。喝!我闭着眼,张嘴一鼓气就吸进去一口,那种苦咸臊臭叫我直反胃,可那种水汽的滋润,又叫我舒服无比。强忍着臭,有意让尿水在喉咙处多停留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咽下肚。连续几大口的骡尿,将五脏六腑的灼烧和嘴唇、咽喉的难受冲散。帽子里还有一些骡尿,不能再喝了,一口骡尿就是一个希望啊。我捡了碎炭块,摆成三角形,把帽壳子放上去,马上把矿灯熄灭了。我知道不到关键时刻不能用矿灯,否则成了纯粹的黑暗世界,就更麻烦了。
周围是无垠的静,世界在这里已被简化成铺天盖地的黑和铁一样的冰凉。饥饿的欲望吐着水泡,直叫我抓耳挠腮。我又端起骡尿,这次好像已没先前那么难闻。喝了一口,那种叫人恶心的臊臭竟然没了。又抿了几口,但仍饿劲难挨!四周除了炭渣子再无别物。难道真要被饿死吗?过去曾听老人们讲,遭了年景的人吃土。无法忍受饥饿煎熬的我,心想左右是死,就抓起一把带水的炭渣子放进嘴里嚼了起来。这炭渣倒没什么味,只是非常涩,难以下咽。闭上眼正准备强行下咽,一下子想起坑道里有矿友刘三丢下的半袋方便面。那是在十几天前,我和刘三装好炭车,正要起身走。“老婆住娘家去了,早上连饭也没吃,这有两包方便面,吃点再走吧。”刘三说着就给我扔过来一袋,他打开一袋,才吃了两口,他的骡子走了,刘三一看急了,方便面从手中滑下,顾不上拣就去追车……
从口中吐净炭渣,拖着酸软无力的身子,激动的我挣扎着爬向炭堆。前面黑洞洞的,后面也黑洞洞的,我像片孤单的树叶在黑色凛凛中无助地飘,只有鼻孔里的两股粗气标志着我摸过的路程。黑色横陈,黑浪排天。黑色在狰狞地微笑。一下一下蠕动,一下一下摸,终于摸到一小块东西,拿起一握是炭块。又换了地方再摸,摸呀摸呀,一手掌大小的一个小方块在指端发出清脆的响声。啊!真是那半袋方便面,我凝结的眉头流水一样荡开。迫不及待咬了一口方便面,嚼着回到放安全帽的地方。就着骡尿,吃了起来。那种美味、那种香甜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吃了几口,就不敢再吃再喝了。但我已觉得身上有了热气,有了精神和力气。
难道矿里真的不管我了?黑暗像海绵吸纳了冷、悲伤、绝望和饥渴。我觉得眼睛又困了,打了几个哈欠之后,强打精神,将车鞍子上的垫子,铺在车板上,躺下打起盹来。但黄虎骡烦躁而悲凉的咴咴咴的叫声扰得我心烦意乱。老伙计,对不起,实在没东西给你吃,我慢慢地把黄虎骡的笼头从头上摘了下来,拍了拍它的脑门。没了缰绳的骡子围着我转了几圈儿,在黑暗里摇晃着两个忽闪忽闪的眼珠渐渐地远去了。只有那种空空荡荡的回声,一下一下敲在我空空荡荡的心里。间或有粗重嗅声,圪嘣嘣咀嚼声在黑暗中回响。黑暗中远远传来的这一切,令我开始泪流满面……
一觉醒来,通气孔处又开出了金黄的榆钱钱。骡子不知何时回到了炭车旁,挨着我站着。空虚的胃像眼镜蛇膨胀的脖颈,我一次次攥紧方便面,又一次次放下。终于忍不住吃了一口,就又锈在了手中,被口水和眼珠冷凝了。必须像国家控制人口一样控制这点方便面,我呼出的气流在身前抛出了扭曲的轨迹。能擦亮黑暗的,唯有呜呜哇哇孩子般的回音游戏以及在黑暗中骡越来越亮的嘶鸣。但通气孔处的那砣砣亮光成了我辨别白天和黑夜的罗盘。我把骡子的套引子放到坑壁下一个固定的地方,每有一次亮光,套引子里就有一个小炭块发芽。
骡虚弱的嘶声里,我又觉得困了。睁眼看头顶,那砣亮光已不见。闭了眼睡,就觉得有点儿凉。为使身子暖和点,我把骡子乖磨得卧下,紧挨着骡打盹。就这样渴了喝骡尿,困了挨骡睡。如此五六次后,醒来,骡却站不起来了。骡肚大了,出气也变得粗重。我的伤感一下子如秋叶刮落,喊、叫、拉都无济于事。骡肚越来越大了,喘声越来越粗了。凭经验,我知道黄虎骡是结住了(这病兽医叫肠梗阻)。骡马牲口本来是吃草料的,吃了带炭沫的树皮,能不结住吗?按理说,结住只要给灌点苏打水、蓖麻油,就能润开。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牲口受罪,把点点滴滴的伤心簸扬在空空荡荡的坑道里。骡肚鼓胀得已不能正常地侧卧。它四蹄伸展大躺着,舌头伸出来,发出一声又一声嗯――啃的喘息,原本大而黑亮的双眼,时不时地翻出白眼仁。像有一把尖刀,剜在我的心上,眼泪断了线地滚落下来。摸着骡冰凉而快要僵硬的躯体,我不由得撅着自己蓬乱的头发。
泪眼迷蒙中,黄虎骡生龙活虎般地站了起来,摆摆头,甩甩尾,又用毛茸茸的大嘴巴蹭我的手,蹭我的身子。坐着骡车飞离了坑道,拐上了窑外的搓板儿路,车轮撞击地面的隆隆声越来越响,身底车底板震颤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我醒了。骡肚鼓得简直就要炸裂开了,间或发出一声低得几不可闻的嗯嗯啃啃的喘声。忽然,我真切地听到从坑道口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同时明显地感觉到身底传来微微的震颤。外面传来的这一信息,一丝一缕剔除了涌动在血液里的绝望。我知道这一定是外面的人在开始营救了。方便面吃完了,骡尿也快喝光了。如何挨到外面的人进来?骡膘肥体壮,少说也有二百多斤肉……黑色的空气中颤起了我扑腾扑腾的心跳声。我取下车鞍上的铁片,割开骡脖上的血管。骡头歪在了地上,骡血冒出,溅在了脸上、衣服上。我疯狂地凑上嘴咕噜咕噜地吸着……直至血没有了,我才停下,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骡翻着白眼断气了,此时轮到我的肚子鼓得快要炸裂开了。疼得我生眼泪直泡。这些天,我腿软得站久了都困难,但还是咬着牙站起,摸着坑道壁慢慢地走……
黑补丁又罩住了通气孔。我像被黑暗领养的一只耗子,必须冷静地面对一切。坑道内的温度并不低,起码在100℃。骡内脏放不了多久就会腐烂变质,而肉比内脏能放长些时间,肚胀像糖一样溶解了,我蹲下来开始盘算。我又迫不及待拿起铁片,拼出全身的力气划开骡肚皮,一股热气喷了出来。刨出胃、肠,刨下心、肝、腰子等内脏,已累出满身大汗。咬了口肝花,一股腥膻味令呕,恶心。但我强忍着嚼。万事开头难,囫囵咽下一口后,舌感就麻痹了。半箧(一半的意思)肝花吞下去后,我觉得身上恢复了精神和力气。骡活着时挨它取暖,死了怎么办?骡皮!对,盖骡皮睡!重新拿起鞍上的铁片,磨快了,我开始剥骡皮。一点儿一点儿,剥得困了就歇会儿。皮剥下一半时,我试着想把骡身翻过来,去剥另一半,但怎也撼不动,只好割下半张骡皮。盖着皮睡,果然没有先前潮冷了。
骡尿终于喝完。空气仿佛遇火就要燃烧。周身罩在夹袄里热烘烘的,喉咙在冒火,干燥随着粗重的呼吸荡向肺、肝、血管。根本吃不下去骡肉,我想到了喝自己的尿。将安全帽支在萎缩成沙奶奶的生殖器下,过了好半天,才闪出了一线细注。叮咚。叮咚。那声音勾得我的嗓子更难受了。犹豫着喝了一口自己的尿水,那味涩涩的、咸咸的,还带一点苦。嗓子有了三分凉意,顺着喉管往下走,一直浓到周身感到湿润……后来,我怎么也尿不出来了。喉咙成了通红的火炉,水像毒蛇箍住了活下去的信心。手无意间摸炭渣时,感到渣里湿湿的,迫不及待抓起把炭渣放进嘴里嚼。嚼出的水非常涩,我闭上眼强行下咽,那东西一触咽喉哇的吐了出来……
那砣砣亮光第十三次转出来时,坑道口轰隆隆的声音突然没有了。头昏眼花的我靠着坑壁,为水沉浸在绝望之中。那砣亮亮的漩涡也突然干枯了。空气里荡着丝丝湿气。天怎么这么快就涂上黑颜料了?我嚼了一阵带水的炭渣,吐出,又开始一、二、三……慢慢地数数。突然有哗啦啦的流水声晃到了耳根,水声很响,让我心里发甜。赶忙摸到矿灯,打开一照,有大拇指粗一股水从通气孔中倒了下来。水!水!我情不自禁地边叫边迅速地爬起,拿着安全帽接了半壳,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那是一生喝到的最清凉可口的水,叫我浑身每一处毛孔舒服极了……水足足淌了一个时辰。我用炭渣把水圈起,围成两米方圆的小水池。这么多的水,喝它十天半月是没问题喽,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此,我不再为食物和水犯愁……
铜勺形的通气孔把那砣砣带着乳香味的亮光第二十次扬起来时,从坑道口传来的轰隆隆声又响了起来,身底传来的震颤越来越大。骡肉已开始变质,一股臭味直冲鼻子。硬着头皮吃了一块,稍感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没在意,饿了继续吃。这一下可不得了,肚子开始是轻微地疼,一会儿比一会儿疼得厉害,剧烈的腹痛疼得我满地打滚,喊爹哭妈,头上直冒冷汗。不久开始吐和泄,病势越来越凶。特别是下泄,刚泄完,没等挪地方,提裤子,就又想蹲了。一连几天,泄得我筋疲力尽,最后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身底传来的震颤时断时续。为一丝希望,我像一具行尸走肉不得不继续忍受着失去阳光的日子。口干舌燥,浑身滚烫,脑袋昏昏沉沉。身子成了发酸的黄酒,正在慢慢变质。整个人已虚脱了。只能腿肚打颤,一升一降地爬着去喝水,手掌和膝盖一蠕一动一步挪不了三指,被粗涩的炭砾磨得锥心的疼,发出吱吱的声音,几趟下来,膝盖的裤子已被磨出洞来,手掌还好点,膝盖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流出,皮肉外翻,然后像馍馍一样串得虚胖,手指一按,钻心的疼使我禁不住叫出声来。爬着喝水还好点,爬着拉屎,腿发酸发僵,胳膊发抖,气喘心跳,往往要歇上好几回才能回来。尤其是用小炭块擦屁股时,炭块还没挨上,就由不住像小时候感冒打针一样哆嗦一下。后来爬回来就成了一摊稀泥,连车板也爬不上去了,只得拽下骡皮在地上躺着。巨大的臭挤压着空荡荡的坑道。我的心里,恍惚得比坑道还要空荡。在热腾腾的黑暗里,我听到了我儿子模糊的笑声,我看见了我老婆肿成桃子的眼睛。以往太阳快要落山时,我老婆改花就做好了饭。如果我还没回去,她准会站在大门口向矿井方向,天好天歪,从没间断。有天快黑了,白毛风卷着雪花,吞没了整个矿区。改花怀里抱着件棉大衣,竟焦急地跑出来在风雪中向矿井方向找来,长长的睫毛都变成了白色。她见我时,像母牛朝我猛跑过来,一股暖流迅速流遍我的全身。“这么冷的天,你甚了,我迟早会回来的,看把你给冻的”,我紧紧地把改花拥入怀里,爱怜地责怪。恍惚中,我看见了改花跌跌撞撞向我走来,心里生出一丝酸溜溜的幸福……伸手去扶她,这才发觉原来是被家的味道晃花了眼。改花啊!你可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如果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咱虎儿可靠谁呀。改花,坚强点,千万要挺住,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自言自语中,我突然觉得两小腿处痒得厉害,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挠,可越挠越痒。这种痒比疼还难受,实在叫人无法忍受。我先以为是这二十多天没洗澡、没换衣,身上生虱子了。那虱子咬得人坐卧不宁,睡不着觉。又一想,不对,虱子咬是这里一口,那里一口,可这种奇痒就固定在两小腿处。因抓挠得多了,就有被抓破的地方,流出来的淡黄的水沾到手指上,手指在哪挠,就给哪传染上。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得了疥病。这病就怕用手去挠,越挠传染的地方越多。小时候得过这病,我妈怕我挠,把我的手指用蘸过盐水的白布裹住。没钱治,我妈用灶坑里烧露的黏灰和点老白酒涂在患处,涂了几次就好了。可现在哪找那东西呢?我的小腿烂成了腐西红柿。不敢再挠了,痒得不行,我就咬牙挺着,把嘴唇都咬破了。那病折磨得人心力憔悴,有种不想活的感觉。这样硬挺了段时间,痒才减轻点。
发生中毒性痢疾后,我不敢再吃臭肉了,身体彻底垮了。被黑色包围着,被清冷和寂寞包围着,被饥饿包围着的我在承受一种游离在生和死之间的极限忍耐。心和那轰隆隆声贴膏药似的黏在一起,身底的震颤停了,心就寒了,只好强迫自己数数,以此打发孤独和寂寞。震波传来,心会因狂跳供血不足,大脑出现一阵晕眩。我估计着外面掘进的速度,有时还想象着自己活着出去的情景。
已经饿得处于昏迷状态的我又一次醒了,是被身上一种蚁行感弄醒的。我感到腿上、胳膊上、脸上、脖子上,有小虫子在爬行。怎么这倒霉,生了虱子,还不把我给活吃了!用手一摸,是条香头粗细,半寸多长的胖虫,一条、两条、三条……啊呀,太多了,身上到处都有。开了只能发出暗黄光斑的矿灯,我看见不仅自己身上爬满了许多不到一厘米长的白色小虫,腐烂的骡肉里更是成团挤挤攘攘贴着。骡肉被它们吃完了,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了,我的悲哀朝黑的抑郁的空气里一抛,禁不住生起一股怒气:你们吃了骡肉,又来吃我!我还没死,先把你们吃了吧。抓起一条塞入口,大嚼起来,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咽下了肚,心里才忽然一动:蛆虫是吃了骡肉生长的,应该干净。但还是不敢多吃,囫囵吞了十几条,不见肚子有反应……
从此,我开始大量吃蛆虫维持生命。日子一个接一个刷亮,日子一个接一个发黑。我的心像的沙柳,等待着最后的镢头。那种计算身底震波远近的寂寞叫我煎熬。我醒了、吃了、拉了,就时不时地仔细听坑道口传来的爆响声,要不就数自己心跳的次数……
通气孔第二十七次拾回亮光丢失的图像时,我已处在半昏迷中。我看见了年迈的父母又在腊月的村口望,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一绺绺扬起……打工出来七八年了。每年过年,我都要带着改花和小虎回老家,和父母团团圆圆过年。可现在我被困在这里,十有八九是出不去了。爹,妈,儿子可能像一只断膀的板旦(蜻蜓)飞不过秋分了……亲情与死亡的恐惧纠缠中,自言自语的我已是泪流满面。我艰难地捻住一粒碎炭块,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爬着到了套引子边,放了进去,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看见了一片白色,耳边有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天堂原来是这样吗?正疑惑间,我看到了妻熟悉的脸在眼前晃。这是哪里?在医院呀,妻伏在我盖的被角哭了起来。活着就好,妻又嘤嘤地说。阳婆(阳光)从窗玻璃上照进来,暖暖的……
那以后,想起下井,我怕,我实在怕啊。所以我就来到了东胜。从老家上来后,我先是在街角打游击摆地摊修车,城管常常过来敲竹杠,票也不开。渐渐有了积蓄,就在街头租了一个安着门的五六平方米的楼梯下的洞。在这个所谓的店铺里,为了使工作的场地大些,我用铁丝和木板在半空吊了一个空间像火车上铺一样的床,然后将妻儿接来。一天晌午,没活。妻和我闲聊。她说,塌方后的第二十八天,我们进入了坑道,看见瘦骨嶙峋的你躺在一堆腐臭的大牲口的尸骨旁,须发蓬乱,脸色惨白,眼窝深陷,身上爬满了蛆虫,揭起衣服一看,你的腿上、胳膊上都长满了疥疮,到处都是脓血,还长着一层一厘米多长的白毛……妻说着说着声音哽咽起来,连我都自己听得小腿发软浑身发凉。那时,矿口塌陷了,我的身子和心也塌陷了。要不是想到了儿子和你,想到有一座山必须得我扛起来,我还怕真撑不下来。我感到我的声音里渗着米芾狂草一样的凉意,这种凉使我从脊梁一直凉到了心尖上。而门外的大街上,人流的喧哗和稀疏的2020的鸣笛声,在不着边际地生长。
许多年后,那场生命与自然的挑战,生存意念与死亡及死亡笼罩的恐惧的挑战,仍然将我的心划得短路。我在一次次闲聊中将这段传奇性的经历不厌其烦地翻晒出来时,我的心颤了一回又一回。而我的亲人们,我的朋友们在我一次次不同声调的讲述中只是品尝了眼泪或者讨厌的滋味,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在膨胀的欲望吞噬着我们的文明和土地中翻晒人活着的意义。
2000年9月初草,2007年10月于鲁迅文学院改定(作者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吉劳庆北路12号东方怡景园院内 西部散文学会1818-2号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