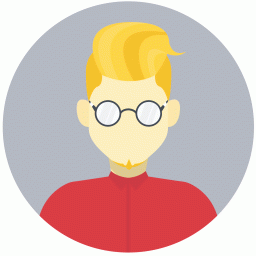无法停止的歌声
时间:2022-08-13 08:35:45
坚持
是干燥的冬天。小街两边的房子挨得很近,红色的。倾斜的屋顶上有零星的积雪,积雪上落满灰尘。一只鸟,羽毛灰暗,在积雪里寻找食物。
站在屋角的人,看不清年龄,睫毛上挂着夜晚的霜花,目光始终注视着对面一排脱尽叶子的榆树,好像在某根枝条里遗落了什么。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每天都是同一个地方,脚下和背后的楼壁上,有一小片冷湿的影子。有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向他张望,很快,又都将窗子关上,仿佛,怕有某种邪恶的东西随风潜入。关窗的声音让冬天颤栗了一下。而那个看不清年龄的人依旧牢牢地站在那里,他的坚持几乎磨圆了坚硬的楼角。
瑟瑟的枝条,除偶尔发出一两声低低的呼啸,一点动静都没有,更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那只鸟,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抖抖翅膀,望一眼站在屋角的人,向灰色的天空飞走了。
马背上的纹身
骑手此刻正开着汽车行驶在某座城市嘈杂的街上,他不住地按响喇叭。
一个来自无边草原的歌手。蓝天绿草间还回响着他苍凉的长调。那匹马,咴咴地叫着(也许是唱着),在初春的河边慢跑,脚步有些零乱。马背上的刺青是当年骑手用匕首留下的,在黄昏暮色里,闪着青色的微光。那是一次遭遇的纪念。骑手和马在雪后的一个清晨,冲出狼群的包围,骑手的帽子跑丢了,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但他紧紧地伏在马背上,最后,狼群终于被甩在后面。
骑手偶尔会烦躁地骂一句穿街而过的行人,有时也会被美貌女子的身影牵引,车速慢下来。唯一让人不解的是,他始终穿着绣满金色花纹的蒙袍,腰间佩着一把锋利的弯刀。刀柄上的花纹也是草原上那匹马背上的花纹。
花园
总能准确找到那条秘密通道。
花园。秋千荡起来,有来自童年的叫声。快乐。荡到高处,看见云绕苍松,落下去,夜一样凉滑的水便溢出来。水草丰盈。花园的门,柔软而清香,钥匙系在线上,线绕在颈上。
深夜,传来时光的钟声。花园的门,倦了,幸福地关上。
疼痛的城邦
远处的城邦,围裹着一条腐烂的青蛇。
死去的青蛇。一条护城的河。河上漂着自杀的人,仰着的,卧着的,多过幸存的鱼。偶尔,会看见岸上有人握着竹竿在打捞。打捞者很少,少过河面上惊慌掠过的鸟。
城门紧闭,城门前面的木桥被虫子蛀蚀得在风中抖动。因为疼痛。
疼痛的还有城墙,城墙上的瓦,瓦间的草,草上的蜻蜓。
还有我。在远处,满怀愁绪地倾听:城邦内,似乎传来让人惊喜的时断时续的哭声!
飞
一柄伞,在手里,风把它撑开。
一柄撑开的伞在手里,我便飞了起来。
一次可疑的飞翔。鞋子从高空坠落地上,很响。飞起来,便看见了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忧虑和懊丧。
鸟儿们的敌视目光告诉我,人类已不再是它们的朋友。空气咳嗽着向深处躲藏,仿佛,我是瘟疫。我感到,人类晚景凄凉!
还看见地上,丛莽山峦与楼宇街道之间,子弹呼啸而过。爆炸已不再让人惊慌,甚至,出门购物的女人,的腿平静地跨过街上血肉模糊的尸首。这是最惊心的时尚。还有堵塞的道路,小丑一样逃亡的政治家,一个疯子,在家的废墟上用三个八度的高音,声嘶力竭地歌唱……
不是我的草原
已经不是我的草原。亲爱的蒙古姑娘穿着彩色短裙跟在马儿后面,她已经看不出老额吉的期待和忧伤。
已经不是我的姑娘。秋天枯黄的草原,像一片苍白的画布铺展在天空下面,我已经找不到你从前的寥廓和力量!
收集者
收集死者的人,背着大大的口袋,缓慢地走在一切的地方。他面前永远没有墙。他胃口很好。他总是背对着生者,我没有机会看见他的脸。
他走路的姿态暴露了内心的平静,正是五月的时光。黑色斗篷,黑色口袋,年轻的骨头在口袋里叮当作响。
多像一位勤奋的收割田野的老人。夜一样的斗篷,刮落新生的露水,惊醒草叶下准备冬眠的秋虫,惊醒泥土。
任劳任怨的收集者走路无声。他谦卑而意味深长地向每个生者点头,他不微笑。他路过的地方,几枚树叶一样的纸钱被秋风把玩着,大地闪烁着冷冷的磷光。
河
还是旧时的模样。在我梦中又一次出现的这条浑浊而窄细的河流,从未有人能说清它的源头,在享受它带来的种种恩惠时,还是那样的理所应当,从容不迫。对岸,那几棵被风吹弯的垂柳,枝条探进水里,仿佛在等待一条不存在的鱼。饵食:一片瘦削的叶。
我看见童年的自己,手里捏着一条纸折的船(船身上有模糊的文字),站在远远的河岸上,看大人们在水里起伏游动,却舍不得将船放进水里。此刻的我问童年的我:“为什么?”那个胆怯而又敏感的孩子,更加捏紧了手里的纸船。他说:“我怕它会沉,我怕它游不回来。”
戏水的人们丝毫没有察觉一个孩子的心事。河越来越宽,岸越来越窄。不一会儿,河水放肆地漫过童年的我的赤脚,漫过现在的我的赤脚……漫过梦,漫过四十年的时光。
天上的树
借着一声霹雳的闪光,那棵金色的树在翻腾的乌云缝隙里一闪。我又看见它神经质的根须,交错着,颤抖着,痉挛般地插入不远处骤风狂卷着的大地深处。那插入一定是疼痛的。大地抽搐几下,惊起一些鸟,一些虫子。奔跑着的人们,撑起伞,不敢往天上看,而泥土里,有些东西在悄然复活。
金色的树根。又一闪,树干和枝条藏在浓云之上,这暴躁而乖戾的炫耀!
以瓢泼似的泪水,不让任何生者安宁。
无数次地看见它,猜测那金色。那黄昏的颜色是刚刚获得的新生,还是早已经腐烂,即将面临的死亡?
城邦陷落
穿透冥想的是一个人的歌声。
一根无形的针,刺穿无形的雾一般变化的冥想。
没有血液流出来,没有气味飘出来,没有奇迹叫出来,甚至,它都不曾有丝毫的疼痛,时聚时散,虚虚实实,渐渐地,它已无法维持那“冥想”的招牌。
一个人的歌声,来自心灵,来自生命。一名世无匹敌的战士,冲进冥想的城邦,我向他献上一串钥匙,一本书,还有一颗头颅。
李松樟,作家,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燃烧的蝴蝶》等。
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觉着很好玩,觉得有了一种调侃和恶作剧式的开心。因为这样的句式常常被一些沽名钓誉的人用在与名人合影的说明文字上。我不想放弃这个已经程式化而且又极富幽默感的句式,所以,我就想到了猪。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真的曾有幸和猪在一起。
“和猪在一起”绝不同于一日三餐中的“和猪肉在一起”,也不是参观和接见式的临时接触,而是说我曾经和那种“生物意义”上的猪朝夕相处,就是我曾经喂过猪。那时我作为知青,队长分派给我的工作就是喂猪。我喂猪是为了挣工分,而猪就只能是猪,它只管吃食,然后负责长肉,之外也还附带着积肥。当时我工作成绩的好坏是和猪身上的肉以及它积的肥直接挂钩的,所以,我对猪的感触至今还十分复杂。现在就是把猪说成为当时我的“分工合作的同事”也并不觉得过分。
曾经帮助我赢得过赞誉,并差点使我获得“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殊荣的是一头被骟过的黑毛公猪。它体格庞大,性情温良,能吃能睡,生活十分规律,而且无不良嗜好,在我所见过的猪中堪称最“称职”的猪。应该承认,这头猪也并不是由我一手喂大的,从我一接手喂猪工作,它几乎就长成一个样板坯子了。最让人称奇的,是这头骟猪竟然能保持持续增肥的生长态势,我喂猪的时间不到半年,但它就在这期间长肉近二百斤!
要知道,那时我要技术没技术,要饲料没饲料,更谈不上现在常用的“添加剂”什么的。它的食谱和其它猪也没啥两样,都是以干草、薯蔓和谷糠粉碎后加水调和,并由我在一个铁锅内搅拌烧煮而成。我把这些东西倒入猪食槽,猪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了自己的饭食。那时人的食物也很匮乏,所以猪的生活就不可能高级。好在这方面猪和人是一个理,只要一饿,它(他)的吃相就好(肯吃)。当然,这也是我们队长教给我的道理。队长说:“毛病都是惯出来的。它不吃就饿着它!饿它三天看它吃不吃!”这之外我还掌握着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喂猪时我另外提着的半桶高粱面。这半桶高粱面理论上是它们的“饭引子”――就是在看到猪吃得差不多了之后,再把高粱面洒到猪食上,这样可以逗引它们多吃。但是,猪的嗅觉很好,尽管每次我都把高粱面藏着,可还是无一例外地让它们识破。嘴馋的和有了经验的猪往往对先倒进猪食槽里的食拱一拱或吹气冒泡地假装吃上两三口,就开始抬起猪脸望着我哼哼唧唧地等我洒高粱面。我对染上这种毛病的猪极为反感,惩罚它们的手段,就是用我手中的铁舀勺冷不丁地敲击它们的长嘴。相比之下,愈加叫我喜爱甚至有些感动的就是这头骟猪,它吃食从不挑剔,即便是不给它加“饭引子”它也能把猪食槽里加满的食吃光,而且还表演似的把猪食槽舔得光光净净。对这样懂事的猪我不能不“偏心”。在这头猪面前不“偏心”那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它越不挑食我就越愿意给它加好料。结果,我几乎把惩罚其它猪省下来的“饭引子”都挪给它当正餐了。当然,这是我和它的一个秘密,我估计它到死也不会出卖我和它之间这个秘密的。
人们把它当作了本村养猪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肯吃不挑食爱长肉也为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的脸上争了光添了彩。我们生产队的几个猪圈就在路边,其它生产队的社员出工散工都从这里经过,所以就经常有人在这里驻足围观,逢到这时我们队长的脸上就像抹了一层油彩似的滋润。有时他高兴了,还叼着个烟袋向人夸耀,说我们队里来了一个会喂猪的知青。他用这样的口气把我介绍给别人:“呶,这就是俺们队的猪倌――小赵!”队长私下里还跟我说,好好干!到年底咱也向大队里为你请一次功,说不定也推荐到县上弄个知青积极分子当当。为了他的这种夸奖差点没把我羞死。因为我同时还饲养着好几头猪,其中一头公猪正好和那只骟猪相反,它是几年如一日,怎么喂都不长肉。队里曾想卖掉它,但没有人愿意买。杀了吃肉,它又不值得让人费事!所以,它就得以那么悠哉游哉地活着。社员们为此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它猪佬――就是永远也长不大的意思。永远长不大也就意味着永远不被宰杀不被吃肉。现在想来,我觉得它简直就是活出了精神内涵的,可以和庄子的“不材之木”相媲美了。
猪佬的毛病是犯在挑食上。因为它的挑食不长肉,我们队长包括本队社员们没有一个不憎恶它的。憎恶它的结果就是使它更加怕人。它的目光不能和人接触,一发现有人看它,它就警觉地躲避。它对人的警觉还体现在对人所“赐”食物的打量上,你投喂给它再好的吃食,它都不会当着你的面吃掉,面对吃食,它选择的是与你对视,一副绝不领情的样子,好像早就看透了你的目的在于吃它的肉,而不是真心给它吃食。后来它还发展到夜间跳出猪圈自己到庄稼地里找食吃。猪圈深近两米,谁也猜不出它是怎样跳出去的。看青的民兵一次次找到我们队长讲理,我们队长就气恼地说:“你们直接把它打死不就得了!也省得让我费饲料了!”队长甚至还冲我吼叫:“看你怎么喂的猪!”
猪佬最后一次是失踪了。它失踪了大家也都没在意。但是三天后人们在一个柴草垛里发现了它。它已经死了。猪佬大概是冻饿而死的。或者说它终于厌倦了猪的生活自寻了死路也说不定。可我又想,要是这个说法成立,这只遭人鄙视的猪就不应该是一般生物意义上的猪了。它有了思想,抑或有了哲学?可一只猪有了思想有了哲学又有什么用?徒然在自己的肉体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精神上的痛苦罢了!
人们把猪佬在柴草垛里提出来一抖落,地上竟然落了一层小米饭似的虱子。那些虱子也被饿死了。队长十分厌恶地摆手说赶紧挖坑把它埋了,要不扔得越远越好。但几个社员还是坚持着把它弄到水坑边宰了,然后他们分巴分巴拿回家打牙祭去了,气得队长骂他们:“丢人败兴的玩意儿们,几辈子没吃过肉似的!”猪佬到死也没逃过被人吃掉的命运。
我实在不是个喂猪的料。猪佬死后,还死过一只母猪。那只母猪可能是得了产后风,它撇下了一窝十二只小猪崽儿死了。我又恨又气地哭过,就和队长提出来坚决不再喂猪了。但是队长这样来劝慰我,他说:“我不是看你会喂猪才让你喂猪的。我是觉得你是知青,那些高粱面多少都能吃到猪肚子里,要是换了别人,还说不定会吃到谁的肚子里去呢!”
当然,队长的说法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别以为一个人的前程就不能和猪扯上关系。我最终没有被推举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就是和这几头猪的生活态度以及它们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的。
赵云江,作家,现居河北邯郸市。主要著作有诗集《云江的诗》,另有小说散文多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