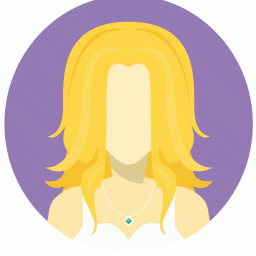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
时间:2022-08-09 07:33:24

[摘要]从18世纪初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出现所谓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欧洲人用美洲白银来交换中国茶叶,但18世纪末美洲白银出现问题,于是在绝大多数原先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淡出中国市场的时候,只有英美等少数国家仍能保持其对华贸易不坠。英国先是依靠印度的棉花、继而依靠鸦片重建对华贸易结构。其间1820年是一个关键年份,从此开始,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鸦片和棉花价值的换位,绝不能视为仅是所谓“黑货”与“白货”问的简单互换。两者的易位反映着中西经济关系由单纯的国家经贸关系向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转变,由基本平等向非互利经济关系的转变,以厦工业革命开展和美洲开始独立进程后世界秩序的重组和殖民体系的重构。
[关键词]英国 中国 白银 棉花 鸦片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100-09
一、从诸多欧美国家淡出中国市场谈起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除英美等国外,绝大多数原先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有淡出中国市场的现象。这是一个所关非细,而又未引起研究者们注意的情况。以进口来说,1764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对华出口总值为1908704银两,其中英国为1207784银两,占63.3%的比重,其他欧陆国家总合起来为700920银两,占比36.7%。此时的美国尚未形成独立国家。英国虽占大头,他国的份额也不为小。到1795-1799年度,情况有了显著变化,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5908937银两,其中英国5373015两,占90.9%的份额;美国374124两,占6.3%,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161798两,占比大幅滑落到2.8%;到1825-1829年度,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9161314银两,其中英国7591390两,占82.9%;美国1534711两,占16.7%,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35213两,占0.4%;连1%的份额都不到,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再看出口,1764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从中国输出货物总值为3637143银两,其中英国1697913银两,占46.7%,其他欧陆国家总合起来为1939230银两,占53.3%。到1795-1799年度,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从中国进口总值为7937254银两,其中英国5719972两,占72.1%;美国1399680两,占17.6%,而其他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817602两,占10.3%;到1825-1829年度,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总值为14390108银两,其中英国10215565两,占71%;美国4116182两,占28.6%,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58361两,所占份额与出口值为0.4%;同样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恰如实录:“在1828年到1829年,1艘普鲁士船、1艘丹麦船、3艘法国船、23艘西班牙船和18艘葡萄牙船到了广州,这些船只所进行的中国和欧洲间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先前对华贸易的重要国家为何要退出中国市场呢?其原因究竟是什么?于此重大变化,尚未见文论及。
除了此时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对其他列强形成挤压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先前用于对华贸易的白银出了麻烦。近年来,因为“白银资本”和“东方经济”研究的热络,我们日渐清晰地了解: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它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来丝绸在中外贸易中的霸主地位,出现所谓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但此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欧美之上,又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配及中国封建统治者时紧时松的海禁闭关政策的作用,使海外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窄。西方国家东来之际无一例外地发现,其提供的商品几乎没有一种是中国必不可少的,而中国茶叶却在该国有着愈来愈广泛的市场。所以,中西贸易呈单向流态,“而要进行以物易物的双向贸易是很困难的”。西方人急迫需求中国的东西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形成贸易一边倒的格局。但有一种东西是中国所缺乏的,那就是银子。自五代以来,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酝酿数百年,到明朝成为不可遏制之势。“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与钱贱而不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溢滥。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1436年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值(此主币体系一直沿用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而银的产量比之需求在中国更显匮乏。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银来购买中国货。据统计,英国人在1721至1740年间,用来偿付中国货物的94.9%是金银币,只有5.1%是用货物来冲抵。人华白银的最大来源地是当时世界银的最大产出地――美洲。秘鲁和墨西哥两地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正如魏源对当时中国流通白银的来源作出的估计:“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但毕竟银的生产是有底限的,长期的恶性开采使得美洲银矿日渐枯竭,到18世纪末美洲银产量开始下落。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了持续15年的独立战争,银产量比战前锐减一倍多;美洲银的减产拉动世界银产量的下挫,世界银产量在1781-1800年是28261779盎司,到1811-1820年降至17885755盎司,1821-1830年更跌到14807004盎司。而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殖民者之间的称霸战争及扩张新殖民地无休止的侵略活动使得各项费用剧增,一方面是白银减产,另一方面是银开销的增大,再者是美洲殖民地在独立运动开始后不再向欧洲宗主国提供白银;还有1779年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其银元市场被封闭,所以从1779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几相夹击,欧洲白银的缺口愈益加大。
因为拿不出较多白银来和中国进行茶叶的交换,在严峻形势下,除了英美两个国家外,大部分欧美国家只能淡出中国市场,这便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多数欧美国家大幅减少对华贸易的重要原因。英美之所以例外,耐人寻味。作为美国,除皮毛、人参和鸦片对华输出外,还依靠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传统友谊及与当地独立革命者们的密切关系,美国人还能从美洲弄到输往中国的白银。作为英国。先是试图依靠印度的棉花来换中国的茶叶,“印度和中国商业交往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印度对华输出棉花”。然后转而依靠大规模的鸦片输出重建对华贸易结构,不仅使其对华贸易保持不坠,且一举变为顺差。此文专论是时对华最大贸易国――英国的情况。鉴于中英鸦片贸易已有很多论说,但棉花贸易或是鸦片与棉花贸易地位互换的研究则基本阙如,本文着力于此。
二、一个转折年份的考订
1820年是个关键年份,是年,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鸦片输出值首次超过棉花。这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统计有些凌乱,马士(H.B.Morse)所撰被视为近代中西关系奠基性著述的两本书的数据就不一致,《对外关系史》的数字是4244箱(其中来自孟加拉和加尔各答的2591箱, 来自麻洼(Malwa)的1653箱),此数字被学者们广泛采用,数字来源是英国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根据1798-1855年从孟加拉和孟买输出到所有东方口岸的官方数字编制而成,最早发表于1855年11月3日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Herald)上;另一来源是美国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编制的1795-1835年间从加尔各答输出到中国的鸦片数,发表在1837年8月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另一本书《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数字是5906箱,其中在黄埔的来自孟加拉的鸦片894箱,在澳门的来自孟加拉的鸦片1221箱,在澳门的来自麻洼的鸦片1222箱,共3337箱,上列为英国船运人;另有英国人通过不明国籍船输入的来自孟加拉的鸦片约1500箱,和通过葡萄牙船运入的来自麻洼的鸦片1069箱,共计2569箱(此数被列在英国名下,而没有列在他国的统计栏目下,证明这些鸦片也是英人通过雇佣第三方船输入)。这些数字的来源是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鸦片交易属不愿被人知晓的秘密走私,记载不一,也不奇怪。两个数字比较起来,笔者更倾向后一数字,因为公司档案为当时的记录,而前一数字毕竟是稍后编制。吴义雄教授通过鸦片战前发刊于广州的《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等资料的比对,认定“《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鸦片贸易统计的学术价值要明显高于《对外关系史》的相关统计的价值”。此外,《对外关系史》使用的是产出地运到广州的统计,此数据往往含多国运入;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系国别统计,可以清楚地知晓本文的研究对象――英国比较准确的统计。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提供的数据下进行。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这些数字详加论证,因为它关涉到一个重大问题,即鸦片何时成为输华货品的第一大宗。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认为1823年甚或之后才出现棉花与鸦片贸易的易位,即从1823年开始,鸦片才成为输华货物的最大份额。此说大概源于1934年出版的欧文(D.E.Owen)的书:1951年,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y)在其出版的另一本流传更广的书中对这点又作了特别强调,书名是“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中文本译名《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该书指出“直到1823年为止,棉花的进口在价值上没有被第二种大宗货物――鸦片――所压倒”。谭中教授也认为:直到1827年,鸦片才超过棉花,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格林堡等据何资料作出这一判断,格氏没有说明,但阅读书后附录可以看出,主要是来自两方面的记载,其一,1823年鸦片输华数量根据马士的记载(按:格林堡的书称此来自于Morse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但翻查马士的所有著作,却并没有一本名称为Iriternational Relations的书。考究内容,此书当为马士的名著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只是格林堡有时用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时又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使译者认为其为两本书,中译本分别译名《国际关系史》和《对外关系史》。再查《对外关系史》中1822-1823年的记载与格林堡所引完全一致,数量是7773箱);其二,1822-1823年印度鸦片在华消费价值的核算,根据“麦尼克行”编制的发表于《广州纪事报及行情报》[又称《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上的统计,价值为7988930银元(比马士的统计7989000银元少一丁点,估计马士以四舍五入法得出)。
但查阅马士提供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发现1823年的判定失之过晚,英国人其实早在1820年就完成了鸦片与棉花的“地位”转换,该贸易年度,英人输华的鸦片价值6486000银元,而输入的棉花总值不过是3239931银元,鸦片价值已超乎棉花价值一倍。值得注意的是,此主要以英国为分析对象,不含他国。再证以前后几年的比较数,181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广州输入棉花价值1347586元,散商为5534916元,总计6882502元;而英国人通过广州输入的鸦片价值为1358000元,后者较前者仍有较大差距。1819年:东印度公司向广州进口棉花价值1643143元,散商进口2361583元,总计4004726元;而英国输入广州的鸦片价值为1531800元。棉花进口额仍比鸦片保持了较大优势。但自1820年后,情况有了根本性转变,1820年的数据前已列举,其后亦复类似。1821年:鸦片进口值4166250元(此数字只是英国输入,该年由悬挂其他国旗帜船并通过澳门输入的鸦片价值另有4849050元),棉花5010667元。1822年:鸦片进口值9220500元(此数尚未包括算在英国名下但可能是美国船从土耳其运入的178500元的鸦片),棉花2984998元(未包括当年美国输入的9876元)。鸦片已远超棉花进口值的两倍。到1833年,“英国贸易的规模,靠了鸦片的滋养,正在与日俱增。在十六年(1818-1833年)当中,鸦片的比重从初期的六分之一上升到后期的一半以上。印度的原棉在重要性上仅次于鸦片,约占全部进口货的四分之一”。可见,笔者将1823年的传统时间认定,修正于1820年的结论是可以确立的。正是从1820年开始,印度的鸦片压倒了印度棉花,成为并长期维持着英国对华输出货品的第一大宗。
直观来看,鸦片与棉花的易位一方面缘于鸦片输华的增加,考察印度输华鸦片最重要的产区孟加拉,鸦片收入在该省财政收入中占比在1820年时有了明显递升,1819年该省的财政总收入为12187570镑,鸦片专买为799825镑,占总收入的6%;但到1820年,该省的财政总收入为13487218镑,鸦片专买为1436432镑,超过上年近一倍,占总收入的比率也陡然提高到10%。孟买也从这年开始规模介入对华鸦片输出。“我们不要忘记,鸦片成为孟买的一种出口商品仅仅是从1820年开始的”。鸦片在华销售价格此间也有了大幅飙升,1819-1820年度在华鸦片“消费”数量为4780箱,而1820-1821年度为4770箱,两者差距不大,但从“消费价值”看,前者为5795000元,后者剧增到8400800元。另一方面缘于输华棉花的减少,1820年“孟买棉花歉收”,但此因并不重要,因为嗣后的岁月,无论丰歉,印棉的对华输出总是一蹶不振。“大约从1819年起以后的十年中,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就处于剧烈的、长期的萧条状态。1819年10月,查理・麦尼克写过一封诉苦的信给他的孟买棉花主要发货人说:我们的棉花市场多少有点古怪,虽然从你那里输入的很有限,而且从孟加拉来的几乎完 全断绝,可是并不见有什么起色和兴旺。”到1820年6月,麦尼克仍表示“很大的遗憾,因为我们的萧条的棉花市场并没有改变”。9月,“棉花的市价又进一步惨跌”。而“一年以后,棉花市场是二十年来最坏的;在广州有十万包以上搁着卖不掉,……12月,麦尼克不得不写信告诉最大的孟买棉花出口商默塞尔公司(Mereer&Co.)说:我们不能鼓励你在下一季度再作棉花买卖了”。也就是说“1820年棉花贸易完全陷于停顿;在1821年是无可挽救的萧条”。转到1823年,棉市“还处在萧条状态之中”。“在1824-1825年间,由于南京棉产的局部歉收,曾经有过暂时的好转。在听说大量存货被焚毁以后,市价又跟着有一度短时的上升――棉花市场变成依赖于这种偶然的刺激了”。1826年,棉花“完全是滞销货。在下一季度中棉花是处在最惨淡的境地。……商人们对于上一季度的亏蚀还有余痛,而行商们又避免向散商购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都必须承担东印度公司配销的棉花”。“1929年,棉花的市价更低了,最差的棉花的市价是六两九钱。有十条船同时在黄埔停留了几个月,因为他们装载的货物卖不出去。行商们自己连一包货也不肯买,只愿意做做掮客。棉花危机把孟买商业打击得很苦”。
“接着在1830年却来了一次更大的崩溃局面,那时候最便宜的棉花只卖到五两七钱!广州的棉花经纪人企图阻止港脚船卸落它们的棉花”。在华贸易人给孟买公司的信上写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大的不景气”。
三、黑白易位蕴藏的历史
鸦片战前,在中西贸易中能够改观西方对华贸易入超局面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货品。而是来自东方印度殖民地的货物,先是棉花,后是鸦片。
中国的植棉史可上溯商周,迄明朝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政府专门规定有地5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还允许“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明万历年间,“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清乾隆年间,棉花仍是“州邑栽之,以资纺织”。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的市场需求。1704年7月21日,詹尼弗(Capt.Jenidr)指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每担叫价7两银,购者还价4.5两,后以5.5两成交。这是西方输印度棉花人华之始,带有“试销”性质。不过,印棉在中西贸易中取得决定性地位还是70年以后的事,1770年代,中国发生饥馑,清政府不得已减少植棉,鼓励种植粮食作物,“导致中国对进口棉的大量需求”。1775-1779年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超英国毛织品的输入(年均额为277671银两),定位在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的位置;但1780-1884年间,英国毛织品的年均输入额达到378696银两,而印棉仅为233074银两。直到1785年后,输华印棉的地位得以完全稳定,1785-1889年印棉的输华价值是年均1698001银两,远超同期英国毛织品的年均额801879银两;自后,印棉输入更有了惊人跃进,1817-1819年,年均升至4527211银两,已是1775-1879年年均额的十余倍。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
从事印棉输华的多是“散商”。东印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不放,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口子,以颁发“许可证制度”等从中获利,并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中英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在早期散商贸易中,印棉是其获利的主要货品,只要顺利,利润率可达40%甚至更高,如1815年运入的孟买棉花赚到了进货价56%强的利润。1774-1797年,印棉的交易额占到散商贸易总额的95%以上。“这种港脚贸易的主要事实是,从印度出口鸦片和原棉,而中国对印度只输出极少量的商品”。早期印棉的来源地主要是孟买、苏拉特(Surat)和加尔各答;“在这个初期年代里,从孟加拉输出的很少,散商并不做这里的生意,直到1820年为止,孟买棉花是很赚钱的”。据统计,从1795年到1840年,加尔各答输往中国的商品以两种最为重要,一是鸦片,占出口总额的64.4%;再是棉花,占总额的27.6%。在另一个主要殖民城市孟买,从1801年到1839年,输华货物中棉花占的份额最大,为49.7%,鸦片占40%。中国输出印度的商品主要是糖,“印度西部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用古吉诺特(Guiarat)的棉花交换中国的糖”。
“棉花贸易的衰退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港脚贸易一般恐慌中最重要的方面”。为何在1820年会出现棉花和鸦片的黑白倒置,那时的人们就有许多研判。有归咎于广州行商制度的,“真可叹息,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可以公开同外国人往来的仅仅十一个人当中,有七个人即使还没有落到破产状态,至少已陷于极端窘迫的地步;由于这个原因,那四个殷实的人就勾结在一起,不受竞争的约束,经常操纵市面,现在棉花的情况就是这样。”但也有为行商辩护的,某些外商就承认“行商在棉花危机中也同样受到损失――由于市价跌落,有些人也破产了。行商中货币的空前缺乏,部分是因为大量资本都呆滞在棉花上”。还应该看到,那时的广州行商代售棉花的利润率的确很低,大致为每担0.2657两银子:即便如此,也“经常发生亏蚀。如果中国的棉花商人拒绝采购,他们的存货就卖不出去,可是他们――行商们――在进货三个月以后必须付给欧洲进口商的价款。每一船货载都被认为是一桩单独的冒险生意,并且常常是在六、七个月以前口头商定的。但是,尽管有这种契约,偿付价款常常是同行商争论不休的问题”。棉花易潮,行商坚持外船到港后现场看样购货,“但外商不愿意这样做”。也有的反过来归因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据在棉花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巴斯人(Parsee,为“散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抱怨:“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处于剧烈的、长期的萧条状态。巴斯商人们把这种情况归罪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制度。”还有些外商将此归咎于在印度的“无理由”抬价,“好像这种货色在这里几乎永远可以获得最大的价钱”。某些西方人还提出中国对印度棉花需求的减少,是因为中国运输方法的改进。“中国本地棉花,已经改变了过去由陆路运输的习惯,用帆船运进广州,这就使它在市场上的卖价比以往便宜得多”。再有是英国方面对信息的不了解,“除了中国人对于印度棉花的需要是决定于南京棉产量之外,他们知道得很少”。但上述说辞都无法解释印棉对华出口由盛转衰的内在缘由。实际上,黑白的倒置主要是受中国和英国两国市场的制约。
在中国,进口的印棉只起着一种补缺作用,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棉花生产,明清时代“棉花,色有紫、白,种有早、晚,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邑人藉之,以给衣食”。显然,棉花在中国有着普遍的种植和发达的交易。所以,印棉输华受中国国内棉市的影响很大,也可以说,价格的波动与中国棉花的收成息息相关,特别是同中国棉花消费的两个最大市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密切关联。“广州的棉价决定于中国收获的情况,并不是决定于从印度进口的数量。这种情况在孟加拉棉花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它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仅只在‘南京棉’歉收的时候送到内地 去,因为它同南京棉在质地上很相近。”如1805年,“麦尼克商号”按照与行商“浩官”的约定运至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浩官”认为是“陈货”,拒绝接收,“别的行商都不肯碰一碰棉花包”。末了,“浩官”还是降价收购了这批棉花,却为此亏了1万多元,原因很清楚,棉市滞涨,卖不出价钱。谁知,第二个贸易年度,因为中国棉花歉收,棉花转成俏货,这年输入了大约14万包(31万担),正常年景约输入6万包,在华经营多年的外商惊呼这是“一种没有听说过的输入”。价格也好得惊人,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创下每担十四两五钱的新高,“质地恶劣”的苏拉特棉也卖到十一两五钱银子的价钱;这只是广州价格,在南京可以卖到32两。但几年后,“广州市场上的棉花又几乎等于是死货,有几个行商手上还压存有一两年前买进的棉花没有卖出”。这一切造成东印度公司在华采购茶叶的巨额入超,需要用印度棉花来部分弥补,而印棉却完全受中国市场制约,价格和输入量波动不定。“棉价的主要波动――有一个贸易季度它的波动幅度大到将近三分之一――是和质量无关的”,“印度棉花在中国的售价从而它的利润都决定于中国收获的情况,这就使英国输入商不能事先精确地断定下一季度的需要。……中国本身是一个大的产棉国家的事实,不仅是印度棉花扩张可能性的限制,而且是那些依靠棉花作为‘大宗货物’的外国商人的永远存在的威胁。”
在英国,印棉入华还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尽管“cotton”一词在英语中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可是直到17世纪,该词更多的还是指英格兰北部制造的某些粗呢毛织品,而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棉花”。据认为1585年亚历山大・法内塞攻占了安特卫普,许多工人移居英伦,才开始英国棉纺业的起源。约1640年,棉纺业才在后来最富盛名的棉纺中心曼彻斯特“生根”。此间,英人穿着的棉织品,仍多依赖东方。这也同传统的毛纺业发生竞争和冲突,毛纺织工人纷纷请愿,1700年,英国议会竟然颁布法令,严禁中国、印度、波斯的印花织物输入。外来纺品受到禁限,民众又需要穿用,英国自身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加上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宜于棉纱的纺织,简直就是一座物候天成的大纺织厂,棉织业因此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历史起点和时代典范。1733年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发明使织布速度加快一倍,纺与织部门间的平衡打破,造成纱供应的不足和技术改造的急需。1761年,“英国奖励工业学会”特别公告:鉴于棉纱的不足给“人民带来很大损害”,特设奖金来奖励发明一种能够同时纺出“六根棉纱或六根丝线的,并能仅由一个人操纵和看管的机器”。突破迅速出现,1764年,“珍妮多轴纺纱机”问世;1779年,克郎普顿(Samuel Crompton)把多轴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集合,发明了混合走锭精纺机;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蒸汽机的纱厂也于这年建立;1788年,英国已有143个“装有自动设备的纱厂”,英伦岛上的动力织布机则从1820年的14150台增加到1833年的100000-105000台。纺织业通过动力蒸汽机率先实现了由小手工业向近代工厂的过渡。又通过蒸汽机与煤炭(后来还有电)、钢铁、机械制造等部门密不可分地联在一起,成体系的近代大机器工业革命在凯歌行进。
棉纺业的迅猛发展又带出新问题――“棉荒”,英国不产棉,原料依靠进口,美洲和印度是其进口棉花的主要地区。为获得廉价原棉以供英国纺织工业需求,殖民当局鼓励印度植棉。18世纪下半叶,印度引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从此印度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1701年,输入英国的原棉不过100万磅;1802年达到6050万磅。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坐视印度原棉大量流入中国?何况,它还牵扯到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中英两国棉纺业的竞争。东方的棉纺品输入西方远比西方的棉纺品输入东方要早,1734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命令来广州的商船“哈瑞森号”(Harrison)等“购买南京手工织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南京布”(Nankeen),这种以松江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出产的手织棕色或紫花土棉布后来几成中国优质棉布的代名词,在欧洲成为时髦人的衣料。而到1786年,曼彻斯特等地的农户手织棉布样品才被送到广州鉴定,结果是“没有一样符合市场的需要”。1790年,来自英伦的100匹棉布进入中国,“它们不大受欢迎,因为价钱太贵,不及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好几种制品”。届1819年,英商试图在广州用拍卖方式来推销样货,结果是“衬衫料子几乎完全销不出去――他们说它是他们的夏布的仿制品(当然仿制得也很差)。条纹布也不受欢迎”。英国质劣价高的棉织品在中国打开销路还需时日。到1833年,“棉布(紫花布)在当时还是从中国输往西方的一种货物,轧棉机、纺织机和电力织机还没有来得及扭转这个流转的趋势”。这一问题直到后来在工业革命的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浪潮席卷下方才迎刃而解。由此可见,棉花被鸦片取代是在工业革命开始(惟其开始,才需要大批量的愈来愈多的棉花),又在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特有时代中出现的状况(惟其未完成,故无法大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棉纺织品来倾销中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其工业品对中国构成价格和质量优势,鸦片愈来愈成为其倾销工业品的障碍。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国转而要求中国禁绝鸦片。
故,造成19世纪初叶中国与西方贸易全局变动的不是棉品,而是鸦片。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荷兰人将印度麻洼及果阿(Coa)、达曼(Daman)等地出产的鸦片和枪管灼火的吸食方法传人中国。1729年,中国年输入鸦片达200箱,也在这年,清廷对愈益严重的鸦片吸食有了反应,颁布第一次禁烟诏令,惜效果不彰。1773年是一个象征性年份,这年,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哈斯廷(W.Hastings)提出由东印度公司承揽鸦片,建立“收购承包人制”,英国的鸦片贸易以政府同大公司的联手实现垄断专营和规模体系,迅即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商家。而此前的普拉西之战使英国征服了孟加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鸦片产地――麻洼、比哈尔(Behar)、八达拿(Patna)和比纳莱斯(Benares)等均在英国控制下。“港脚贸易旧基础的普遍衰落,特别是棉花市场衰落的最显著的以及最重要的结果,是全力经营鸦片。在其他进口货的利润――即使不是数量――缩减的时候,鸦片的进口大量地和稳定地扩张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广州行号所找来的很多新往来户和人,特别是在孟买的,都是鸦片货主”。
值得注意的是,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成为鸦片战争前长期存在的现象。姚贤镐将1817-1833年中国惟一的开放口岸广州的主要进口商品分为“西方产品”和“东方产品”两类,其中产自西方的产品货值不及东方产品的1/3,这既是世界资源生成和经济地理配置的表现,又是殖民地经济的反映,西方殖民者从东方攫取资源再向东方进行交易,换取西方需要的钱物,产品出自东方,赢利却是西方。而在“东方产品”中,货值最高的便是棉花和鸦片,其余不足挂齿(如檀香、锡、胡椒 等)。即或在1820年之后至鸦片战争前夕,英国统计资料也表明,其对华出口商品的最大宗仍是鸦片和棉花,棉花年均进口50万担,每担均价10元,年均进口值500万元。而此间中国茶叶年均出口总值为945万元。如果不算上鸦片的进口,中国仍将保持顺差。
对人华鸦片和棉花价值的换位如此较真,确因该问题所关非细。它绝不是黑色鸦片和白色棉花的所谓“黑货”与“白货”间的简单互换,也不是两种输华货品的一般易位。棉花输华的背后,是促进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加强中国棉纺业与英国棉纺业的竞争力,中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输入大量的海外棉花,正如《海国图志》所描述:孟买左近“邻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而其棉纺织的部分成品市场又在海外,这种原料市场两头在外,中国负责加工的国际协作方式,必然以中国棉纺生产的技高一筹、质高价廉作为依托,这种纳入国际分工环节和流通领域的状况对中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生成必定是很有帮助的。输华鸦片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种毫无益处的废物,又不简单是一种废物,它在毒害中国人身心的同时榨取其财富,西方殖民者几百年追求未得的白银由中国转流欧洲的企望,经鸦片贸易的途径得以实现,完成了英国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全然改观。在鸦片规模贸易之前,是白银流入中国,之后,是白银流出中国。通过鸦片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出中国,各方面的统计很不一致,有学者认为“19世纪20-40年代,白银的流出量合计约达4.8亿两”,或有高估。新近研究表明,1807-1829年间,中国约有4000余万银元被英国人运出广州口岸,而1829-1839年间,中国的白银净流出量约为6500万银元。结果是“纹银为内地之至宝,今外夷烟土不以货物与我易,必以纹银向之买,计三四年间,为数已数十万万”。(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简称F.O.233/181/35)1836-1837年,清朝有关方面展开有关鸦片弛禁的讨论,赞同者与反对者的观点对立,却又殊途同归,立足点都是从日趋严峻的白银问题来考虑,反对弛禁的想以严禁鸦片来防止白银外流:赞同弛禁的则以高关税来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杜绝走私,并实行鸦片的以货易货,不让银子出现在鸦片交易渠道,“惟鸦片进口后止准全行易货,回帆不得带回银两出口”。(F.O.,233/180/18)时人把“一年数千万之纹银不为外洋席卷”,看作是那个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若能解决,“从此民财日盛,催税日盈”。(F.O.,233/180/45)情势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的地步,终于促使道光帝在1838年下了严禁鸦片固塞白银外流的决心。
在1835年前的10年中,鸦片使印度的“土地价值提高了四倍”,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10倍;鸦片收入提供英印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1/7,“而且用不着使印度贫困就给英国每年带来600万镑”的纯利进入国库。我们明了这一切,也就能明白殖民者选择鸦片打开中国市场的内在推力,明白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和选择中国。鸦片与棉花的易位,从深里说,反映着中西经济关系由单纯的国家经贸关系向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转变,由基本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向非互利的变相奴役性质的经济关系转变,以及工业革命开展和美洲开始独立进程后世界秩序的重组和殖民体系的重构。鸦片堪称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英-中-印三角贸易的基石。进而可解,为什么在1838年清政府实行严厉禁烟政策后,英国政府要作出如此强烈反应――为邪恶的贸易不惜打一场国际战争,因为这个基石在英国殖民者是万万不能抽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