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媒体对聋人的称呼
时间:2022-08-01 06:0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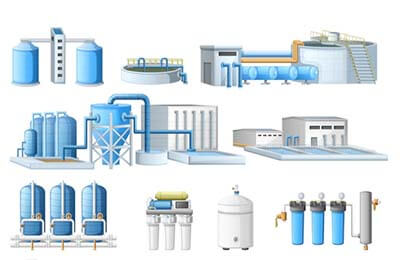
黑白分明
前几年,曾经参加过一个全国性的特殊教育者工作会议。一位与会的香港聋教育专家曾经提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内地是怎样称呼聋校的学生的?”当时有些愕然,不知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有的说称“聋哑学生”,有的称“听力障碍者”,有的则叫“聋生”,大家都在面面相觑,等待着他的正确答案。
由于现在国家对外窗口都打开了,也明白了当时主讲者的提问意图了。从一个简单的称呼可以看到我们对聋人的认识是否科学,聋人是否得到了人们应有的尊重。比如“聋哑人”、“哑巴”、“健全人”、“健听人”等。
我认为将聋人称为“聋哑人”,或将聋校称为“聋哑学校”都是有违科学的严密性的,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聋人只是听力障碍,并无咽喉疾患。不会用口语说话的原因也是因听力障碍干扰了自己对发音的控制而导致的“哑”状。文艺小品和媒体中称呼聋人为“哑巴”的现象是最遭聋人唾弃的。因为这个称呼中包含了对聋人的鄙视和嘲笑,是对聋人人格尊严的严重践踏。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懂得互相尊重的社会,没有残疾人,只有残疾的社会。将听力障碍者称为“聋人”(听力程度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称呼另当别论),将无听力障碍的人称为“听人”。这也是一种互相尊重,互为平等的象征,希望各宣传媒体和文艺作品能真正地把好对聋人的称呼关,因为他们是社会文明的导向。
心 月
都说人民群众是语言的创造者,一般在平常的交流中,别人说我是“耳聋的”或者“大听的”,再没其他说法了。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接受“耳聋”两个字。只要别人说话没有恶语,就不能认为凡说“耳聋”“聋哑”之类的字眼有侮辱之意。有些聋人太在意自己的残缺,对别人说什么都要细抠字眼,实在没必要。许多事物都是约定俗成的,对聋人的叫法也不例外,当大众习惯某种叫法,就会脱口而出,他根本不会考虑是不是有侮辱之意。有人向我调查倾向于哪种叫法,我回答:听障人士。我的理由是既然聋人不敢正视“聋”字,那就避“聋”吧。
襟眼簪花
呵呵,不管是聋人也好,听障人士也好,都只有一个共同点:耳朵都不太灵光。
因为这个共同点,我们才能成为朋友。我们又何必过于咬文嚼字、斤斤计较于“聋人”和“听障人士”里面侮辱成分有多少呢?也许只是他们说者无心,而我们听者有意呢。何必自寻烦恼?何不把这些时间用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呢,这样岂不是更有意义?争论啊,争到何时方休?即使能争论到尽头,又能争出什么来?
从故乡到异乡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昨天晚上,学生告诉我,他刚从公安局那里回来,是去做手语翻译的。那里有个聋人犯罪团伙。我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后,心里很沉重。当时我忽然有个冲动,想写写关于聋人犯罪与教育方面的帖子。
于是我问了网蝶老师,说明了来意后,问她那里有没有关于聋人犯罪问题的材料?老师告诉我,今天拒绝了一个电视新闻单位调查聋人犯罪问题的手语翻译要求。我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要拒绝?她只回答我一句话:拒绝反映聋人负面影响的报道。
哦,我明白了。一切尽在不言中。感激之余,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有人说:其实,在我看来,名称只是一个代号,关键是要提高整个聋人群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既需要他们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我可不同意这个观点。名称并不只是一个代号,它包含着语者的思想倾向和某种态度。而对于“提高整个聋人群在社会中的地位”,我认为,聋人自己努力固然重要,但是舆论导向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标签作用,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春使心
以我的自身来说,刚聋时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但现在我完全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只尊重事实,事实如此,我只能坦然接受。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懂得扬长避短,可以做到听人所不能及的事,让听人只有尊重、不敢小瞧我的份,这就是我的自信。所以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聋子,我跟陌生人交流时,猜不出他(她)的意图,我就说我听力不好,或用笔谈或要他(她)打简单的手势。
其实怎样称谓,我认为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这个社会中独立,能在这个社会中有出色的表现,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力量、智慧和勤奋,要让人尊重你,靠的是我们自己。
快乐天使
如能统一用“聋人”这个称呼诚然最好,但它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与社会文明进步有关。
就拿“聋人”这个称呼来说,虽然是个简单的名词,但在不同的人眼里却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可以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聋人”两字承载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聋人”一个简单完整的意思呢。
“听人”这个称呼是如何出现的?我想听力正常的人,是没有必要使用这个称呼的,起码在他们看来“听人”这个称呼是多此一举的。同样,“聋人”这个称呼又哪里令人敏感了?我认为真正敏感的是聋人自己。同样是“聋人”这个称呼,有的人看到的是后面的“人”字,然而,有的人想得更多的却是前面的“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