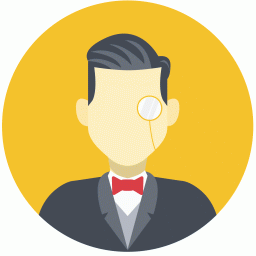巴金《家》的三种爱情模式及意义简论
时间:2022-06-09 09:34:36

摘 要:在《家》的三种爱情模式中既有古典爱情模式的再现与重演、继承和异变,亦有新型爱情模式的建构与传达。三种模式隐含着作家的深层创作动机与叙事意图,体现出反叛与革命的意识形态旨归。
关键词:《家》 爱情模式 文化原型 意义
一、引言
长篇小说《家》是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为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充满了青春色彩和激情,传达出在新旧文化转型期“父”与“子”、“传统”与“现代”的种种矛盾和纠结,体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在对家族悲欢离合的历史叙述中,高家三兄弟的爱情叙事显得分外动人,它们代表不同爱情模式,呈现不同的爱情景观,也承载特殊的文本意义,隐含着深层创作动机和叙事意图。
二、爱情模式之一:古典爱情婚姻悲剧的再现
在古典爱情婚姻故事中,模式结局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式爱情婚姻喜剧,另一种是“有情人不成眷属”的“好梦难圆”式爱情婚姻悲剧,它们透露出人类社会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普遍的美好期待与渴望。古典的爱情婚姻悲剧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与《牛郎织女》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悲剧经典而流传不绝,成为民族对美好圆满爱情婚姻渴望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东汉的长篇爱情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典型的婚姻悲剧,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妻为捍卫自身婚姻爱情而坚贞殉情的故事强烈地控诉家长专制的罪恶。在历史长河中,类似的婚姻悲剧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与表妹唐琬,也因母亲的专断干涉而使唐琬被迫改嫁并最终抑郁致死,却无意间成就了他们的千古绝唱《钗头凤》。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更因宝玉、黛玉、宝钗三人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爱情悲剧传统和悲剧精神发展到顶峰,发出耀眼光华。
觉新与梅、瑞珏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因浓厚的传统爱情婚姻悲剧色彩而显得刻骨铭心、哀怨缠绵与愁肠百结。觉新和表妹钱梅芬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他们本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却因双方家长一时赌气和嫌隙而“棒打鸳鸯散”。他们的命运也由此改写,梅嫁与他人后很快守寡,因不能忘情于觉新最终抑郁而死。觉新屈从家长意志,凭着家长偶然性的拈阄与素未谋面的瑞珏结婚。幸而这位女子善良忍耐、温柔贤淑,给觉新减轻了精神苦痛,补偿了一些心理缺憾。然而,这位贤惠端庄的女子最终未能逃脱传统迷信的阴影,为避“血光之灾”被迫到城外分娩并难产而亡。
觉新与梅、瑞珏之间的三角婚恋关系从文化原型看是古典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的复合交织,也有着《红楼梦》的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三角婚恋关系的痕迹。他们的爱情婚姻毁灭既来自家长们独断的权力意志,也和自身悲剧性格密不可分,是主观因素和外在家长专制横加干涉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觉新是位既受新思潮影响又背负传统文化重压的典型形象,因长子长孙的特殊地位,这位代父行职的年轻人在处世中奉行“作揖主义”、不抵抗哲学。这种消极被动的人生理念表现为对家族内部明枪暗箭伤害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缺乏自我的人格意识和抗争精神,呈现出精神人格的多重性分裂,这使他深爱的两个女子成为无辜牺牲品。钱梅芬和瑞珏形象具有古典女性特征,她们也是传统文化的背负者。梅的忧郁气质像极了唐琬和林黛玉,她们为爱而死的结局也惊人相似。瑞珏的温柔贤淑、善良大度和薛宝钗有几分神似,但瑞珏的结局要比宝钗更加悲惨,她是以死亡为代价成为传统迷信的无辜牺牲者。因此,觉新与梅、瑞珏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古代家长专制“棒打鸳鸯”的再现,他与瑞珏婚姻悲剧是古典婚姻悲剧的重演,二者皆反映了古典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婚姻理想在新旧文化转型期的幻灭和悲哀。
觉新的现实原型来自巴金大哥李尧枚,现实中的他没有觉新那样幸运,而是选择了自杀,这使巴金的情感更加愤激和痛苦,更坚定创作信念以拯救受压迫的无数年轻生命。觉新形象因具有他大哥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而显得格外复杂。梅的现实原型来自巴金的一位表姐,与他大哥感情很好,全家年轻一代都希望她成为他们嫂嫂,但因姑母不喜欢“亲上加亲”而未与大哥结合。据巴金回忆,这位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十几年内生了一大群儿女,成为爱钱如命的可笑胖女人。通过文本内外对比,钱梅芬这一人物形象反差具有天壤之别,不像觉新那样性格里有许多现实原型影子,那么,在对这一女性形象塑造时,作家精神意识深处不自觉地倾向了传统文化中温婉女性的类型,成为传统文化中天使类型女性在文本中的重现。另一传统女性形象李瑞珏的性格和现实原型的性格和经历不同,虽然她也有祖父死后被迫搬到城外茅舍生产的经历,但并未因此而难产身亡。通过文本内外比较可以看出,作者正是借助古典才子佳人爱情婚姻幻灭的悲剧模式,达到批判传统道德和家族罪恶的意识形态目的,“加工证明了意识形态完满性对作家的控制,意识形态的交战杀死了小说中的人物。”[1]
三、爱情模式之二:古典爱情喜剧的异变
古典爱情故事中与爱情婚姻悲剧相对照的是古典爱情婚姻喜剧传统,举案齐眉、琴瑟和鸣是这类大团圆爱情婚姻的共同图景。一些历史人物的美满爱情婚姻往往也为后世人们津津乐道,范蠡与西施的泛舟西湖传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当垆卖酒的佳话,梁鸿与孟光的举案齐眉,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志趣相投等等,给后人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元代王实甫的戏剧《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和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是古典爱情喜剧的经典,反映特定时期怀才文人精神与意识深处“金榜题名”的前程事业与爱情婚姻双重圆满的浪漫主义梦想和幻想。
在小说《家》的第二种爱情模式中,作家承继了这种古典文学的爱情表现传统,对觉民和张蕴华(琴)的爱情结局设计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类型,是对觉新与钱梅芬和瑞珏的第一种悲剧爱情模式的调和平衡。这种爱情模式的设置和觉民与琴二人的自身性格分不开,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是新人,接受过新思想洗礼,都有叛逆精神和共同理想追求,在精神方面能达成默契,可谓“心有灵犀”,并且他们有过较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对彼此性情有更多了解,这是他们产生爱情和成功结合的内在基础。觉民作为高家二少爷,他沉稳冷静、平和谦逊,具有中庸内敛的精神气质,其接受新思想的程度要比觉新高,同时又没有觉慧的激进激愤。琴作为新女性形象,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同校,并主动带头剪发,具有追求自由光明和个性解放的意识。
其实,细读文本还会发现,他们二人之所以能成功还有相似家族背景的天然优势。二人社会地位、身份门第相当,并有亲戚关系,可谓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因此,他们最终获得琴思想开明的母亲的同意与支持。觉慧曾羡慕这一优势,总幻想鸣凤有琴那样的身份地位和学识见识,这样鸣凤在自己眼中就完美无缺了。门当户对是传统婚恋文化的一种重要观念,在古典爱情喜剧中,这往往是考验男方的“门槛”。《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爱情圆满的实现,需要在张生取得同等社会身份和地位之后。一介贫寒书生最终金榜题名,有了功名仕途,才有与崔莺莺喜结连理的政治资格,方能获得崔夫人的点头应允,成就美满幸福姻缘。《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婚恋可谓超越时空生死,却无法超越门第身份的藩篱。柳梦梅终究要考取功名,成为新科状元之后奉旨赐婚,方能成为岳父大人的乘龙快婿。“落难公子中状元”往往是古典爱情喜剧的一个重要甚至关键的条件。
觉民与琴逐渐发生心灵共鸣并互生情愫是自然而然的。当高老太爷答应好友冯乐山把自己的侄孙女嫁给觉民时,他坚决拒绝,表示要作自己爱情婚姻的主人,绝不重复大哥的爱情悲剧。在觉慧帮助下,觉民成功逃婚并和琴一起勇敢地捍卫他们的爱情,最终取得了爱情保卫战的胜利。这是新爱情思想对传统婚恋观的胜利,“对奔向新前程的孩子们来说,它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和政治进化乌托邦的情感对应物……”[2]他们不会重蹈大哥的覆辙。文本外琴的现实原型并非像琴这般快乐如意,健康地奔向光明和希望,而是被家庭的牢笼所囚禁,最终成为一个性情古怪的老处女。文本内,作家则给她安排了理想的人生方向和爱的归宿。
觉民和琴的爱情模式显然是古典爱情喜剧的变异,只是转换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将爱情双方换成一对具有现代叛逆精神和革命性的新人而已。从某种程度意义上说,这也是古典才子佳人爱情理想的现代实现,为的是突出新旧文化转型期一代新人的反叛精神和抗争意识的严肃意义。
四、爱情模式之三:新型爱情悲剧的建构
与前两种爱情模式不同,觉慧与鸣凤的爱情叙事是一种新型爱情叙事,它的新型就在于爱情的双方有着天差地别的社会地位,是一场少爷与婢女间镜花水月的爱情幻梦,对于鸣凤来说也是一场无法超越的命运悲剧。
觉慧在高公馆中一直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出现,他的人道主义和泛爱思想即是叛逆精神的初始动力。由于五四新思想的启蒙和特殊的童年经历,这位高家三少爷对于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产生同情和怜悯,这是一种包含有美好人性精神的闪光,特别是年轻婢女的温柔美丽和纯洁善良以及她不幸的双重弱者地位更容易引起这位具有泛爱思想少爷的怜香惜玉之感,激发起他对于弱者的同情心和保护欲。在同鸣凤不断交往中,他的人道同情和泛爱思想复杂地与男女间的爱情混同纠结在一起。凭着一时的青春期冲动,这位叛逆者在高家梅林未经深思熟虑就许下要娶鸣凤作三少奶奶的爱情盟誓,这给了一个在底层挣扎渴望被拯救的少女一线命运转机的希望和生存动力,同时也给了她一个美妙虚妄的幻梦。另一方面,觉慧又伴随着两人之间社会等级和身份差异的矛盾焦虑,遗憾于他们之间无法跨越的身份地位的鸿沟。他不自觉将作为丫鬟的鸣凤与作为小姐的琴表姐反复比较,幻想鸣凤有琴的社会地位和门第身份,这正是叛逆者深层精神中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碰撞冲突纠结的无意识流露,其内心深处渴望的仍是传统范畴的才子佳人完美结合的理想爱情模型。正因如此,在鸣凤死后,觉慧才有那个将鸣凤的婢女身份置换为小姐身份的雨夜之梦,它正是门当户对情结的潜意识表达和愿望的象征性满足。
就鸣凤而言,这位底层少女有对自身不幸命运和处境的顾影自怜,也有像小姐少爷般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梦想与渴望,更幻想有位英俊少爷能够将她从生活与命运的泥潭中拯救出来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位底层女孩的愿望和意识正是灰姑娘情结的体现。当然,她也是矛盾纠结的,当她回到自身现实处境时又不禁心灰意冷。在这样的心态下,她和觉慧开始了鲜为人知的秘密爱情冒险。在她眼中,这位少爷是她逃离底层命运的“诺亚方舟”和全部希望。鉴于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她将改变自身处境的梦想降至最低,卑微地希望成为他一个人终生的专职女奴。因此,鸣凤对觉慧的爱情是混杂了被拯救的成分在其中的,并不是两人精神世界的“心有灵犀”和默契共鸣。
这个女孩子尽管跟觉慧姐姐认识过一些字,但毕竟不是系统完整地接受文化熏陶和教育,更没有机会像琴一样接受新思想的启蒙洗礼。尽管她有善良温柔、单纯刚烈的本性,其内在心灵空间在文化方面的确是狭窄的,她无法想象和理解觉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也无法理解觉慧在家中所时常体验到的“狭的笼”的窒息感和孤独感。这也是觉慧时常矛盾焦虑和游移不定的根源和烦恼所在。他甚至对这种情感关系产生厌倦和离弃的念头,“那青年底女儿一对眼睛和那广大的世界比起来,算得什么呢?那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够单为它们而放弃一切的。”“所以在他底脑里的战斗,鸣凤是决然地失败了。他是准备着到了某个时候便放弃她。”此时的鸣凤对这种微妙心理变化一无所知,仍做着被他拯救的玫瑰色幻梦。
在他们外部条件和内部精神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因两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无法进行更宽广的精神灵魂的交流沟通,这场所谓的爱情注定是一悲剧。即使冯乐山不讨鸣凤作姨太太,一旦觉慧为所谓的社会责任和事业放弃她,那么,对鸣凤的打击同样是致命的,她的选择也许同样是死亡。在鸣凤最后欲求救于觉慧的短暂日子里,觉慧各种各样的繁忙情形让人预感到,这是他准备放弃鸣凤的不祥前兆和牵强借口。他曾听说冯乐山要在鸣凤和婉儿间挑选姨太太的传言,在鸣凤欲言又止的哀伤凄苦和痛苦不安的表情中怎会觉察不出蛛丝马迹?其实在他得知鸣凤要被冯乐山纳为小妾前一天,就已经产生毅然放弃鸣凤的念头。在鸣凤死后,他所谓的忏悔自责也不能说没有真情因素,但同时让人感觉这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的自我表演和情感宣泄,显得苍白而空洞。在鸣凤死后的日子里,他不久便将鸣凤遗忘,将空虚情感逐渐转移到琴表姐身上,并因此与伦理道德发生冲突纠结,透露了他们爱情关系的脆弱与虚妄。
鸣凤的现实原型是一个叫翠凤的寄饭丫头,她严词拒绝做巴金远方亲戚的姨太太,甘心嫁给一位贫家丈夫,可见作家深层创作目的和叙事意图显然是以女性的死亡成就叛逆之子的成长突围,成为其走向社会寻求新生和光明的动力源泉之一,“她们圣洁的幻影并不表现女性生存的真相和女性愿望的真实,只不过是男性青年反叛父权专制、反抗社会压迫、进行自我拯救时忠心忘我的助手兼随手可抛的工具。”[3]可以辩证思考的是,这种新型爱情悲剧叙事的背后也许透露出作家如觉慧般的矛盾游移与表达焦虑。
五、结语
从以上三种爱情模式可以发现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动机与叙事意图。第一类爱情模式意义在于,它是作家对大哥深沉纪念的有效方式,有着以此控诉抽象制度罪恶的心理动机。第二类爱情模式意义在于是对第一种模式的对冲、调和和平衡,是对反抗家长意志的叛逆者们的精神奖赏。这两种爱情模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关系,互为印证,共同传达出作家深层的意识形态旨归。第三类爱情模式作为新型爱情悲剧是一个近似拯救与被拯救的爱情叙事,虽然它同样是作家用来批判“敌人”的道具,同时也是作家试图构建的一种爱情关系的可能性,包含了作家对这种爱情言说的矛盾焦虑,使得它成为可拓展阐释关于门第地位、社会身份、家世背景、教养性格、精神层次、忠诚与背叛等很具张力的想象空间。
注释:
[1][2]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92页。
[3]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参考文献:
[1]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