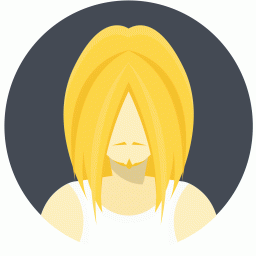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妇女剪发放足运动述论
时间:2022-05-15 03:25:59

摘要:在革命潮流的影响和国共两党的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群众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妇女剪发放足运动就是其中一抹亮丽的缩影。这场旨在解放妇女的群众运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于革命政权不稳定、革命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不同声音未能得到合理宣泄等原因,武汉等地的妇女剪发放足运动很快归于沉寂。
关键词:武汉国民政府;剪发放足;革命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137―04
梳髻和缠足是中国妇女沿习久远的社会习俗。近现代女子剪发放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生活面貌,这一现象因此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总体上看,虽然学界对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剪发放足问题研究比较深入,且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妇女剪发放足运动的研究似乎略显不足。①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妇女剪发放足运动作为近代妇女剪发放足史上的重要一环,影响了之后数十年间国共两党剪发放足运动的基本走向。②本文试图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妇女剪发放足运动的历史背景及阶段性特征做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妇女剪发放足运动发起的主要原因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妇女剪发放足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所营造的革命气氛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助推。此外,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派的大力支持及各级妇女协会的组织领导等不无关系。
“剪发放足也是革命。”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革命重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新的社会风气也随之吹遍武汉地区。“在这革命中心的武汉,好像人人都革命化了;好像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其思想行动,都通通革命化了”,以致“剪发放足也是革命”成为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③由此可见,剪发放足在当时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据曾任汉口妇女部部长的黄慕兰回忆,1926年她参加革命的标志就是剪掉长发,④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耀眼标志”就是剪掉了辫子。⑤当时汉口报纸有孙传芳在上海将凡是穿西装和剪发的女子都当成便衣“赤党”予以逮捕之类的报道,⑥则从反面强化了“剪发就是革命”的观点和社会心理。另外,当时武汉地区缠足妇女之多,令苏联来华人员都“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觉得缠足女童的神态“特别令人心酸”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者对缠足妇女的同情和废止缠足的坚决态度。
1927年召开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直接推动了两湖地区的剪发放足运动。汉口泰安纱厂工会干事张金保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后,带领汉口工人武装训练班的女工剪去了头发。⑧武汉国民政府辖下的湖南长沙地区也在开展剪发运动,中国湖南省党部机关报《湖南民报》还对那些没有剪发的革命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现在有一班革命者,至今还把几根头发存留着,今天一个洋耶史头,明天一个面包头”,他们既然“有这些空费的精神,有这些空费的时间,为甚么不将她全然用在革命工作上?”⑨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即使是革命者也未必人人都剪发,但这些未剪发的革命者受到批评则反映出“剪发就是革命”的正当性。国共两党都希望通过改造妇女的生活面貌,为外界和当地民众树立妇女的崭新形象。国民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北伐战争,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20世纪20年代初期,两湖地区的妇女剪发放足运动呈现出民间自发与政党动员相结合的特征。1925年,中共武昌区委成立了武汉妇女协会。同年7月,中国湖北省党部将之改为湖北省妇女协会。北伐军入汉后,妇女协会的活动由秘密逐渐转为公开。不久,又改选汉口市妇女协会,并成立了新的武昌市妇女协会。⑩各级妇女协会受中国各级党部的妇女部领导,并且各级妇女协会与各级党部的领导人员大致相同,其中不乏跨党党员。据曾任中共湖北省妇女协会秘书的袁溥之回忆:“省委妇委、妇女部、省妇协,三块牌子一套班子。”只是妇女协会作为半官方的民众团体,成员范围更广泛一些。1927年3月前,湖北省妇女协会的中心工作主要是组织开展放足运动和识字运动,直到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时,其中心口号才变成“剪发”与“放足”。
二、妇女剪发放足运动的阶段性特征
综合考察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妇女剪发放足运动,不难看出其中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运动前期不仅规模大而且涉及面广,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运动后期因受时局等因素影响,渐渐趋向沉寂。
为了推动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1927年3月8日,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并在汉口举行了群众大会。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决定对放足、识字、职业、教育、参政等问题进行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武汉党政要人詹大悲在大会上呼吁要解放妇女必须解除妇女身上的锁链,因为缠足残废我们妇女同胞的身体,而蓄发后因每天梳头照镜,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他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剪发放足运动,这样才能使广大妇女求得解放,得到真幸福。大会决议“从今日起湖北各地妇女严禁缠足,已缠过的一致起来解放”。詹大悲本为著名报人,深谙社会心理的转移,他将剪发放足与“革命工作”相联系,正与当时的革命潮流相呼应。天津《大公报》在3月20日突出报道了詹大悲关于剪发放足的演讲内容。天津《大公报》为民间文人所办报纸,新闻敏感性极强。这就意味着女子剪发放足已经成为关系妇女解放的核心问题。剪发开始时多为革命者的自觉行动。据时人观察,在当时的武汉,“走在马路上所见的女子十之七八是剪了的”。
与剪发的自觉行为不同,在放足方面,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措施。1927年3月23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公布的《取缔妇女缠足条例》明确规定,取缔缠足以三个月为劝导期;在劝导期间责成各县县长合同各县党部妇女部及协会设法剀切劝导;未及15岁之少女,如已缠足须即解放,未缠足者不得再缠;15岁以上30岁以下之缠足妇女,限期解放;30岁以上之缠足妇女,责令解放,不加期限;在劝导期间终了后,查有故意违抗者,由各县县长科以罚金仍令限期解放,其罚金由该县县党(部)妇女部及妇女协会办理有益妇女事项。《条例》要求在取缔缠足之前应先劝导后罚金,并针对不同年龄段采取不同措施,体现了革命政府取缔缠足的决心。4月19日,中国中央党部妇女部召开妇女放足运动大会,分配宣传和调查工作。放足运动委员会随后要求“武昌、汉阳、桥口在四月成立分会,进行放足运动,一星期内组织宣传队,五一作大规模宣传”,同时,“组织调查登记队,规定小足登记表”,并制定了《放足条例》。《放足条例》与《取缔妇女缠足条例》内容有所不同,对武汉30岁以下的妇女而言时间更仓促,“劝导期”缩短,时间提前到“阳历五月十六日”;对“到期不放足者”,处罚更为严厉,除罚款外还增加了“游街示众”等惩罚方式。当时湖北放足运动委员会要求的放足组织还未建立,如何在短时间内成功放足,是摆在运动组织者面前的问题。从相关资料看,放足运动采取“宣传”与“强迫”两种方式。4月27日,武昌市党部要求“用强迫的方法,限期放足”,同时组织宣传队和调查队,“每日轮流出发”。5月3日,刚成立的汉口放足分会召开“化装宣传会议”,准备在桥口等地分别表演。所谓“化装宣传”指的是表演话剧,试图通过表现缠足女孩的痛苦来激起观众同情,从而达到宣传放足的目的。此时妇女放足出现几个特点,一是放足人群向下层女工转移。“桥口女工三十岁以下者一律解放,三十岁以上亦定期解放。”二是由城市转向乡村。比如桥口地区“各乡村均布满放足空气,妇女们均自觉的或被迫的将足放了”。三是禁止幼童缠足。武昌放足宣传队发现“都府堤某号六岁女孩”缠足,“即携该孩入内,立解其缚,严斥其母”。改变了以前放足多为女学生的状况,对社会底层触动极大。
在剪发放足运动中,一度出现了强迫剪发、当众解除裹脚布、游街示众等强制行为,并遭到当事人的抵制和敌对方的攻击。1927年5月5日,中国湖北省妇女部向省党部提出发起剪发运动案,剪发女性虽然日渐增多,但不久转变为强制行为。强迫剪发的行为在武汉街头时常见到,大多为湖北省总工会劳动童子团所为,但在湖北各地,强制性剪发遭到阻力,在黄安,有人“被逼过甚,至于坠楼而死”。
放足运动也不是牧歌式的和平运动。来自政治对立方的报道,显示出放足运动的另一面。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说,武汉工人纠察队在棉花厂女工放工后,“当面便要那一千数百妇女除去脚带,非立时放足不可”,广东省党部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也报道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汉口缠足女工“押着游行,沿途喊口号”。这些报道显示强迫放足的方式一为当场解除裹脚布,一为游街示众。5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汉口市妇协宣传队将一位年轻女性“脱去其包脚布,赤足拖鞋,捉至妇女协会惩办。一时尾随而观者,人山人海,莫不叹妇协会办事之认真,则惩一定可警百也”。宣传队采取的方式也是当场解除裹脚布,所谓“尾随而观者,人山人海”只是“游街示众”的代名词。然而,汉口《民国日报》并未批评这些行为,反而肯定了宣传队的做法。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逆转,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剪发放足运动渐渐缓和并趋向沉寂。四一二反革命前后,当武汉国民政府得悉东南一带“剪发的女同志被诬为共产党,受尽侮辱”这一情况后,考虑到强迫剪发导致许多妇女离开革命的队伍,并引起封建势力的反攻,所以决定暂时任其自由,“不必如放足运动之积极”。5月中旬,因夏斗寅、杨森先后叛变革命,武汉地区的妇女放足运动也随之“无形松懈”。七一五反革命后,将剪发女子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谣传越来越盛,剪发女子的处境更加险恶。“一般的新军阀,把剪发的妇女,都当做了共产党看待,学校女生,受了新军阀重大的威胁不少”。为了避祸,“有些女人赶忙搞些假发,在后脑勺上挽个粑粑头,不能梳粑粑头的,只好到乡里躲起来”。
三、妇女剪发放足运动的经验教训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妇女剪发放足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采取过一些过激的措施和办法,既给当事人造成一些伤害也给整个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其一,必须加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领导。在武汉国民政府妇女剪发放足运动前期,中国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对妇女剪发放足运动非常重视,并成立各级妇女协会作为妇女剪发放足运动的指导机构,先后组织召开妇女放足动员大会,颁布有关取缔妇女缠足的条例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自觉或被迫卷入这场革命洪流之中。由此可见,政党、政权和妇女组织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武汉国民政府因面临种种危机而无暇顾及妇女剪发放足之类的事情,致使轰轰烈烈的妇女剪发放足运动迅速归于沉寂。像妇女缠足这样积弊已久的社会习俗改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政党的大力支持和稳固的政府部门的组织疏导,既不可能顺利推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到实效。
其二,必须建立健全的妇女权益保障体制。早在1926年中国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就明确指出,要按照“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使妇女享有法律、经济、教育、社会等一切权利。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剪发放足运动就是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合理稳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在制定和执行有关措施的时候漠视妇女尊严,未能考虑妇女缠足的实际情形,导致运动偏离常轨。小脚具有性的含义,缠足女子认为当众双足“不仅伤风败俗,而且极为屈辱”。当众解除裹脚布,无疑严重刺伤了缠足女性的尊严。事实上,“足之能放与否,应以以前缠裹之情形为断,年龄大小关系,实不甚重要也”,因为有些女性虽然年龄小,但“弓形早成,足骨早断”,不如“听其自由”。在急于“解放妇女”的心态下,妇女自身的痛苦并未得到重视。本为解放妇女的剪发放足运动,却给妇女套上新的枷锁,增加了新的痛苦,这是革命者始料未及的。
其三,必须考虑社会习俗改良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缠足妇女拒绝放足与传统婚姻观、审美观等因素也不无关系,变革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本非易事。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妇女剪发放足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和审美观。由于“怕将来小脚女子嫁不出去”,“除了少数顽固守旧的家庭以外,社会各界都是支持放足运动的”。但是,要想彻底改变一种风俗习惯绝非短时期内采取一些过激的办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只有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因素,针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分阶段、分步骤,采取多种措施,才能逐步改变。
其四,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尽量避免强制手段。武汉国民政府开展妇女剪发放足运动之初注意到宣传教育的作用,但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剪发放足的理由,应为党报宣传的重点,但党报报道较多的是剪发放足运动开展的工作成绩,希望对剪发放足运动产生指导作用,而剪发放足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则报道较少。剪发放足运动的急进化与此不无关系。剪发放足的理由虽然体现了“革命”的正当性,但不同的声音基本被压制。比如缠足妇女是否不能“担负革命工作”就另有可议之处。有材料表明,北伐军入湘后,“即缠足妇女,亦亲送饮食至火线,使我军得解饥渴”。通过一些强制措施即便能暂时达到某些预期目标,但控制力稍一松懈,旧的习俗又难免会死灰复燃。
注释
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载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兴梅的《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政权与妇女组织配合下中共根据地反缠足运动(1928―1949)》(《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等;姚霏的《近代中国女子剪发运动初探(1903―1927)》(《史林》2009年第2期);闻驿的《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妇女放足运动》(载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武汉妇运史资料》第6辑,1983年)等。其他有关国民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一些文章对此问题也多少有所涉及,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列举。
②以放足而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不缠足运动,是由中央政府组织、以禁罚为重要手段的运动,甚至出现了当场解除脚带等性羞辱方式(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而中共根据地的放足则是政权与妇女组织配合下,“重在宣传、动员、辅以严禁”(杨兴梅:《政权与妇女组织配合下中共根据地反缠足运动(1928―1949)》,《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这些都能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妇女剪发放足运动中找到源流。
③荷笠:《“革命”问题》,《中央副刊》第96号,1927年6月30日。
④《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31、38―39、54页。
⑤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页。
⑥邵季昂:《死里逃生之纪录》(续),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5日。
⑦[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驰译《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议员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⑧张金保:《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4―75、88页。
⑨见鬼:《短棍与头发》,《湖南民报》1927年4月18日。
⑩武汉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武汉市志・社会团体志》,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229―231页。
[11]张松林:《不朽的丰碑――纪念李硕勋烈士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第94页。
[12][1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8、659页。武汉市妇女联合会:《武汉妇运史资料》第6辑,1983年,第102―106页。
[14]羡皮:《湖北全省妇女运动》,《中央副刊》第149、150号,1927年8月22日、23日。
[15]《昨日汉口十万妇女热烈纪念三八节》,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16]《三八节武汉妇女会详情》,《大公报》1927年3月20日。
[17]诏年:《党政治下的武汉妇女》,《新女性》第2卷第6号,1927年6月。
[18]《取缔妇女缠足条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19]江柳声:《汉口妇女之放足运动》,《申报》1927年5月17日。
[20]武汉市妇女联合会:《武汉妇女运动大事记》(初稿),1981年,第31页。
[21]湖北政法史志编篡委员会:《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第556―557页。
[22]《武昌女党员放足运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
[23]《汉口放足运动委员会注意宣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25]《省工会检查放足运动成绩》,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
[26]《汉口桥口放足运动之急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27]《妇女放足运动之积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9日。
[28]《省党部三十二次常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
[29]黄宝实:《北伐时期的经历与见闻》,《传记文学》第13卷第2期,1968年8月。
[30]蔡寄鸥:《四十年来闻见录》,汉口震旦民报社,1932年,第198页。
[31]黄咏台:《从汉口逃出一个同志的报告》(续),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32]《驻汉记者述武汉近况之一般》,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
[33]《妇女协会热心放足运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3日。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95页。
[35]《武汉各党部妇女部联席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3日。
[36]《省妇协工作之紧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37]杨玉华:《湖北妇女》,《湖北妇女》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20日。
[39]荣孟源:《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38―139页。
[40]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1]姚灵犀:《采菲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