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场合隐性采访有没有底线?
时间:2022-03-24 05:4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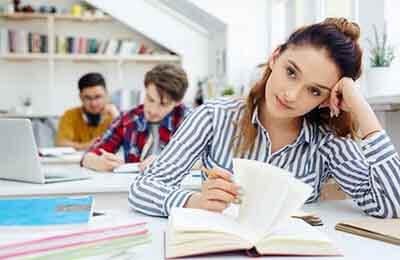
目前中国新闻界,由于受众阅读期待和追求报道真实性的驱动,隐性采访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成为某些媒体的“镇山之宝”。记者自然是满心欢喜,而学院派的研究者则从权利与义务的对等、隐私权的保护和诸种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因素出发,提出对隐性采访应该加以若干限制,隐性采访应该有自己的实施底线和应遵从的原则,但同时也提出:对于在公开场合中活动的人可以使用隐性采访这种采获新闻信息的方式。
何为公开场合?研究者在讨论公开场合中的隐性采访问题时所说的公开场合,一般是指“用于公共活动的物理空间”(顾理平《隐性采访论》第183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如道路、公园、广场、剧院等场所。在这些场合里,顾理平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一种主动昭示于人的行为,即使不是主动昭示,在法律上也应该认为是可以通过新闻进行报道而不必事先征得被采访者的许可。否则,许多新闻活动就无法开展”(《隐性采访论》第184页)。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不存在隐私(宁居)的侵扰问题,顾理平还引张新宝、普洛赛尔等人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显然,顾理平的这一主张是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但在我们看来,这一主张恰恰有待于重新进行反思。公开场合中隐性采访存不存在隐私侵权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公开场合中存不存在私人空间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公开场合里存在私人空间,那我们就必须对在其中进行的隐性采访进行必要的限制,不能随便对一个处在公开场合里的普通人实施隐性采访。那么,公开场合里有无私人空间呢?根据我们的个人体验,这个空间显然是存在的。比如,你坐在广场边的长凳上想安静地休息一下,近在咫尺的吵闹显然会产生侵扰;广场上一对偎依在一起的情侣,也不会希望他们身边围满无聊的看客。当然,这里所说的私人空间有物理的存在形式,但更主要的是指一种精神空间,这一点恰是前面所提及的公开场合定义中所忽略的一个维度,而这个维度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与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一样重要。由于对公开场合里私人精神空间的忽略,使得人们在谈论公开场合中的隐性采访问题时,犯了一刀切的错误,而忽视了公开场合中人的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应该做的针对不同性质的活动采取不同对待方式的努力。
因此,隐性采访的实施,公开场合不应该成为它的理由,或者说,认为公开场合中可以进行隐性采访这一观点存有疏漏之处。我们不能仅以物理空间的公开或私人属性来作为隐性采访是否可以实施的依据,还要虑及人们活动的性质问题。
从保护普通人的生活安宁这一基本目的出发,对于公开场合中的隐性采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实施底线或曰原则:对于公开场合中卷入公共活动的人可以实施隐性采访。即:我们没有必要在征得每个参加公共庆典的人的许可之后,才能让摄像机扫过他们;同时对于那些在别处独自低头沉思或默默垂泣的人,我们也不应进行侵扰。这样既保证了新闻采集活动的正常开展,又为私人活动留出了自由的空间。
在关于公开场合中隐性采访问题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及这样的例子:公开场合中的情侣亲吻可不可以进行隐性采访?对于这一问题,顾理平是这样说的:“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马路上的恋人亲昵行为,如接吻等,他们的行为本身是隐含主动昭示于人的意思表示,新闻记者通过隐性采访加以报道,不该认为是侵权行为――它可能是媒体对一种美好情感的赞美,也可能是对有伤风化行为的谴责,都属于合法、合理的正常新闻报道范围。”(《隐性采访论》第197页)公开场合中恋人的亲昵行为是否就“隐含主动昭示于人的意思”?我看未必。恋人间的亲昵行为大多是情动于中难以抑制所致,在这一点上,公开场合与私人住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公开场合缺少必要的遮掩(保护),但说他“主动昭示于人”实在有些冤枉,最多不过无意中曝露于天下而已。有人看到、记在心里,这是允许的,但如果刊载在报纸上,或是播放在电视里,予以传播,就有侵扰之嫌,被采访者有维护隐私、还其安宁、讨回公道的权利,哪怕媒体是出于赞美的初衷。因为这是一种私人活动,根据我们前面提出的原则,记者和媒体不应侵扰他们的安宁。也许有人会以有伤风化作为抗辩的理由。恋人在公开场合中的亲昵行为如接吻是否被看作有伤风化,也是一个有待考量的问题。因为风化本身,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公开场合中的接吻在20 年前毫无疑问会被大多数人认为有伤风化,但今天,就我们的观察和体验,人们已经把这种事情看得稀松平常,很少会有人再上升到风化的高度。
在媒体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令人恐惧的今天,在处理记者、媒体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时,对记者、媒体的权利进行适当限制,是可以接受的,就如同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公开场合中隐性采访的底线问题一样。因为在媒体与安宁正常的生活二者之间,大多数人的选择恐怕还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