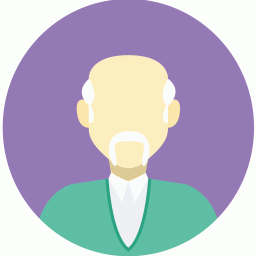国土规划中的“法律理性”
时间:2022-02-26 05:20:29

2010年12月,国务院了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我们认为,《规划》中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即禁止开发区域和限制开发区域的划定及其相关规制措施的规定,是《规划》之“法律理性”的集中体现。
追认和完善地区发展成果
――法律主要是社会变迁的反应装置,而不是社会变迁的推动装置
《规划》后,官方舆论称之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战略大棋局,也是考验中华民族发展智慧的“珍珑”难局。这类评价更多表达了评价者的某种良好愿景,或是溢美之词。其实,规划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追认和完善地区发展成果,而不是建构性地去设计发展地区和发展模式。“作为马后炮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一说法不但不是贬低规划的制定者,反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者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教授曾提出如下命题: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1]。“法律由事实而生”(The law arises out of/after the fact),“法律规定,并非语言,乃系事物”(laws are imposed, not on words, but things),“因种种行为之经验而立法”,“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 这些经典的法律谚语其实也蕴含着这个深刻的法理。马克思甚至阐释得更为明确:“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达法律,在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表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任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极端任性。”[2]
对此,以下的评论更显得客观公正。
东北工业区曾经是中国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地区规划,这不是拍脑袋的决定,而是因为解放后东北有领先于全国的重工业基础,发达的铁路交通,以及邻接盟国苏联的地缘优势,东北的优先发展显得顺理成章。而中国从未规划过放弃发展东北,或者用其他地区取代东北的工业地位,但它仍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被沿海地区代替了,可以说,规划既没有在上世纪50年代凭空制造东北,也没能在八九十年代成功挽救东北的经济地位。更为人熟知的地区规划例子是北京市,北京市一向注重区域规划,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规划北京人口绝对不能超过1000万,但很快被突破,接着又规划不能超过1500万,又被突破,只能不断随着城市发展编制新的规划,很难说这些规划在任何多大意义上指导了北京的城市发展。实际上,即使在中国很短的市场经济实践来看,先有发展后有规划,也是常见和普遍的状态,从上世纪80年代的长三角产业集群,到最近的成都城乡一体化试验区,几乎都是本地先动起来,然后请求中央在规划中进行承认[3]。
事实上,目前的河南已经或正在向最适合于其自然禀赋的方向发展――即粮食主产区,以及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因此,明智的做法只是确认或追认其为“中原经济区”而已。同理,青藏高原本来就适于作为禁止开发区,这里一直就是中国的“水塔”和中原农耕地区的生存屏障。明智的做法当然也是确认或追认其为“重点生态功能区”或禁止开发区而已。其实,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主要作为限制开发区的“中原经济区”和主要作为禁止开发区的青藏高原,这种区域之间的发展分工的格局,作为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国家事实”,已经存在数千年的历史了。这里面蕴含着使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密码” [4]。
防范和化解国家政治风险
――法律的主要功能是防范生态风险、粮食风险等最坏情形的出现
《规划》后刚刚过去一年,国务院就接着了最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其中规定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西北地区涉及的连片特困地区是六盘山区、甘青藏区、新疆南疆的三地州,以及此前规定的14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陕西50、甘肃43、青海15、宁夏8、新疆27。其中有些县已包含在上述的连片特困区中)。从分布范围来看,西北贫困地区乃是全国贫困地区中分布地域范围最大的一个地区,是全国市场化发育程度最为滞后的地区,也是全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地区。在《规划》中,西北贫困地区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这是一个将生态安全、扶贫攻坚、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集于一身的地区。因此,也是国家政治风险最大的一个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划》将西北地区主要规定为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并给予特别保护,彰显了其真正的“法律理性”。
法律的主要功能是防范最坏情形即最大风险。这个极为重要的法理,在中国,已经被人们,尤其是各级各类立法者和决策者忽略很久。我们也许知道,“国家之安全乃最高的法律”(The safety of the state is the supreme law),“法律效果在乎强制执行”,“法律应着眼于频频发生之事件而制定,不应着眼于不能预测之事件而制定”。但是,“预防重于救济”,并不是人人都熟谙其中的深义。尽管我们明白,法律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预防可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但是,桑斯坦教授却更进一步,他研究认为,遍历现代世界各国,许多需要发挥预防功能的法律原则是瘫痪性的。风险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可能预防全部的风险。预防原则应当进行重构,代之以灾难预防原则,即对重大危险进行预防,并在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中注意相关法律措施的成本[5]。这显然是一个重要而及时的提醒。中国的西北地区是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重大成本进行“预防”的地区。这是因为,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的治理和控制是几千年来历代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是中国政治地理学上的“好望角”[6]。“西北虽然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但却是国家稳定、统一和安全的中心” [7]。因此,我们需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法制保障之于西北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城乡统筹的重要性。同理,将中原粮食主产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极为明智的举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是当代中国应该预防,并且是可以预防的重大政治风险。《规划》将其作为重点予以规定,体现的便是其非凡的“法律理性”。
全国四大功能区是一个大尺度、大空间、长距离的“分工―交易”(经由财政转移支付)格局,也就是说,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的开发区或限制开发区的人们要向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的禁止开发区的人们 “购买”生态产品,而后者则要向前者“购买”工业品等。尽管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以提供主体产品的类型为基准划分的,每个功能区内部也是存在各类产品的“分工―交易”格局的,但是“西北水木和东南制造”,这却是中国最宏观也是最重大的区域分工,这是由西北高东南低这一中国特有的阶梯式地形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由此导致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宽泛的、松散的“反馈环”。当分工和交易在尺度上变得越宽泛时,“反馈环就变得愈益松散,动机也就愈小,而环境行动的挑战就变得越大。”[8]相反,“当反馈环收紧时,进化运行得最强有力。当个体主要与宇宙里小尺度子集相互作用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得最自然,即在各种实时的时间尺度上实现了它们行动的成本和收益……我们更可能保持住宅无垃圾而不是社区无垃圾;更可能维持社区环境而不是国家环境;更可能显示对国家环境的关心而不是对全球环境的关心……我们很难兑现未来。于是,在空间和时间两者上,直接的总优先于远距离的……再循环计划之所以运转,在某种程度上在于它使人们自我感觉良好,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奖励和处罚相联系着。”[9]
当广东云浮市的居住在优化开发区的市民,可以直接驾车或徒步穿行在市内限制开发区的绿道并体验和饱览到其中的美丽的田园风光时,他们更愿意向本市的限制开发区的人们“购买”生态产品,而不是向千里之外的大西北“三江源”的牧民去“购买”生态产品。因此,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是在一个宽泛的、松散的“反馈环”的现实背景下进行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并富有实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保障,保护“中华水塔”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当然,保证富有实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运行,也只是减少中国生态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西北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环境恶化会导致当地人口的严重贫困化,但是解决贫困问题的目的不仅仅是简单地快速增加村民的收入,而是要在资源利用和维持生计中间达成一个平衡。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是扶贫中的第一要义……通过减少风险实现可持续性,扶贫和环境保护达成了一致。”[10]这里的含义就是,要通过明晰土地和草场产权来“收紧反馈环”, 这将在各种实时的时间尺度上实现牧民行动的成本和收益。在资源利用和维持生计中间达成一个平衡点,这是制度设计的关键所在。
规制和约束政府寻租行为
――立法主要是规定“不可为”事项,而不是“可为”事项
根据《规划》的要求,中央根据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各自的功能定位,分别设定了不同的考核指标。自此中国将告别“唯GDP论”的考核体系。未来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将加码。比如,对于禁止开发区,《规划》规定:“按照保护对象确定评价内容,强化对自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况的评价。主要考核依法管理的情况、污染物‘零排放’情况、保护对象完好程度以及保护目标实现情况等内容,不考核旅游收入等经济指标。”对于限制开发区,《规划》规定:“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实行农业发展优先的绩效评价,强化对农产品保障能力的评价,弱化对工业化城镇化相关经济指标的评价,主要考核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民收入等指标,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工业、财政收入和城镇化率等指标。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强化对提供生态产品能力的评价,弱化对工业化城镇化相关经济指标的评价,主要考核大气和水体质量、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治理率、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草原植被覆盖度、草畜平衡、生物多样性等指标,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工业、农产品生产、财政收入和城镇化率等指标。”
显然,《规划》中的这些规定,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区性规划中地方政府的强势性和GDP冲动,尤其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意义重大。在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前者,如果对当地政府仍以GDP作为其政绩考核的指标,那么,法律规定对相关区域的“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就是一句空话,就很难规制和约束政府的“土地财政”等寻租行为,相关法律就会形同具文。当然,这里还有更为重要的言外之意,就是,对于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尤其是前者,《规划》对其进行定位及对相关考核指标的规定,似乎有些“画蛇添足”之嫌。根据一般的法理和原理,法律一般只规定“不可为”的事情,而不限定“可为”的事情。哈特曾对法律提出了一个功能主义的定义:法律的存在指的是某些人类行为不再是选择性的,而是在某些意义上是义务性的 [11]。基于哈特的这个定义,我们认为,如果要真正感受规则的存在,那么最好是从义务(职责或职权)的角度来理解规则――只要我们违反它,就会随之带来某种不利的后果或负担时,我们就感受到了规则的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规则都具有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要素:“如果…则…否则…。”
也就是说,如果主体功能区规划只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区进行规定,这样会更加合理和可行。对于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尤其是前者的地方政府,即使法律不规定他们“可为”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以及相关的考核指标,他们也有足够强大的“自我激励”去进行积极地、探索性地开发,因为就凭市场化这只“无形之手”已使他们具有了足够的利益空间。公共服务是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间通过相互竞争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没有良好的公共服务的地方,民众会“用脚投票”。更何况,如何“优化”开发,如何“重点”开发,如何进行城镇的布局和规划,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更明白相关的局限条件,从而会因地因时制宜地采取发展策略。公共工程的规划者往往不信任普通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在实施大规模的工程时把丰富的地方性的、实践的、传统的和习惯的知识排除在外[12]。事实上,只有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在通常情况下是土地功能和禀赋的最佳识别者[13]。立法不宜对政府“可以做什么”作出规定。“容许之事,未必悉合正义”。因此,《规划》对于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这些涉及“可为”事项的规定,其意义并不大,甚至连指导性意义的发挥也令人怀疑,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城市化更多是历史“演化”的产物,是由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所促成的。《规划》之于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其象征性的“确认”意义显然大于其实质性的“规制”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规划》似乎“太强调生产区位,而忽略了未来交往对地区的革新”。中国香港如果在1950年代,会被定义为贸易区,但是贸易过程中积累的规则感,则最终让香港变成了信用可嘉的金融中心。而美国波士顿过去也是港口,但现在却成为高科技中心。底特律若是被定义为“装备业和汽车中心”,那么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它被“去中心”了。不是定义什么就应当是什么,在全球化格局中,资本、技术和贸易的需求让其最终变成什么,而且过程会有一定的随机性。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发展更能证明并非规划的产物,而与张五常说的“县际竞争”,从下往上的发展冲动有关[14]。
“法无禁止公民即可为,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法理。所谓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法律授权。所谓“法不禁止即自由”,指公民的行为无法律禁止皆不违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它仅是一个“法理”,在我国广义的行政法、民法等相关条文中,并无明确的引用。确切地讲,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接受与体现,如“依法行政”等。然而,《规划》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公法”属性的规范性文件,理应充分体现 “权力应严格解释”,“受任人不得超越自己所被授予之权限”等这样的“法律理性”。 国土资源的开发和优化配置,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一,还是要尊重、运用市场主导和取向,而不能沿袭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思路。如果政府通过立法,规定许多“可为”的事项,那么,就极有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上中央集权过度扩张的倾向,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越伸越长,市场价格信号会被扭曲,国企垄断性加剧,挤占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寻租腐败的土壤有增无减[15]。所以,《规划》明确规定,对禁止开发区域,要依法实施强制性保护。这是《规划》中的“法律理性”的集中体现。
科学规划国“土”资源的合理布局
――“法律不强人以不能”
《规划》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不同的国土空间,自然状况不同。海拔很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以及其他生态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的区域,并不适宜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有的区域甚至不适宜高强度的农牧业开发。否则,将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对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造成损害。因此,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根据不同国土空间的自然属性确定不同的开发内容。”“一定的国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必有一种主体功能。”因此,是要将国土空间开发从占用土地的外延扩张为主,转向调整优化空间结构为主。这样的规定是明智的。
但是,《规划》后,为了易于理解,《规划》参与制定者的相关解释曾以“屋子里面房间的功能”来做比方,来阐释国土主体功能区划分的道理。这样的解释,显然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房屋对应的是物品的空间摆放和处理,但是国家的主功能区规划主要规划的是国“土”,而不是国“人”。房间内物品的空间摆放和处理对应的是人的流动,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的行为具有发现性,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再现,他们会通过流动来选择和确定不同区位的真正角色,他们是“无形之手”,而不是完全遵循着“有形之手”的指示 [16]。“法律不强人以不能”。法律要规定可以做到的事,不能规定人们做不到的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规划“国土”配置,但不能规划“人才”流动。如果事实上把国土和人才捆绑起来配置,就是典型的“乌托邦智慧”。也就是说,法律只能规划国“土”,而不能规划国“人”,国土相当于法律上的不动产,“国人”(人力资源)则类似于法律上的“动产”。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将地籍管理和户籍管理捆绑在一起的管理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这些“动产”要素事实上在各类主体功能区之间如何流动,主要不是靠政府的“规划”,而是遵循市场规律来配置的。有一首歌叫《回娘家》,歌词的部分内容是“原来她要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这反映了过去那个时代,“人流(背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物流”(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信息流”( 要回娘家)“三位一体”式的流动。“托人给乡下的朋友带些礼物并捎个口信”,也体现了同样情形。但是在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三位分流”的场景――“住在广西阳朔乡间旅馆里的汤姆,每天通过电子邮件给美国洛杉矶的公司发去创意方案,偶尔也会给英国伦敦的弟弟用快件寄去广西的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今天已经成了一个“人流的归流、物流的物流、信息流的归信息流”的时代了[17]。“人流”的一般必要性应该是旅游――因为旅游不能被(就像死亡、吃饭以及不能被一样),而不是“做事”,知识经济时代的许多事务――尤其是智力产品,我们坐在家里就能完成。我们已确实无法对“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进行“三位一体”式的规划了――除了民族国家的国“土”之外。
尽管《规划》认可了这样的现实:我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生态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并与主要消费地呈逆向分布;一些地区粗放式、无节制的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短缺、能源不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大规模长距离调水(南水北调)、运煤(西煤东运)、送电、输气(西气东输)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带来了交通拥挤、地面沉降、绿色生态空间锐减等问题;劳动人口与赡养人口异地居住,等等。这样的现实意味着,政府如果要将这里面涉及的“人流”、“物流”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并使其与规划中的国土主体功能区相“协调发展”,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政府并不能全面和实时地掌握关于“人流”、“物流”的信息。事实上,只有流动中的“人”和“物”乃是其流动目标和方向的最佳判断者和识别者。提出所谓“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概念,并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提法――“土地的城市化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应快步跟上土地城市化”,是很让人费解的。
在《规划》的文本中,还是在多处体现了政府对“人流”、“物流”进行前瞻性的“规划”的意图和决心。“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在集聚经济的同时要集聚相应规模的人口,引导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人口有序转移到重点开发区域。”“城市化地区和各城市在扩大城市建设空间的同时,要增加相应规模的人口,提高建成区域的人口密度。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减少人口规模的同时,要相应减少人口占地的规模。”这样的试图在实现国土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同时,“规划”人口(人力资源)流动的做法显然值得商榷。正是由于《规划》承载了过多的使命,所以,其目标便必然成了一个“完美”的目标:“我们既要满足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土空间的巨大需求,又要为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而保护耕地,还要为保障生态安全和人民健康,应对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保护并扩大绿色生态空间。”这些目标,作为“愿景”是可以的,但是,要作为一部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些目标使“法律不堪重负”。
法律人都明白,“法律不强人以不能”,尤其是不能规划作为能动主体的人的流动。“简洁乃法律之友”,简约的法律才有力量。法律的目标必须明确而简洁,而且要易于达到。《规划》一方面要对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3%的所谓适宜开发的地区进行空间节约集约式的开发,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55%的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这两个目标,从执法的成本上来讲,很难兼顾,法律的强制力的面向只有顾及一头。重点应该是,“对农产品主产区,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但仍要鼓励农业开发;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但仍允许一定程度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正如前述,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是我们输不起的风险。风险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可能预防全部的风险。所以桑斯坦主张,预防原则应当进行重构,代之以灾难预防原则,即对重大危险进行预防,并在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中注意相关法律措施的成本[18]。真正领会了其中的真义,《规划》中的“法律理性”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
注释:
[1] 【美】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经验的疆界》,丁丹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2]W・Friedman. Law in a Changing Society.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72: 1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4][15]《国土规划的理性自负》,。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3月3日。
[17]《应淡化区域功能设置中的建构性》,view.news.省略/a/20110610/00003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3月6日。
[18]王勇:《网路、公路与铁路》,images.省略/art/86174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3月2日。
(作者分别系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北贫困地区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三农法律制度建设研究”〔09XFX002〕的阶段性成果)